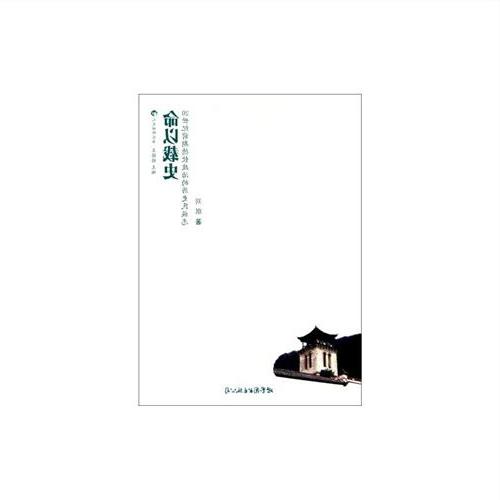王铭铭刘雪婷 刘琪 读王铭铭新作《人生史与人类学》
《人生史与人类学》 汇集了一篇"绪论"与三篇相关论文,总结了近年来王铭铭对于相关主题的思索。
王铭铭开宗明义的写道:
我推崇"人生史"这个概念。"人生史"指的是一种不怎么像社会科学的方法,它不同于"量化研究",虽则相比更接近"质性研究",却与之差异也大。......我的主张是,"人生史"研究有一个明了的前提,即被选择的个别人物的整体一生。
什么是"整体一生"?那也就是被选择的人物生死之间的生活。这个意义上的"人生史",与古代中国的"人物志"是有相通之处的。我的追求是历史方面的,以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究,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穷尽相关文献,进行相关口述史或口承传统(如传说、传闻、谣言、访谈)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有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制作某一"history of a life"。
"人生史"是一种与传统社会科学不同的研究方法,然而,王铭铭并非凭空提出这样的概念,而是基于他对于人类学学科史,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深刻反思。
王铭铭对于学科史的反思,从两条脉络加以展开。首先,是对民族志知识及人类学"认识制度"的梳理。王铭铭认为,现代人类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阶段,人类学以"文化科学"的客观性为荣;第二,是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阶段,格尔兹敢于承认自己的学问与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之间的差异,并且,在此基础上将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视作是和平相处的众多观念世界的一个世界;第三,是以利益或权力理论为基础的"后诠释时代"。
王铭铭认为,格尔兹的"修正版"现代人类学是我们应该回归的研究基础。然而,王铭铭又进一步指出,格尔兹总是试图清除"乱相",建立干净的类型,这就使他丧失了对于人文世界中混融内涵的关注。
以溪村的故事为例,从巴斯(Frederik Barth)和利奇(Edmund Leach)对于"当地思考者"的论述出发,王铭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以为,人类学研究,不简单是去追寻不同于自己、且相互不同的文化模式,而是寻找不同的模式的当地综合方式。进行现实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差异与区分而确立的理想型概念,显然是不充分的;人类学研究者尚需对这"三位一体"的文化基础加以宇宙观的结构分析及社会观的道德分析,并在方法论上形成一种基于"当地的广泛综合"。
王铭铭对于学科史的另一反思,集中于历史与结构的关系。延续《经验与心态》中的思考,王铭铭试图寻找"过程"与"结构"的合一,寻找历史学关注的时间线条与人类学关注的"深层结构"的汇合。王铭铭认为,历史的线条本与人类学的"结构关怀"不相矛盾,"如果说,\'历史有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不仅可以表现为宇宙观的空间秩序,而且也可以表现为历史观的时间形态。
"传统中国的"治乱"与"兴衰",正是这种时间形态的表现。此外,克虏伯(A.
L. Kroeber)关于"天才"的论述,也引发了王铭铭的兴趣。王铭铭同意杰尔(Alfred Gell)的论述,即人类学之不同于社会学,在于其对"传记的深度"的追求。受冯友兰的启发,王铭铭进一步指出,这种"传记的深度",应当被深化为"境界的深度"。
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空场景中,解析不同人物的"人生境界",以及这些"境界"背后的社会观与文化观,由此达致对"历史的生命感受"的认识,这是人类学应当具有的使命。
最后,在对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解读中,王铭铭对社会科学的"集体中心主义"展开了批判。王铭铭指出,社会科学"集体表象"的理论倾向于排斥所谓无关宏旨的"个人小事",偏重国族政治、文化、战争、经济等所谓的"全局描述"。
"集体表象"中的"集体",实则指的是"国族",这一概念,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既丧失了对人的生命实质的关怀,又使其视野局限于"国家",而无以涵盖小于这一"整体",或大于这个"整体"的"社会事实"。王铭铭认为,从表面上看,司马相如固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个人物却在人生的不同时间段中,穿越过"社会"一词所无法涵盖的另一种"整体"的范围。王铭铭写道:
一方面,如果说他确实是一个个体,那么,也可以说,这个个体,自身就是整体性的,他不是作为等待的整体的社会加以涵盖的碎片存在的。相反,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司马相如集家国天下的所有成分于一身......他的人生,与这一人生之外的世界之间,不是二元分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交错和包容的关系。作为一个个体,他所包容的,也不是一个近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而是一个正在构成某种相互关系的、超越社会的大一统体系。
关注作为"整体"的"个体",为个体"著书立传",是王铭铭倡导"人生史"研究的旨趣。事实上,在王铭铭看来,他并非第一个摇旗呐喊之人。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传记本是底蕴深厚的体例,然而,随着20世纪"国族主义"的兴起,"人的专史"逐渐被"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说"取代。
20世纪前叶,梁启超与钱穆都曾提出过"回归史传"的倡导,却很快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到了21世纪的今天,王铭铭再度发起了"回归"的努力。
赞誉之词自不多言,在我看来,这本《人生史与人类学》,应该放在两个脉络中加以认识。第一,是"后殖民时代"对人类学造成的挑战。当世界在现代化浪潮中被塑造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以"寻找他者"为使命的人类学家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惑:传统民族志是否应当被抛弃?人类学是否还有用武之地?新的"民族志"应当怎样书写?传记式的写作方式,更加接近哲学的思考,为人类学"突破自身"指明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第二,是"西方社会科学"在我国的遭遇。
自19世纪中叶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以来,国人对于"西方"总有一种矛盾的双重心态:一方面,小心翼翼亦步亦趋的跟上西方科技与文化的进步,生怕自己成为"落后分子";另一方面,又总是带着些不甘心,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与西方抗衡的蛛丝马迹。
在学术界中,第一种心态导致了自愿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为西方理论寻找"中国脚注"的"不懈努力";第二种心态看似"爱国",却往往掉入将西方思想作为坐标,将某些"中国概念"生搬硬套的窠臼。这本书,是突破这两种心态,真正回归中国历史与传统,并以此为基点重建"社会科学"的可贵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