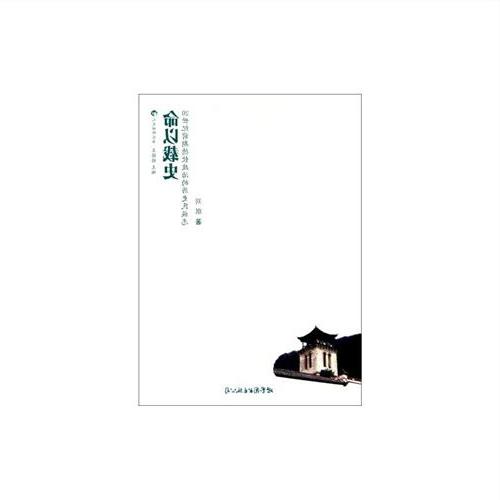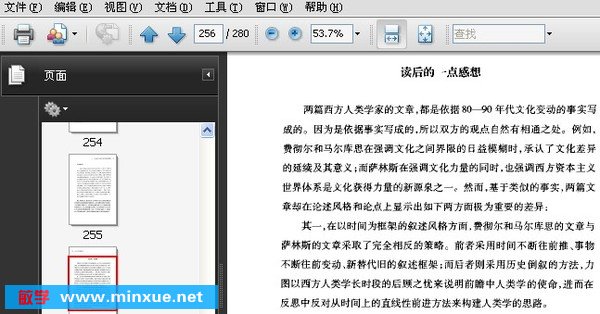口述史王铭铭 试论口述历史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几点启示
近年来,我国口述历史在理论和实践上日臻成熟。一方面,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它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已经被学界所公认,口述历史杂志、专栏、学术团体以及各种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多个学科所使用,并出现了诸如口述历史民族志等,富有交叉学科特点的新方法、新成果。
在口述史学科发展较为完善的西方史学界,口述历史属于社会史门下,两者在研究理念、方法、路径等方面,有很多相通和共性之处。中国当代社会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正处于学科建设的关键时期,口述历史除了能够为其提供新史料之外,在理论和方法的构建上又会有哪些启示呢?
一、人人都有历史:当代社会史研究视野的定位
“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该被遗忘”,这是写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1]扉页上的一句话,它不仅代表了这一本书的历史价值判断,而且标明了口述历史所秉持的一种史观。
广义上讲,凡是利用口述史料写作的历史都可以称为口述历史。从这一概念出发,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时,就有了口述历史的记录。它是人类历史证据中最为古老的形式之一。然而,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口述史学创立以来,口述历史专指“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
”[2]口述历史产生之初,史学界更多地把它视为一种活史料,因其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凸显了它的价值和地位。作为口述史学的创立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的创办人艾伦?内文斯(AllanNevins)是一位政治史学者,他关注的访谈对象多是政界、商界的精英和社会名流,倡导通过搜集他们的口述资料,丰富和扩充文献档案内容,并以声音的形式更多地保留历史记录。
1961年,杜鲁门图书馆首开美国总统口述历史计划,通过采访政府政要、白宫管理人员、家庭成员等相关人物,为历届总统和政府搜集口述访谈资料,以挖掘和补充文献记录之外的原始资料信息。
直到1960年代中期,口述历史研究者才开始重视并着手撰写来自下层社会的历史。“美国开始出现第二代口述史学家。他们不仅将口述历史视为非传统资料的一种来源,而且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描述与赋权于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和在历史上被剥夺权利的人群,进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学家所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而扩展口述历史的搜集范围与视野。
”[3]那些曾经被档案资料忽视的平凡大众、劳动阶级、弱势群体开始成为口述访谈的对象,他们不再是历史中的默默无语者或抽象的数字,而纷纷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将自己的经历和记忆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下来传之后世。
口述历史的这种转变或者可以称之为颠覆性的革命,是在西方整个新社会史发展大背景下发生的,它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研究对象的转换,而是隐含着历史观的变化。
历史是由谁创造的,谁才是历史的主角?这是史学研究需要反复思考和不断追问的话题。基于这种认识,口述历史内容不断拓展,广涉社会生活史、家族史、妇女史、黑人史、劳工史、个人生命史等多个层面。今天西方的口述历史,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层次的人群,可以发挥的主题极其广泛。“自下而上”、关注底层、让大众发声,使口述历史拥有了“人民性”这一值得称道的主要特色。
尽管我国史学界对“社会史是什么”尚没有统一的认识,还存在着通史说与专史说的分歧,范式说与视角说的争论。但是,从我国30多年社会史研究的实践来看,一系列专题研究,基本揭示了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话题。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中国社会史的当代部分,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很大一部分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延续。但同时,还有一定的范畴是中国当代社会所独有的或变化极大的,后者的开掘需要与整个当代史研究状况紧密联系、综合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当代史(国史)研究才真正开启,最初它是从中共党史社会主义部分中分离出来的,多年来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等方面,尤其是对国家领袖人物和上层决策的研究比较突出,这与其断代史的学科性质相差甚远。
因此,有学者积极倡导“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认为“与当代政治史、当代经济史和当代文化史的研究相比,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但滞后,而且薄弱,是个亟须填补的空白。”[4]也有学者更加直接地指出,当代社会史虽起步较晚,在国史分支学科中最为薄弱,但依然是国史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5]目前中国当代史之于社会史最需要的,一方面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使其真正囊括当代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多维的观察视角,使其实现从多个角度全面、多层次地呈现国史的进程。
有学者指出“国史可以说是断代性质的全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目前国史研究中,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活动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
……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的历史全貌。”[6]面对当代史的研究现状和社会史一起步便肩负的重要使命,厘清当代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就显得十分迫切。而一个学科的独立性,除了表现在研究内容之外,它的研究视角、取向、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口述历史在这方面为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口述历史的成果也使得社会史实现这样的作为具有了可能性。从近年我国口述史著述来看,有关于“大跃进”、五七干校、“文革”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等共和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有关于“土改”、“民主改革”、“上山下乡”等重大事件的记忆追索;也有关于梁漱溟、老舍、浩然、舒芜等文化名人,以及知青部落、农民工等普通人群体生活经历的记录。
这些选题和历史细节是以往当代史中欠缺的,映衬了社会层面的历史变迁,为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作为中国当代史的分支史,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史:从研究内容上来说,它以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其研究重点一方面是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真实形貌,另一方面要揭示社会组织、结构、制度变化的动因和规律,而其难点在于分析民众心态、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流变;从学科属性上来说,它既具有继承性,是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史的延续,又具有开放性,是以新中国建立为起点,正在进行和不断发展着的历史,由是观之,它也是现实性最为突出的史学研究;从研究视角和立场上来说,它引用和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结合,立足民间史料开展区域研究,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最终实现对整体史的全面认识和把握。
带着这些新鲜的治史理念和研究取向,当代社会史定将成为中国当代史中最活跃、最具发展潜力和前景的学科。它的学术意义和贡献,以及它的现实功用,决定了它是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撑,更是学科发展的新动力和生长点。
二、生命叙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路径选择
我们反对把社会史看出是边角余料,或是“剩余的历史”的简单组合,这既是对社会史不公正的贬低,也与社会史长时段、整体研究、“解剖麻雀”的主张完全背离。当代社会史研究是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为主脉的社会历史研究,一方面要突出有别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要时时观照与这些分支史相互交叉、渗透的诸多领域。
然而,当社会史把观察视角放低、缩微时,极容易陷入琐碎和零散。我们如何能够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串联起来,在平凡、芜杂的琐事中梳理出社会变迁的脉络线索,进而揭示整个大历史的主流呢?
借助生命叙事应该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体,无论伟人还是普通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他们在历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而社会变迁也在他们的人生岁月中留下了层次不一的痕迹。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
[7]利用个体生命历程来反映时代变化和探究社会问题,已经被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采用,口述史在这里既被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同时也是达到这种较高诉求的主要资料来源。
尽管口述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长期以来遭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但它的鲜活灵动、形象感人也始终令抽象枯燥的文献史料无法与之匹敌。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讲述的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血肉丰满、感人至深,在个体生命的讲述中映衬出了宏大的社会主题。
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重建了人民曾经活过的日子,另一方面又将个体与社会紧紧联系起来。这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也是从年鉴学派到社会史代表人物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以来一直倡导的观点,即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这也应该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旨趣所在。
那些源于记忆的生命叙事对当代社会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其一,个体记忆中承载着时代的集体记忆。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看似个人生命历程的讲述,表达的却不只是个人生活的苦乐辛酸,而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共同经历和命运。
正如保罗?汤普森(PaulThompson)所说的“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8]在生命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有时甚至可以反观到自己的影子。
其二,集体记忆一旦形成,会影响到人们的共同历史意识,甚至影响到民族的认同感。口述历史通过讲述来唤醒人们的记忆,从而发现和揭示其中隐含着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群体的社会心理。
其深层的价值在于重塑人们的记忆,从而加强或改变人们对历史的判断。《中国知青口述史》采制者刘小萌这样评价十三位知青的口述:“希望紧紧围绕这些典型人物的回忆,对那场运动和掩身其后的社会大背景,加以多角度的深度再现。
”[9]正是在这些看似个别人物的微观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洪流。这里没有直接的说教,更不是板起面孔的论理,而是把人们曾经活过的日子活脱脱地展示给人看,这才是历史本应存在的形态,由此也才能打动人、吸引人、教育人。
2008年我采写的口述史文本《从童养媳到劳动模范》,记述了一名普通妇女从旧中国的童养媳,到建国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省劳动模范的人生历程。几十年间她个人命运的变化十分曲折,而这些变化又无不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新中国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她的故事中有所呈现:
土改与合作化运动:
沈阳解放那天晚上,那雪下的大呀,白菜都冻到地里头了。一过了年,家家户户男的去开会,开会就写牌子、木头桩子,下头就放粮,完了钉桩子,写着姓氏名谁,分地。俺们家分了一垧(十亩)地,还分了三亩不好的,在壕沟外的坟圈那里,只能种荞麦,这日子就好了。
49年开春就自己种地了,求人换工差具(互助组的前身),你家有犁我家有马,合着干。1952年成立初级社,55年冬天就走合作化道路了。开始入社,我二哥入了,我妈也入进去了,那都是自愿的。
那时候,有钱的不愿意入,愿意自个儿干。我愿意入,到工作队登记,人家告诉我:“你不行,才十五岁,不够十六周岁,不到入社年龄。”我就说:“我今年不够,那这冬天能干活吗?你不得到明年才干活吗?到了明年春天我不就十六岁了?就这么给我写上了,不两天,就正式批准了,我就入社参加革命了。
入党记忆:
1958年我就上大队当队长去了。大跃进起早贪黑地干,都得干到半夜,政策一下来,工作队一来一宣传,咱就带头呀,一干就干到半夜。那时心里头充满了乐、兴奋,怎么干力气也干不完,干什么都高兴。在地里歇气儿的时候,看见有块粪,赶紧按到苗根底下埋上,也不嫌脏。
……我是56年4月份入团的,1959年2月24日入党。要入党了,睡不着觉,高兴得都掉泪,那种滋味比上老何家去的心情还复杂,不知道是乐还是难受哇。总觉得一天书没念过,苦出身,做童养媳出身,一点文化没有,一下子就要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也整不好那滋味,那激动劲。
宣誓那天,来我们公社开的宣誓会,一看到那党旗挂出来,眼泪就止不住似的,瞅瞅主席像,瞅瞅党旗,就是一个高兴、激动,没有话说。就寻思一个给人家当童养媳的,今天站着讲话跟个人似的了,扬眉吐气了。我心里总是暗想要严格要求自己,党员就得像个党员样子,做出个表率出来。
“文革”时期的乡村干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挨批斗了。罪状还挺多呢,主要罪状就是抱着刘少奇大腿不放,破坏民兵连,教育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自己却找个军官跑了。再一个,就是这儿开会那儿开会,在家劳动少。其实呢,那时规定,大队干部每年必须劳动120天,我每年都超,可谁给你证实呀?当时王登云是大队书记,我是副书记,开除他党籍,让我签字我没签。
我说:“不行,开除他就得开除我,一切事都是经我们三个支委决定的。”他们没办法就走了。他们找不出事儿,能查出错嘛?分房场,王登云书记那房场,院里头有坟,还有棵小榆树。
我那房场,偏脸子,坡儿,完了咱自个儿垫,好房产都给社员了。王登云家里五个孩子,生活可困难了,但公家的便宜一点不占。秋天生产队分白菜,地头马踩、碾子轧、扒拉棵的不好的白菜分给大队干部,然后分小队干部,最后那好的才分社员。社员为啥佩服你,就在这。
老劳模的晚年境遇:
2003年,我听说《沈阳日报》登了一则消息,说给劳模补助,我这心里挺盼望又挺不好意思。这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党还想着咱们,还给钱,我觉得这是挺讨愧的事。2004年,农电局来通知,让我到市工会去领2000块钱补助。
我身体不好,老伴和妹夫替我去领的。结果到那一查,我是五十年代的劳模,给了5000块钱。你瞅这5000块钱拿回来,我就哭上了。我就寻思啊,党还想着我呢,还一个劲地给钱。我现在的钱就够花了,因为我工资低,都给补助两回了,退休时110块零3毛,那年补了200多,后来又补助了100多。
一个劲地给钱,我的心里可真不好受。这些年也不为党工作了,一点余热也不发挥了,你看张成哲和尉凤英这些老劳模,人家还在工作,还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你说我现在啥工作也不做了,党给的钱还拿,真不好意思啊!
中国当代社会史首要任务是深入细致地呈现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再现人们平凡而真切的生活时日,其次是在相邻学科的碰撞中寻找阐释问题的理论和角度,针对当下社会问题,给予历史的分析和判断,惟其如此才能在学术交流与整合中显示其应有的学科地位,并避免曾有学者批评的,由于一味地迎合社会学“导致社会史变成了‘社会学’的‘历史投影’。
”[10]碎片化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它实质反映出的是,如何处理微观个案研究与宏观整体洞察,展示历史细节与运用理论分析的关系问题。
口述历史的研究实践证明,这两者不仅不是相互矛盾、不共戴天的,而且只有既兼顾又结合,才能够结出好的成果。细节是历史的血肉,没有细节历史势必显得空泛,但拘泥于细节的堆积或利用细节肢解历史,就难以给人以历史整体感,甚至误导人们对历史本质的认识。
从细微处着手和切入,时时牵引和昭示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背景,最终落脚于对历史原因、经验和规律的把握,这才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该做和必须做的工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三、多学科交叉印证: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度拓展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历史被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医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所应用,虽目标指向各有不同,采写手段同中有异,但“抢救活史料”的客观效果却为多角度的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和分析文本。
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好比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科学面前,历史的地位本质上是寄生式的。历史学家借用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协助我们理解过去。”“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理论的史学作品不断拓宽、加深了历史探索的范围,于是史家以往不曾考虑的问题浮现了,而过去一直忽视的主题也纷纷跃出。
”[11]这种判断对当代社会史研究来说可谓恰切适宜,也就是说,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口述史制作,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涵,滋养了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社会学视域下的口述史最为典型的是,孙立平和郭于华共同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此项研究已经进行了十余年,他们先后在华北的西村、陕北的骥村、东北的石湾和西南的柳坪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工作,在搜集到的大量民间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记录了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形态,揭示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乃至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乡民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这些经历的感受、记忆、讲述和理解。
这项基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口述史研究,突出了社会史研究的两个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正如研究者所言:“既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妇女都是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参与者和重要动力,她们当然也应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言说者和解释者。
然而,在正式的历史和革命史记述中,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她们的所思所想,她们的记忆和讲述却往往无声无息,她们的故事成为一种历史中视而不见的缺失。
她们没有历史,或者至多只有由他人代言的女性历史。”[12]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其深入村落收集口述史料的目的就会发现,他们意在通过“诉苦”这种记忆的追溯,重现“土改”的“真相”,并以此来丰富对“革命”、“斗争”和“社会动员”等理论问题和观念问题的认知与理解。[13]
与上述研究相似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李绍明、王铭铭和杨正文等主持的“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计划”。此项研究2006年10月启动,调查地点集中在“藏彝走廊”地区,主要针对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通过口述史的形式访谈了10位曾经参与或亲历“民主改革”的老人。
他们当中有西南地区第一批民族研究者,有亲历“民主改革”第一线的民族工作者,有参与“民主改革”决策的政府官员,有当地头人的管家,还有曾经在当地土司与人民政府之间担任翻译工作的人员,以及经历过“民主改革”的喇嘛和一般百姓。
口述史之所以成为必要,就在于“关于‘民改’的起因、过程、结果,正式的文字记载至为大而化之,未能充分展现这个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活生生的历史动态’。
而侧重于口述史,也使我们能够将一个历史大事件放在不同人物——如土司、民族学家、工作队员、士兵、干部、商人、百姓——的人生史中考察,从其在人物人生史中的地位,来反观‘民改’的历史相貌。
”其更为深层的诉求在于,要想真正理解“中国这个包含不同社会的社会”的空前变局,“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是根本。”[14]
如果说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意在破解历史真实之“相”,那么由首都医科大学师生完成的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15]则直指赤脚医生现象对当前首都农村卫生工作的启示。从1965年冬天开始,北京共为各郊区县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培训了5000多名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70年代京郊“赤脚医生”已达到1.
3万余人,为农民提供防病、治病、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服务,直至1985年,卫生部开始对赤脚医生进行业务考核,改称“乡村医生”。
这项研究通过现场调查、人物访谈等方法,从卫生部门管理者、赤脚医生和受益群众三个层面,反映了当时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卫生管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行医和教育培训、医患关系,以及有关的社会政治背景、经济制度和村落文化。
其价值不仅在于回顾与梳理了赤脚医生在我国医疗卫生史上书写的奇迹,更在于可以透过这被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为当前探索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上述几例虽专注于各自学科命题的解读,但其生动、细腻的口述史资料无疑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宝贵资粮,它们不是散落于民间的可有可无的片段故事,而是承载了共和国生命历程的集体记忆。这些基于对某一区域或多个个案细致、完整、全面的记录,蕴含着带有普遍意义的当代社会变迁问题,也是社会史可以参与多学科讨论对话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依据的前提和基础。
口述史的实践证明,迈向田野、问询民间是当代社会史研究获取史料、开掘研究问题、理解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
当代社会史虽时间跨度不长,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只有把这些从日常起居到社会心理,从民风民俗到社会结构的巨变都如实记载和深度诠释,中国当代社会史才真正是人民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发挥史学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
正如英国社会史学家塞缪尔(RaphaelSamuel)所说:“社会史的活力在于它关心的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着眼于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权贵名流,侧重于日常事物,而不是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
”[16]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口述历史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的重要基石和源泉,因此,充分开发和利用口述历史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必然选择。













![王铭铭格尔茨 《裂缝间的桥:解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王铭铭)扫描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2/66/266ea9f25632d56bef8ed77caf313328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