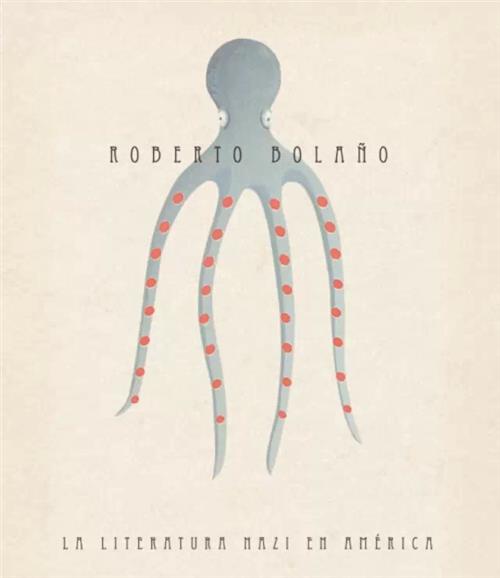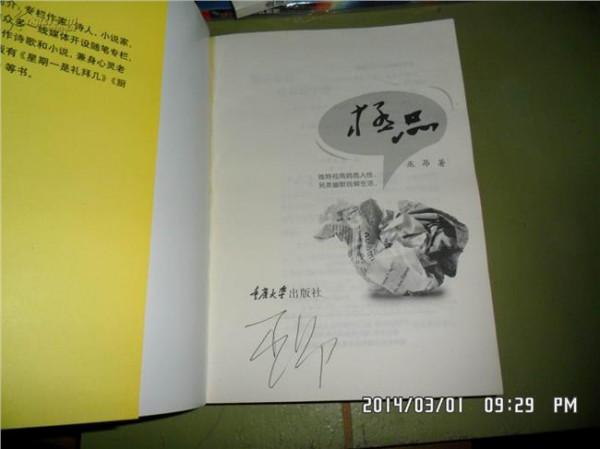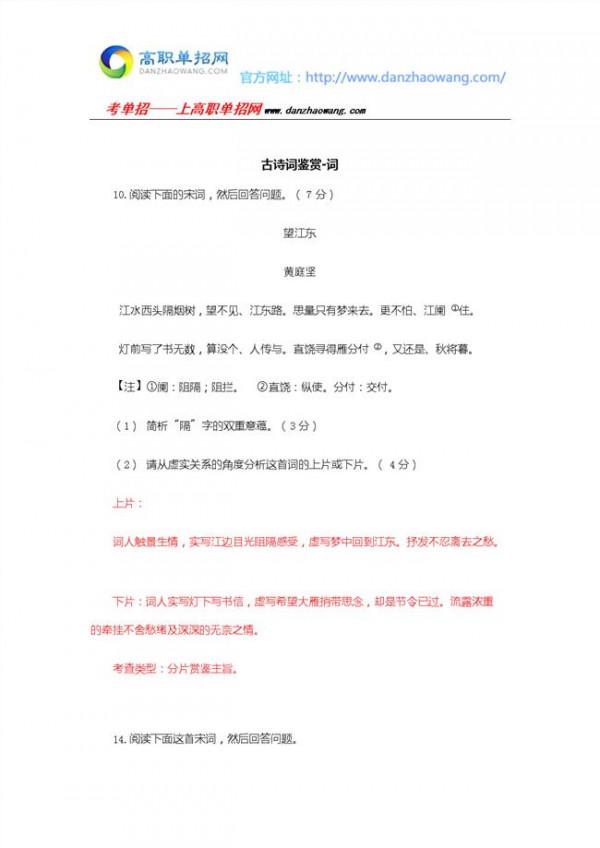巫昂的诗歌 朵渔:巫昂 被伤害的历史 ∣《文学青年》巫昂专号
在巫昂学习写诗的最初的岁月里,她的诗像雨后的蘑菇一般,以一天四五首的速度拥挤着钻出地面。那个时期她的诗作是那样的阳光灿烂,并且带有乡村生活特有的那种青草的痕迹。这种最初的创作,就像“初学时的口哨”--“欢快地、自娱自乐地表演自己的技艺,一遍又一遍,忘我而不知疲倦”。
这种凭窗写作的姿态持续了大概两年左右,她写下了上百首诗歌,我甚至没有勇气读完。如果读完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写出一句话。她写得太多了,我们能体验到她书写时的急促,但是没有一点用力的痕迹,轻松随意,像是用左手随意写下的--一幅漫不经心的样子,从不给自己定下某种“作战计划”,“甚至带着些许鄙夷”。
这个时期,和她一本正经地讨论诗歌,似乎是件困难的事情。她自己总结自己的写作方式时说:“喝了大杯的茶写,在阳光底下写,一睡醒就写”。“一位专业诗人的业余写作”,很符合她这个阶段的写作心态。
“美是浮在世界表面的尘埃吗?”巫昂早期的诗作在反复做出这样的提问。她此时的诗飘浮、温润、通透,她的书写如鱼得水般自如,毫不节制,但奇怪的是,读起来却体会不到阻碍,没有一点挂饰物的感觉。在她一些最优秀的短诗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满足,一种平衡感。
“奇怪的果子/长满眼睛的果子/你吃它/它看你一眼/你亲吻它/它又看你一眼/你丢弃它/它最后看你一眼”(《最后一朵》)此一时期,巫昂更倾向于对静态事物的偏爱,而拒绝一切令人不安的、低沉的、嘈杂的声调。在对经验的处理上,她此时更多的依靠寓言化和诗里的幻想性。她在这个时期已经拥有诗歌观念的自觉和诗歌语言的成熟。
巫昂没有明确的学艺史,她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先是用语言来推动自己,然后再加入少量的自传材料。她的一部分诗歌技艺似乎是从散文中得来的,有一种散步般的精致与散漫。她写得诚实,质朴,没有明显的焦虑感,因此,这也使她避免了许多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学艺的青年诗人经常会染上的坏毛病。
她的诗作与她的早年生活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她有过一段乡村生活,她研究过蜘蛛织网,她听到过“蚯蚓鸣叫”,她留意过三角梅般的石阶上的青苔。这些在她早期的诗作里很容易读出来。“午后,四下里静悄悄/出差归来的蜜蜂/回到久别重逢的花朵/怀中”(《午后,四下里静悄悄》)“林中水浅的地方/鱼少女在那里居住”(《林中游记》)。
还有一种自传材料,被她用一种圆熟的技巧进行了巧妙的伪装--她对早年的家庭暴力的记忆。她这种隐藏很深的自传性质,就像鱼鳞在沙中闪光,你意识到了却很难捕捉到,这需要借助于她数量可观的散文、小说、札记来破译。
早年的家庭暴力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经历过因赌博引起的家庭暴力,这使我在日后对任何形式的博奕与冒险都不再感兴趣;巫昂见证过另一种暴力,母亲因不堪忍受父亲的暴力,带着她姐弟二人住进了医院的一个小房间。这样的经历不仅仅影响着她对男人世界的看法,更深刻改变了她对待女性自身身体的态度:
凡是我所爱的人
都有一双食草动物一样的眼睛
他注视我
就象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
--《凡是我所爱的人》
对“食草动物”般的男人的偏爱,这在她的日常的个人生活里一再得到验证。而对女性生殖的多次描写,也可以看出她早年生活的烙印,“妇女病”,“我失去了一个孩子”等等,血腥,暴力,甚至有些残忍。生殖对一个女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摧毁性的(毕加索说他从不与“和别的男人生过孩子的女人上床”),可怕的是,巫昂过早地接触了这个残酷的主题。
巫昂对个人经验的处理很老道。虽然是暴力经验,她也是用一种蜘蛛织网般的笔调在写,努力在个人精神和早期家庭生活现实的可怕压力之间保持着“快乐的平衡”。她从来不会对文字使虐,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书写者被文字围困,形成一个语言的硬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