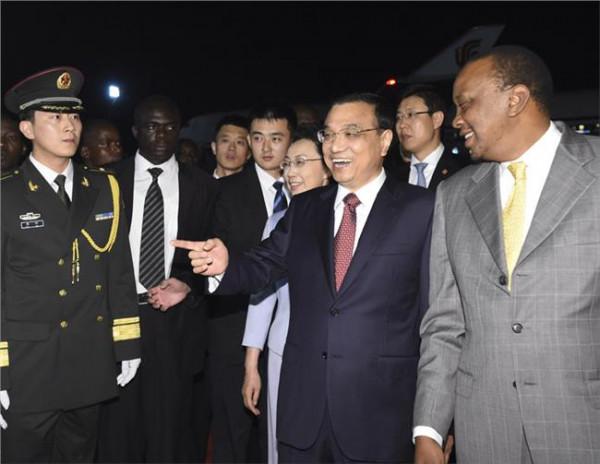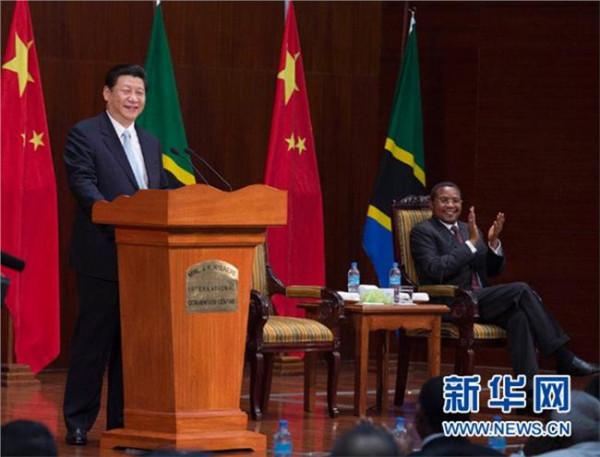邱兴隆人品 邱兴隆:国际人权与死刑
将死刑问题与人权相联系,是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人权运动发展的一个耀眼的亮点。在这半个世纪中,国际人权运动在死刑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由放任到限制再到废除的转变。具体说来,假如我们把《世界人权宣言》的出台作为当代国际人权运动的肇始,那么,在这一运动的初期,无论是国际人权文件还是国际人权学界抑或是国际人权活动,在死刑的合法性问题上,均是三缄其口。
而这实际上是以沉默来显示对死刑的放任。然而,在这种局面维持不到20年后,国际人权运动对死刑问题已不再在沉默中镇静,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组织对死刑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最终促成了限制死刑的条款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的出现,以及后来的诸如《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之类进一步限制死刑的国际文件的产生。
以此为表征,国际人权运动对死刑的态度由放任转向了限制。而限制死刑的精神在国际人权文件中的得以确认,并未使国际人权界对死刑的不满得到平息,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鼓舞、促成与助长了这种不满,在“死刑是对作为犯罪人的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侵犯”的口号下,国际人权界迈出了要求彻底废除死刑的一步,进而促成了《<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第六议定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以及《<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的先后问世,从而使废除死刑成为了国际人权法视野中的共识。
国际人权运动在死刑问题上的态度因此而由限制转向了废除。
本文拟以国际人权法中的死刑规范为线索,展示国际人权运动对死刑的态度的这一演变过程,剖视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图为完善中国的死刑制度找到一个参照。
(一)《世界人权宣言》对死刑的放任及其原因
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死刑问题上的沉默是显而易见的。这最明显地反映在《宣言》不但没有提及死刑问题,而且,不包括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死刑相关的条款。尽管《宣言》第三条将“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作为人的三大基本权利予以了确认,也尽管其第五条规定了“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但是,从《宣言》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来看,这里所说的人人所享有的生命权是不适用于应处死刑的犯罪人的,而这里所禁止的“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刑罚”也并不包括死刑。
因为一方面,《宣言》的颁布与钮伦堡军事法庭以及远东军事法庭对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审判相隔不久,此二军事法庭都对重大战犯毫不犹豫地判处了死刑,而《宣言》的发起国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亦即二战战犯的命运的决定者。
很难想象,刚刚代表国际社会施加了死刑的这些国家,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后便通过《宣言》宣告死刑侵犯人的生命权或者是残酷、不人道的刑罚。
另一方面,在《宣言》通过前,全世界仅有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在《宣言》通过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只有极个别的其他国家采取废除死刑的行动,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人权委员会创始国在当时很少有不保留有死刑的。
因此,同样难以想象,这些国家在国内法上保留死刑的同时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宣告死刑侵犯人的生命权或者死刑属于应予禁止的残忍或不人道的刑罚,或者在作出这样的宣告后,对于国内法上所保留的死刑无动于衷。
《宣言》对死刑所持的是放任态度,也为随后产生的《欧洲人权公约》所印证。该《公约》第二条在确认“任何人的生存权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规定“不得故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但法院依法对他的罪行定罪后而执行判决时,不在此限”。这里的“但书”实际上是确认了死刑的合法性。
既然作为国际人权大宪章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死刑问题上保持沉默,受其指导的国际人权运动在其之后的10多年的时间中对各国死刑的适用持相应的放任态度,也就顺理成章。正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我们没有见到与死刑相关的任何国际文件,而且也几乎没有听到过对死刑不满的呼声。那么,国际人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在死刑问题上为什么会持沉默与放任态度?至少,可以从如下数方面来分析其原因:
其一,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世界人权宣言》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理解为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其二,罪犯的人权范围尚不确定。在《世界人权宣言》产生前乃至在其产生后一段时间,罪犯的人权没有受到国际人权界的专门关注。
其三,对生命权的特殊保护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生命权具有不同于人的任何其他权利的内容与意义。原因在于,生命是人的一切权利的载体,而生命权是人最高的权利。虽然生命权的这种特殊性自古以来便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否则便不可能有诸如“生命神圣”之类的说法,但是,《世界人权宣言》并未突出生命权的这一特殊性。
在《宣言》第三条,生命权与自由权以及财产权被同样确认,尽管在排序上生命被列在首位,但是,这样的排序并不足以意味着对生命权的特殊保护。
自由刑与财产刑在当代刑罚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动摇,而生命刑却倍受责难,原因正在于生命权具有不同于自由权与财产权的特性。而在这种特性没有得到重视之前,国际人权法自然不可能将死刑作为排斥的对象。既然《宣言》没有一般地突出对生命权之不同于自由与财产权的保护,当然不会产生为强调对罪犯的生命权的保护而排斥死刑的实践。
其四,排斥死刑的国际气候尚未形成。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与国际人权法的创制,离不开国际社会大气候的要求。在死刑问题上也是如此。只有当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国家对死刑形成了一种排斥态度之时,国际人权运动才有可能提出并实现排斥死刑的方针,国际人权法也才可能就死刑作出相应的排斥性的规定。
假如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尚未形成排斥死刑的态势,国际社会便不可能产生排斥死刑的要求,而国际人权运动便很难提出排斥死刑的方针,即使提了出来,也难以付诸实施。
事实上,《世界人权宣言》通过时,不但没有形成排斥死刑的国际气候,相反,死刑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正在受到重视。如前所述,至《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之时,全世界只有7个国家完全废除了死刑,而且,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南美洲(5个),并均系对国际社会影响不大的小国。
因此,无论是从对死刑持排斥态度的国家的数量来看,还是从它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来看,都不足以成为一股势力,更不可能对国际人权运动与国际人权规范形成大的影响。
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当时不但在数量上占压倒多数,而且,对国际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国家均在其列,尤其是《宣言》的所有发起国与首批成员国几乎无一不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两相对比,《宣言》通过前后,对死刑不采取排斥而采取放任态度,便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结果。
(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相关的国际文件对死刑的限制及其原因
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18年,即1966年12月16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应运而生。尽管差不多整整10年以后即直至1976年5月23日它才正式生效,但是,无疑,自它产生之日即标志着国际人权运动对死刑的态度不再是沉默而是转向了限制。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刑的限制集中体现在其第六条的规定,具体表现在如下数方面:
1.强调生命权的特殊性,突出对生命权的特殊保护。《公约》第六条第一项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这一规定相对于《世界人权宣言》关于生命权的保护有了明显的加强。
一方面,它明确了生命权是人人所固有的权利,强调了生命权的与生俱来性。“固有的”一词,英文为inherent。而inherent不只具有“固有的”之意,而且同时也指“内在的”、“与生俱来的”。
所谓内在的,当然是指非外界所赋予的,而所谓“与生俱有的”,无疑指的是人一旦出生为人便拥有的。因此,将生命权视为一种固有的权利,实际上是强调生命权的自然性与神圣性,亦即不得人为地剥夺的属性。在《公约》所保护的诸种权利中,唯有生命权被冠之以“固有的”字样,而其他任何权利诸如自由、财产等等,无一有这样的限定词。
对生命权的这种不同于其他权利的属性的强调,构成国际人权法对生命权的保护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如前所述,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生命权只是被与自由权及财产权置于同一序列中予以保护,没有被冠之以“固有的”的定语而突出其不可人为地剥夺的属性。
另一方面,强调了对生命权予以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严禁任意剥夺人的生命。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对生命权的保护仅限于对人人享有生命权的确认,而没有就关于生命权的保护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与此不同,《公约》则明确强调生命权“应受法律保护”,并进一步强调了“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从而将对生命权的保护摆在了极其醒目的位置。
不仅如此,《公约》还将对适用死刑的具体限制与对生命权的保护同列于一条之中,因而将生命权与死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等于宣告了凡不遵守本条的限制而适用的死刑,在国际人权法上便构成对生命的任意剥夺,直截了当地说,便是对生命权的一种侵犯。
2.将死刑的适用限于最严重的犯罪。《公约》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这实际上确立了适用死刑的一条大致标准,亦即界定了死刑的适用范围。据此,只有对最严重的犯罪施加的死刑才有可能是正当的死刑,而对任何非最严重的犯罪施加的死刑则构成不正当的死刑,亦即构成对人的生命的任意剥夺。
3.从追诉时效的角度将死刑的适用限于行为时的犯罪。《公约》第六条第二项还规定,死刑的“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的法律”。根据这一规定,只有按照犯罪时有效的法律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才有可能适用死刑,任何犯罪,如果在犯罪时有效的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即使犯罪后生效的法律规定可以判处死刑,也不得被判处死刑。
这实际上确立了死刑不得溯及既往的原则。在国际人权法的视野内,溯及既往的死刑无疑意味着对生命权的侵犯。
4.授予死刑的受刑人以赦免或减刑请求权。《公约》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大赦、特赦或减刑”。这是一个授权性规范,授予了被判处死刑的人以请求赦免或者减轻的权利。同时,该项还规定,“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
这同样是一个授权性的规范,授予了国家通过赦免或者减刑而免除死刑的权利。虽然该项不是排斥死刑的硬性规定,即没有要求国家对每一请求减免死刑的人都予以减免,因而不可能绝对导致死刑的免除,但是,它毕竟树立了国家可以减免死刑的导向,对于减少死刑的实际执行具有积极意义。
5.严禁对未成年人或孕妇实施死刑。《公约》第六条第五项规定,“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于孕妇不得执行死刑”。按照前半项,任何人,只要其在犯罪时未满18岁,便不得被判处死刑。而按照后半项,只要是怀孕的妇女,即使被判处死刑,也不得予以执行。这是从犯罪的主体或者说刑罚的对象的角度对死刑的实施的限制。鉴于该项对死刑的排斥具有绝对性,其对死刑的限制作用不言自明。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以上限制死刑的精神与措施,得到了《美洲人权公约》的认同与发展,并得到了《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等国际文件的重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