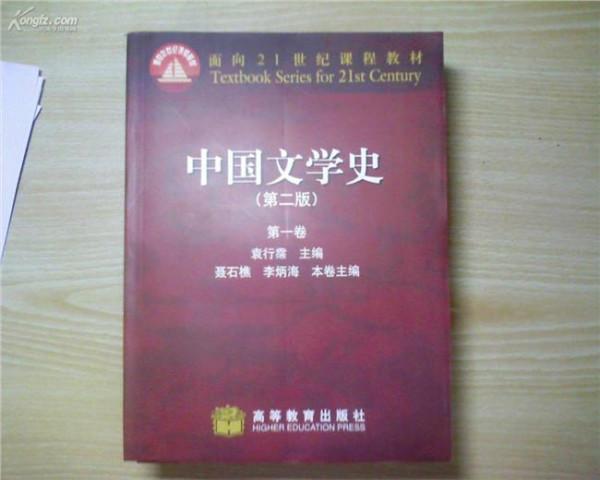三言二拍中男女變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
中國婦女不論是在歷史洪流或是文學作品中,一直在男性霸權文化之規範與逼迫下,扮演著屈從與次等的角色,絕大多數的女性一以未有受教育的機會,故不得智能之發展,進而掌握文字與知識為自己發言;二以未得經濟自主權,故而需依附在以男性為合法繼承人之宗法制度之下,一生在從父、從夫、從子的過程中日漸凋零而無法擁有自主之生命,這其中更隱含著色衰愛弛、不能生子等七出[1]的危險,又有時局紊亂父可鬻女(如竇天章賣竇娥抵債)、夫死婦當守節(如魏代曹令女,夫死以截耳斷鼻的方式拒絕改嫁)等意外…,婦女之生命隨時處在無法自知並掌控的狀態當中,幾千年來的「男尊女卑」、「夫主婦從」模式一直重複地犧牲耗弱佔二分之一人口的婦女生命,此種現象要到清末民初之際因西風東漸才又有了重新反省的契機。
古代婦女之困難處境與從屬地位自不待言,而在中國嚴密的宗法制度社會下,男女之分際與身分地位之認同是極為清楚的,簡言之可化約為「宰制-受制」模式,故一般觀念裡男子得以身為男兒自豪,女子則多以身為女兒自卑,這是一種天生的不平等,男女性別的孑然分立與隨之而來的不同社會規範在儒家禮教千年來的教導與浸染下,早生根成一種文化的深層結構而難以撼動,更已內化成中國人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的集體文化基因與道德規範準則。
宗教用以安頓生命,其經典中的祝願祈求可說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深層願望了,在唐朝的《藥師經》[2]中藥師佛行菩薩道所發出的十二大願,對於來世的期盼除了「智慧無邊」、「端正黠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外,第八大願為「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百惡之所逼惱,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證得無上菩提。
」對於女人來說,今生今世的「百惡之所逼惱」,只能虔誠地燒香拜佛以求來世轉生為男,才得脫離苦海,證得無上菩提!
雖說如此,現實人生的諸多險惡,有時也會有藉由喬裝打扮而改變性別、身分者,其裝扮變身的目的為何?不同的性別裝扮又引發出什麼樣的結果?如果說男女變裝是一套文化符號的改變,人們認同的實際上是一套顛撲不破的符號系統網,在本文中即「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權力結構關係,而不管文化符號背後真正的性別事實與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與能力?本文擬以文學文本明代馮夢龍所編纂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與凌濛初所著「二拍」(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作為觀察的出發點,希望藉由男女變裝的文化解碼,來剖析解讀「男尊女卑」、「男主女從」這一套運作千年的符號系統。
本文擬以女性主義的「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觀點做為全文的切入點,並輔以符號學理論對於男女變裝提出論述與辯證。
《性別政治》是卡特米列(Kate Millett)的博士論文,於1969年出版,此書的出現確立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地位。米列的主要觀點為「性即政治」,男女關係一如政治當中結構性的權力關係,是一種「宰制-受制」、「統治-從屬」的關係。
米列進一步定義性政治為:「統治的性別嘗試將其對從屬性別之權力維持及伸展的過程。」[3]在中國,宗法制度就是建構「父權制度」的依據,其確立「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性別政治,更藉由不斷社會化、性別角色刻板化的過程,使男/女不僅服膺接受,更將統治/從屬的社會分工內化為意識型態。
而服飾,是一種非語言的文本,它可說是符號學中的「二度體系」[4],它建立在可被語言解釋的基礎上。服飾,更聯繫著該文化的釋意方式與價值規範的體系,如「喪服」中的「五服」[5]不僅規範著生者與死者間的宗法關係與血緣親疏遠近,更有服喪時間長短的區別;「被髮左衽」、「斷髮紋身」在中國文化系統中被解讀為蠻夷之邦無文化之人;「左衽」在日本文化系統中則規範著死者穿和服的方式;「披髮」已成為當代不分男女的蓄髮自由,較難讀出其中的文化意涵;「紋身」是某些原始部落的美體方式,在當代台灣又成了青少年追求時髦的價值呈現。
那麼男扮女裝、女扮男裝在一個古代中國「男尊女卑」的社會裡又分別呈現出什麼樣的文化意涵呢?男人何以放棄相對於女性較高的地位與身分,屈就扮女?女人又在什麼樣的刺激或情況下必須謹慎扮男?本文將對三言二拍中的男女變裝相關篇章做一深入的比對觀察,期能建構出男女變裝背後之性別與文化意義!
中國早在周朝就形成了宗法制度,並從而確立了上下階級與內外之分,而如此鮮明的階級意識更是藉由典章制度來彰顯其內容,上自國土分封[6]、祭典儀式[7]、居處宮殿,下至日常座車、衣著服飾等無不規範謹嚴而不得任意僭越,所謂: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8]
中國之統治階級創造出嚴密的符號系統來填充其宗法制度,更透過這一套符號系統來強化統治者的穩固地位,並從嚴控管低下階層對此符號系統的顛覆。可說中國人千年來都是活在宗法階級的「符號系統」規範下!
正因為中國人的符號系統鮮明,男女性別之分際在《禮記》〈曲禮上〉即已規定得極清楚: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以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十三經注疏-禮記》,頁37)
又〈內則第十二〉則規定男女內外之別: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十三經注疏-禮記》,頁520)
故而男女有別,男主外而女主內,各司其職而不可隨意跨越。而影響著男女地位之高下者,尤以〈郊特牲〉中所言之三從為最: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以知帥人者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十三經注疏-禮記》,頁506)
因丈夫在知識(知)上與經濟(爵)上之自主發展得以為婦人之帥,由此則宰制者與受制者,統治者與從屬者的權力結構已由經典制度清楚劃分區別,男女地位因此被規範在「男主女從」、「夫為妻綱」的系統底下。
此外,中國冠服制度可說自《周禮》、《儀禮》已臻完備,其與階級制度相互對應,互相說明,不論在款式、布料、采色、文飾或形制等方面都有清楚而嚴格的規範[9],歷代亦有所增刪。若舉三言二拍之成書年代-明代的服制為例,則有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禮服、文武官員常朝之服、及士庶階層的巾服等種類,又規定「不許官民人等使用蟒龍、飛魚、鬥牛圖案,不許用元色、黃色和紫色,不許私穿紫花罩甲等」[10]。
而明代平民[11]男子多戴巾帽,穿袍衫,著鑲鞋;女子則頭梳髮髻,或紮巾包頭,穿團衫外罩背子[12]、比甲[13],下裳多穿裙,自宋以降則纏足之風盛行。可見男裝、女裝之搭配也是各成系統,不相雜次混淆。
「服裝」(包括男裝和女裝)可說是一種純粹制度化、標準化的準則,一如語言學中的「語言」(langue);而「裝扮」行為則是一種個人化、實踐化的穿衣過程,可對應於「言語」(parole)[14]。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以為:
語言是一種制度,一個有所限制的抽象體。言語是這種制度短暫的片刻, 是個人為了溝通的目的而抽取出來並加以實體化的那一部份。[15]
若對應著服裝來思考,在古代中國「服裝」是一套統治者制定的冠服制度,它是一個有所限制的體制,並以辨識身分為目的,表現在服飾的圖案、顏色、形制上而有諸多專屬或禁制。而每一次的「裝扮」都可說是冠服制度實際執行的過程,即個人在社會活動時將其抽取出來並實體化的那一部份,而對外「溝通的目的」就是讓觀者辨識出裝扮者之身分、階級與性別。
以此論述邏輯推理,則「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正是裝扮者有意的以服裝制度為前提,並藉由裝扮進行掩飾性別事實並達到對外溝通的目的。
當社會之權力結構、處世規範與冠服制度等緊密交織成文化符號網,即社會性別(gender)[16]一如符號學中的能指(signifier),而價值、規範一如所指(signified)時(見圖一),則天生為男則享「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不幸而為女,則「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17],生理性別(sex)隨即必當服膺社會性別的價值與規範。
生理性別 社會性別 價值、規範(依時代而有不同內容)
男 → 男 弄璋;主,外,尊,讀書仕進,…
女 → 女 弄瓦;從,內,卑,忠貞節烈,…
圖一 性別與文化符號系統的關係
性別上的天生不平等,因為能指與所指間頑固而緊密的連結,故只能等到下輩子才能祈求翻身了!此世翻身既不可能,更無進步的醫學技術可提供變性的要求,故而偶爾的謹慎變裝倒成了或可一試的變性方法,不管其目的為何,然而藉由變裝可進行性別符號的對置(男變為女,或女變為男),也可達到身分改變的效果。
原本被視為當然的生理男性(或女性)服膺社會男性(或女性)的價值或規範(見圖一),經過男女變裝之後,外在的辨識系統因為被顛倒錯置了(見圖二),一則掩藏起生理性別的事實,二則刻板的性別價值與規範也跟著鬆動了,不論男女忽然可以易位思考。
進一步說,「變裝」的意義即是撤換掉原本加諸個人的符號系統,如性別、階級、身分地位與隨諸而來的處世規範與禁忌等等,而變裝後即意味穿戴上了另一套文化符碼以供他人辨認、解讀,除能避開原有身分之窒礙難行外,新身分更帶來處世行事之方便,變裝人得藉此達成一己之宿願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