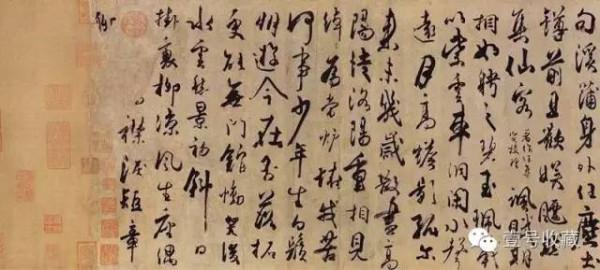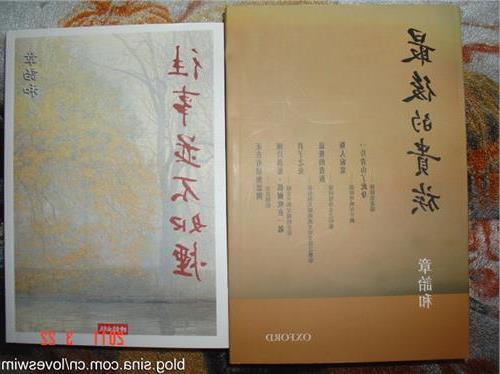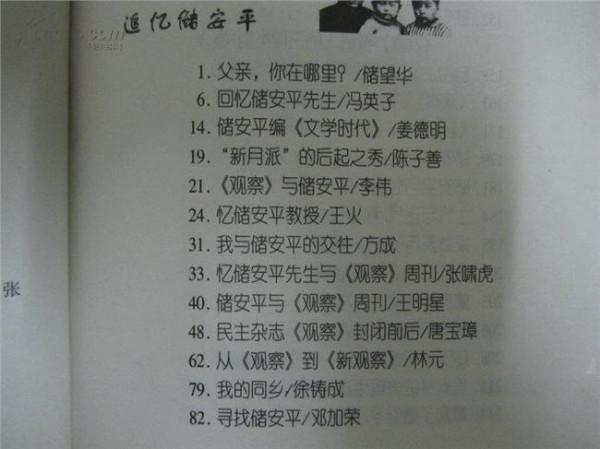章伯钧章士钊 章诒和:储安平与章伯钧
要我劝劝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热血沸腾。父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倍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而中共则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
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
真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负戈前驱,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其实,激荡浩淼之风华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学识,已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在他们的身后,也已是枪弹飞越,飕然有声。
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父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父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父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父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父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父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论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政府的文章。”
父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中国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⑽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父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激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父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汇”与“光明”血脉相通,都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父亲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身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党。
6月10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日一大早,父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日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去之前,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父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
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国家内部党与政,党员与官员之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这么一种关系,的确少见。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
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告密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
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恶风扑面,惊雷炸顶。整个形势在这样一群书生眼前,变得狰狞恐怖。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
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中央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
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领导人的许德珩、孙承佩,“光明”的负责人常芝青,还有九三学社里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裴文中、薛公绰等也纷纷表态、亮相。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