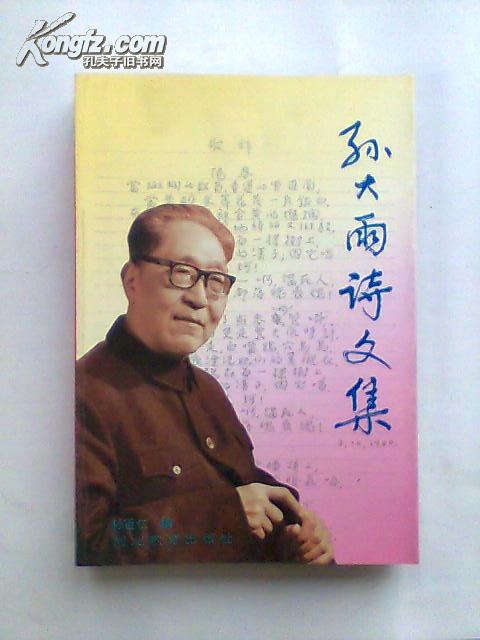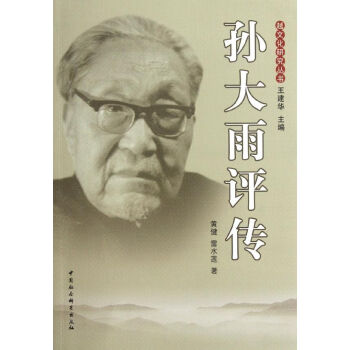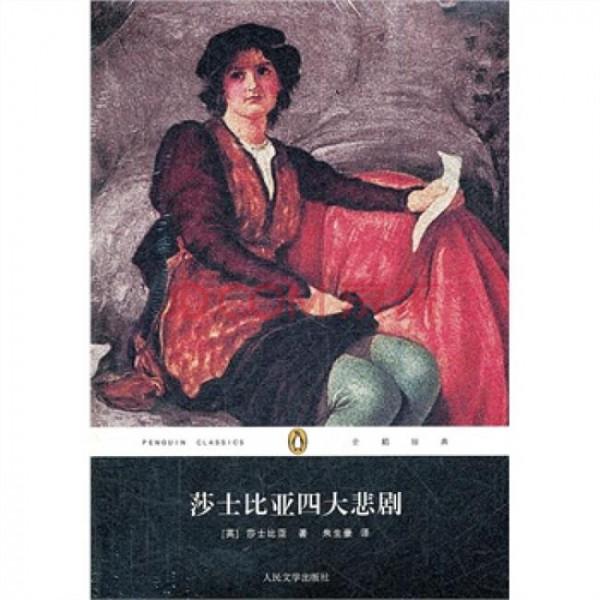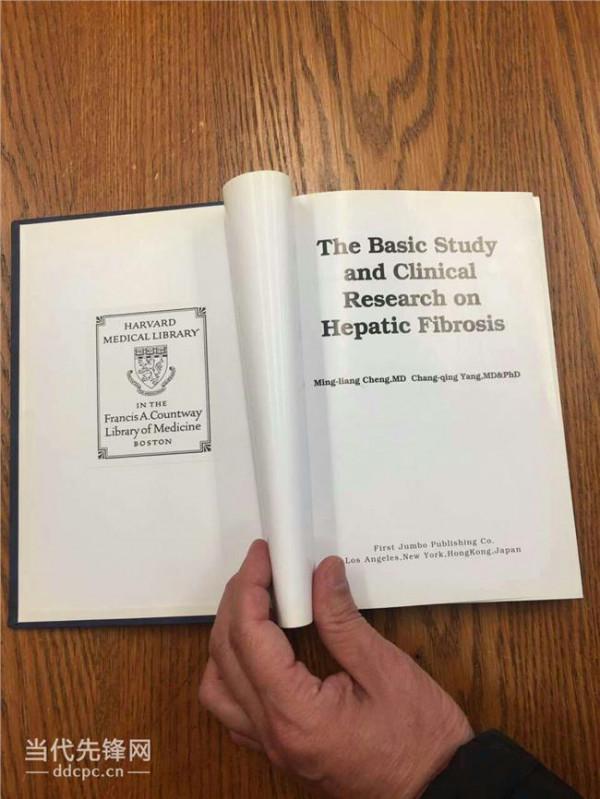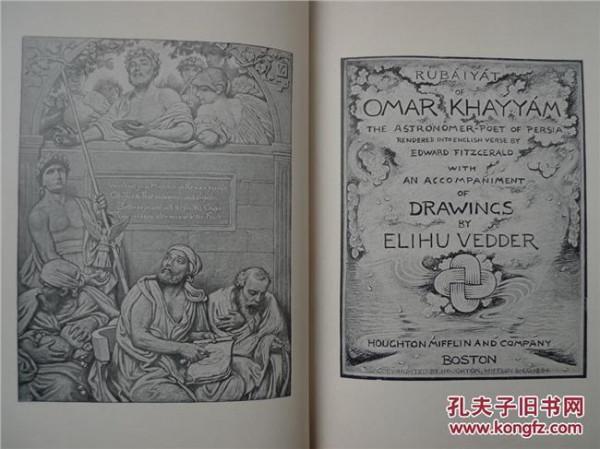莎士比亚孙大雨 盘点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中国牛人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除了早期创作一些诗歌外,主要作品是戏剧。一段时间里,学界认为莎剧共有37部,后经考证新增3部(《两个高贵的亲戚》《爱德华三世》《一错再错》)。
就艺术形式而言,莎剧主要是诗剧,台词主要用无韵诗行写就,同时兼用散文,剧中夹有短歌、小曲及剧中剧的韵文。莎士比亚是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但首先是独步千古的语言大师。换句话说,是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予了莎剧不朽的生命力。
有论者指出:“任何人想在翻译上达到顶峰,准想翻译几个莎剧。”此说不免绝对,但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想翻译几个莎剧”者从来不乏。在莎翁诞辰450周年之际,特对其戏剧之部分中国译者及相关译作简作钩沉。
自20世纪初以降,翻译一直是莎士比亚戏剧进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早在1903年,上海达文社即曾出版《英国索士比亚澥外奇谭》(下文简称《澥外奇谭》),译出莎剧故事10个;1904年,林纾与魏易合作译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下文简称《吟边燕语》),包括《肉卷》《铸情》等莎剧故事20个。
上述二译本皆为兰姆姐弟(Charles and Mary Lamb)所着《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之故事梗概。
《澥外奇谭》译者不详,其影响也有限。《吟边燕语》在莎士比亚中译史上的作用当不可小觑。在该译本序言中,林纾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等进行过言简意赅的描述,他说:“英文家之哈葛得,诗家之莎士比,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莎氏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然证以吾之见闻,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余老矣,既无哈、莎之通涉,特喜译哈、莎之书。
”《吟边燕语》出版后,学界嘉评不少。
郭沫若赞其为“童话式的译述”,并让他既感到“亲切”又“感受着无上的兴趣”。王佐良更指出:“许多人是通过这个译本首先接触到莎士比亚的艺术的,而且长远保持了深刻印象。”值得补充的是,林纾说自己“特喜译哈、莎之书”,除了《吟边燕语》,他与陈家麟还曾于1916年联手译出好几个莎剧,包括《雷差德记》《凯彻遗事》《亨利第四纪》《亨利第五纪》及《亨利第六遗事》,译文同样是相关原着的故事梗概。
林纾对莎剧的翻译不无开创之功,但其笔下的莎士比亚还仅是“西方大陆上一位神奇超凡的故事大王”,真正意义上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出现尚待田汉、梁实秋和朱生豪等人的跟进。“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学成为我国文艺的主流,莎剧的介绍与翻译于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直接根据莎剧用白话翻译的散文体译本。
这方面,田汉可谓第一个吃螃蟹者,分别于1921年和1924年译出《哈孟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田氏说自己志愿选译莎剧,其根由如下:“莎翁的人物远观之则风貌宛然,近视之则笔痕狼藉,好像油画一样。”
梁实秋是我国声名远播的莎士比亚翻译大家之一。梁氏曾这样“总结”《莎士比亚全集》译者所需条件:“一是其人不才气,有才气即从事创作,不屑为此。二是其人无学问,有学问即走上研究考证之路,亦不屑为此。三是其人必寿长,否则不得竣其全工。
”这一说法自有几分调侃意味,因为梁实秋本人即“才学两优,译作兼行”。至于“必长寿”云云,读来更有几分不尽之思,因为梁氏1930年着手翻译莎剧,而一直到1967年方译竣并出版《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卷,诗歌3卷)。
梁实秋翻译莎剧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忠于原文,虽不能逐字翻译,至少尽可能逐句翻译,绝不删略原文如某些时人之所为,同时尽可能保留莎氏的标点。”对于梁译,余光中有过评价如下:“梁氏的译本有两种读法,一是只读译本,代替原文,一是与原文参照并读。
我因授课,曾采后一读法,以解疑惑,每有所获。”还有一点也值得指出,即迄今为止,梁实秋是我国以一己之力译毕《莎士比亚全集》的唯一人。对此,李奭学慨叹道:“他独力撑起《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那份豪情与毅力,大概只有莎翁本人可以等量齐观,而梁译所处的社会与环境,其实又远逊莎翁创作时的从容。”
朱生豪是我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又一巨擘。1935年春,他开始收集莎剧各种版本、诸家注释和有关资料,同时研究表演艺术,为翻译莎剧做足了功夫。自那以后直到他生命终结的1944年底,虽然时运多艰而又命运多舛,他以一殉道者之精神译出莎剧31部半。
对此,苏福忠不无唏嘘:“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22岁到32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朱生豪翻译莎剧所遵原则如下:“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
”朱译面世后,好评如潮,王元化即曾说:“朱译在传神达旨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不仅优美流畅,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文微妙处,莫不令人击节赞赏,是我读到莎剧中译得最好的译文,迄今尚无出其右者。
”有意思的是,朱生豪本人对其好多译文也有过评说,主要见诸他写给宋清如的信件之中,此不妨摘引些许:“担心没法子保持原来的对白的机警漂亮”(谈《无事烦恼》《如君所欲》《第十二夜》等“三部曲”之翻译);“《仲夏夜之梦》比《暴风雨》容易译,我不曾打草稿,‘葛搭’(这两个字我记不起怎么写)的地方比较少,但不知你会不会骂我译得不太像样”;“其中用诗体翻成的部分不知道你能不能承认像诗,凑韵、限字数,可真是麻烦”(谈《暴风雨》之翻译);“《皆大欢喜》至今搁着未抄,因为对译文不太满意”;“比起梁实秋来,我的译文是要漂亮得多”(谈《威尼斯商人》之翻译);“《风流娘儿们》进行得出乎意外地顺利……似乎我在描摹市井口吻上,比之诗意的篇节更拿手一些”;“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尤其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谈《威尼斯商人》之翻译)。
综而观之,朱生豪对迻译莎剧是自信的,对自己的译文也是满意的。关于朱译莎剧,还有一点也值得指出,即人们往往将其统称为散文体,事实上其中有着大量经典的诗歌翻译。
从上文不难见出,不论是梁实秋还是朱生豪,其在莎剧译介上的成就皆有目共睹,但在不少人看来,他们的译本也还存在着不足,最为要者,是它们都采用了“降格以求”的散文体。相关论者以为,莎剧既是以素体诗为主的诗剧,理想的译本自然应该是诗体。
为着“必也正名乎”之理想,不少译家纷纷一试身手:1929年,朱维基以诗体翻译了《乌赛罗》片段;1934年,孙大雨提出以“音组”移植五音步的素体诗理论并付诸《黎琊王》之翻译实践;1944年,曹禺为成都的剧团上演而用诗的语言译出《柔蜜欧与幽丽叶》;上个世纪50年代,卞之琳、吴兴华、方平等也推出过部分莎剧的诗体译本。
据我们观察,以诗体形式翻译莎剧可谓人心所向。朱生豪虽曾明确反对“逐字逐句”地翻译,但他对每个莎剧中的诗歌却尽量采用诗体试译。
对于以诗体形式传译莎剧,梁实秋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的译文完全是散文……如果能有人把原文的无韵诗译成中文的无韵诗,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我们应当馨香以求。”
在对莎剧诗体译本的鼓与呼中,方平可谓不遗余力。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经过名师的指导,课堂的训练,这文学翻译的路子全凭自己的摸索。”而在多年译莎的摸索中,方氏渐渐酝酿出如下翻译思想:“越是经典名着,它的艺术形式越是应该受到尊重。
尤其是戏剧,属于时间艺术,词序和句列,很有讲究,在翻译过程中不必要给移位了(变动了艺术形式),原来的语气往往因之而变形了。”相信正是因为此,方平这才力主以诗体形式翻译莎士比亚戏剧。
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鼓与呼而且起而行。在他辛勤主译主编之下,一套集数人诗体翻译成果的《新莎士比亚全集》最终于2000年诞生。对于书名中的“新”字,方平有说明如下:“这‘新’就是重新认识莎士比亚”;“以更接近于原着风格的译文,以新的戏剧样式,结合着现代莎学研究成果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争取做到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实践证明,《新莎士比亚全集》确实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感受。
说到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翻译,还有一个人也不能不提,他便是苏福忠。苏氏曾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该社所出朱生豪莎剧译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始终看重,认为其在中国近代英译汉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因为喜欢朱译至极,在竭力呵护与弘扬之余,苏氏还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完善,恰如他在给朋友的邮件中所述:“其实从九十年代起,我就在逐步改造人文社那套全集。
应该说,那套全集还是有水准的,但是历史剧和诗歌,请了七八个译者翻译,是大跃进的做派,译风不统一是自然的,主要是压制了个体行为,和朱生豪一个人翻译那么多剧本,形成很大讽刺。
……其他出版社的版本也是大杂凑,所以我想出一个译者集中一点的版本。”这个“译者集中一点的版本”不久前业已问世,取名《莎士比亚全集经典插图本》(新星出版社,2014)。
该“全集”可谓名副其实,因为本文开首提到的三部莎剧新着皆已纳入其中。至于“全集”的译者,署名为“朱生豪 苏福忠等”,但总共也就三人,苏氏在其中的角色及贡献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