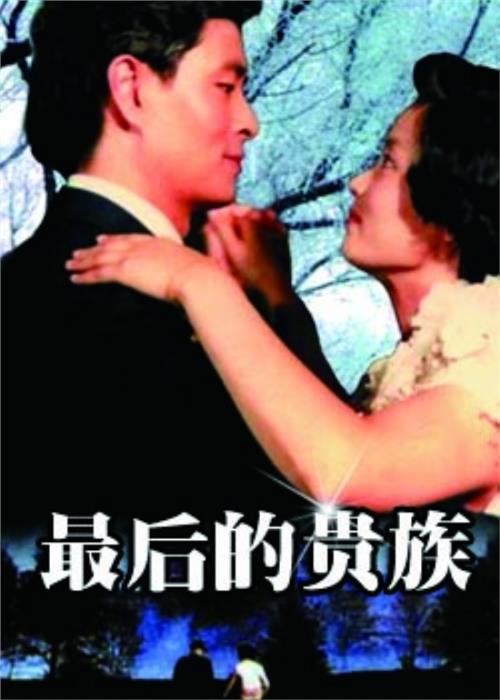陈岱孙的祖父 最后的贵族陈岱孙 zz
有几个经济系的学生们起得迟了,离开课还有一刻钟的时候,他们便已着急的跑了起来,可还是晚了一步,等他们赶到时,整间课室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听众里除了经济系的学生,还有许多外系外班的,他们只得努力挤进去,和那些没占到座的学生们一起恭恭敬敬地站在后排。
这门课叫“经济学概论”,是经济系学生的必修课,并不似文学史那样通俗有趣,反而因为充斥着大量专业名词而显得枯燥无聊,可它居然能吸引到这么多学生,可见这门课的教授极为不凡。
离上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门缓缓开了,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熨烫妥帖的深黑西服和雪白衬衫,俊眉修目,挺拔似临风玉树,他站在台上,微微一笑之间却自有一种儒雅高贵气度,让喧嚣的课室瞬间安静下去。
他不急不缓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有力的英文单词——“wants”(欲望,需求),然后,便从这个词起,他开始讲述人们经济活动的起源,动力,接着再讲效用,供求,价值,他的语言非常精炼,却极端条理清楚,对概念的解释简明扼要,却准确到位,有时候他还会稍加停顿或简略重复要点,方便同学们记笔记。
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他的国语说得极好,字正腔圆,清晰有力,抑扬顿挫间有一种自然的韵律,充满音乐感,让人心旷神怡。学生们也都非常热衷于记笔记,因为他的话记录下来,不必增减便是一篇完整经济学佳作。
有人举手提问,他停下来,很耐心回答问题,不久又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他道:“这么笨?”同学们哄然笑开,他微微扬起的嘴角有一丝善意的笑。
他有着中国传统学者的从容不迫和英伦绅士的细致周密,还有着恰如其分的幽默感,这样的谈吐气派,让他成为了当时联大学生心中的偶像。
这位教授名叫陈岱孙,他是福建福州人,出身于大名鼎鼎的“螺江陈氏”。他的家族在明清两代出过不少进士和举人,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之中曾有六子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传为一时美谈,陈家世代簪缨,有官至刑部尚书,连林则徐也自称其“门下士”的陈若霖,还有清末帝师陈宝琛,他是陈岱孙的伯祖父。
当代陈家也出过不少著名人物,包括海军中将陈庆甲、交通建设学家陈体诚,担任过司徒雷登秘书的陈矩孙等人。陈岱孙的外祖家也非常显赫,他的外祖父,舅父都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陈岱孙的家族可谓人才济济,星月交辉。
陈岱孙是家中长孙,从小聪颖,于读书一事上极有天赋,家人便对他也寄予了厚望,教育极为严格。他六岁入陈家的私塾,国学方面,在祖父的督促下,学习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西学方面,外祖父特意为他请了英文教师,自幼他的英文就很好。十五岁的时候,他考入当地有名的鹤龄英华中学,免修中文课,英文课也可不听课,只参加期末考试,他以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四年的课程,而后,十七岁的他考入了当时极为难考的清华学堂。
清华当时的学制是8年,分中等、高等两科,每科4年。高等科的一一二年约等于高中的二三年级,而高等科的三四年则等于大学的一二年级,他入的是高等科的三年级。清华学堂实行淘汰学制,在校的学生又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优异学生,故而竞争极为激烈,但他凭借天赋和努力,在两年后的毕业甄选中,成功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入读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经济系三年级。
他的博士就读于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哈佛大学,4年后,他如期获得了博士学位,班上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学中,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位,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同时获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尔后,他又去法国定居了半年,旁听巴黎大学的课程,在欧洲各国短暂游历。
他是1926年年底回国的,随即便接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他回到母校,任教于经济系。那一年,他才刚刚二十六岁。
出身世家,少年成才,留学名校,高大俊朗,而且他还颇有生活情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打猎、跳舞,尤其桥牌打得精彩”,这些特点简直是文艺小说中一干男主角的标签,当时的陈岱孙完全符合小说中“王子”的标准。
任教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已经年届不惑,可岁月仿佛更为他添了一分成熟气质,他西南联大的学生任继愈还记得他在网球场上的风采,说“在学校网球场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经常出现。这四位是金岳霖、陈岱孙、赵乃博、浦薛凤。
陈先生风度翩翩,赵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裤褂。他们的球艺很娴熟,特别是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他的翩翩风度,不知折服过多少女子,当时,联大女生在找男友时,都把他当成标准,声称自己要找一个如陈先生一般的人。
然而,他终身未娶。
出生于1900年,去世于1997年的他,独自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
据说,他终身未娶是因为一个女子。
十九岁那年,他与他的同学同时爱上了一位女子,两人相争,又恰逢要出国留学,于是两人击掌为约,谁先得了博士,谁娶其为妻。
这样一个契约,在现代人眼中,幼稚得可笑,可是他把它当了真。那时青春正年少,心中有的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唤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情万丈,赤手空拳,却有决心和勇气打一个天下。更何况,那时的他又岂肯对谁服气,他笃信自己不会输,他会拿这世间最负盛名学府的博士,等他有了坦荡前途,他要回来娶最好的女人。
在美国威斯康新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他毫不犹豫地申请了哈佛大学。在哈佛,他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提出“垄断竞争”学说的张伯伦,有后来获过诺贝尔经济奖的奥林,与他同级的二十多人皆不是泛泛之辈。为在这样强手云集的环境中取胜,他付出了十二分的努力。
哈佛的后两年,在导师的推荐下,他得到了一间位于哈佛图书馆的研究小隔间,从此他可以随时凭证入库,整天呆在里面读书。
他的哈佛记忆,不是古老美丽的校园,亦不是同学间的游乐嬉闹,而是图书馆那间只够摆一张桌的狭窄隔间。
除了本专业必修的经济学著作,他还读哲学和历史,读到累了,他便去图书馆另一层的文学阅览室去,那里有丰富的欧美文学名著。他通常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去文学阅览室,其它整块的时间他都用来读专业书。
哈佛的灯总是亮得很早,黄昏的余晖尚未散尽时,阅览室中便已是灯火通明,他靠在椅上,闲闲读一本小说,周遭宁静,手指翻过书页沙沙有声,灯光那样柔和,他放任自己沉入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中,只需三两个钟点,他便能忘了一天疲惫,晚饭后,他又能以无限的精力投入学习中。
如此,他过了四年,没有过旅行,没有体验过异域的风情,没有过寒暑假,连星期休日也一并取消,除了两个夏天离校参加中国留美学生夏令营的二十天,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波士顿。
四年后,他肄业,进行博士答辩。哈佛的博士答辩素以严苛著称,考官一共四位,皆是学术权威,如果答辩完,四位考官不发一词,那意思便是“明年再来”,在哈佛读了七八年博士还拿不到学位的大有人在,他答辩的时候,“紧张得汗顺着脊梁往下流,”不过他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作为班上最年幼的学生,他的答辩却一次通过,他不仅拿到了学位,还获得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
便如离开中国前所设想的那样,他果然学成归国,他还被母校清华聘任,他像所有的陈氏子孙一样,走了一条最正统的道路,以数年的寒窗苦读换取了一个光明的前程。
现在,他可以坦然走到那个女子的门前,告诉她,他来兑现他的诺言。中国的戏文里总是反反复复上演类似的传奇,邻家的少女永远在窗下绣着白头鸳鸯,等那远行的士子衣锦还乡,就算那人一世不归,她也一世守着爱情的信诺,等他归来。
可是,那不是他的传奇,他的传奇,不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等他归来,她已嫁作他人妇。
他忘了,和他相约的不是她,而是同样也爱着她的另一个男人。
他是出过帝师的陈氏子孙,天生秉承着儒家的风骨,他认真地恪守着君子一诺千金,他要堂堂正正赢。可情场如战场,他要道义,他的情敌要的却是结果,战场上多的是诡计欺诈,哪里会有不变的盟约。
他还在哈佛苦读的时候,他的情敌早已先下手为强,对那女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攻势,没错,违背了盟约,欺骗了朋友,这样赢了也不过是胜之不武,可是那又怎么样,他的情敌抱得美人归,而他却黯然离开,独善其身。
从此之后,他一生都不曾再爱过谁,一生都不曾娶过妻。
在他的学生眼里,那个女子也并非什么天仙般的人物,不过只是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诗文传世,也不见得多倾国倾城,连名字都没有留传下来。她何其有幸,让那么优秀的他全然看不见别的女子,她有什么好,叫他对她念念不忘一辈子?
也许并不是世人揣度的,“得不到的东西最好“,也许他的不娶并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爱情失败和朋友背叛的双重打击。他一路走来,无论在鹤龄中学,在清华还是在哈佛,他都是最优秀的人,家人宠爱,同学崇拜,一路坦途的他,比别人更加无法承受失败,而且光是爱情失败还好,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朋友的背叛。他们已经花前月下的时候,他还在一心一意地守着盟约,在这场初恋里,他就像一个呆子,被人愚弄得团团转。
这件事就像一盆冰水,迎头浇上了骄傲的他,浇灭对爱情的热情,从此,他寒了的心,一辈子也不曾暖过来。
他的故事在学生中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他的失败,虽然很“傻”,却叫他的学生肃然起敬。
毕业于北大国际经济系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一诺千金》,他写道:“学问之外,同学舌尖上的岱老是一诺千金的夕阳武士,在这个千金这诺随意打破,爱情像政治逢场作戏的世界里,简直是个亘古神话。”
在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人用种种手段赢得天下,比如“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的曹操,比如“无赖近乎小儿”的刘邦,然而,史书中却总有一个角落为某些“傻气”的人保留,他们败了,可仍被称之英雄,比如华容道上为信义放走曹操的关羽,比如乌江边自刎以谢江东父老的项羽,比如,陈岱孙。
关于陈岱孙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著名翻译学家许渊冲写过一篇《这一代人的爱情》,在许渊冲的笔下,陈岱孙终身不娶,为了的是一个叫王蒂澂的女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和一个校友同时爱上了她。他们双双回国后,在他们两人之间,王蒂澂选择了他的校友,他也坦然退出,他和那位校友仍是好友,只是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法爱上别人,选择了独善其身以终老。
许渊冲的版本流传得更为深远,故事中,王蒂澂选择的那个男子叫周培源。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十有八九是他的门生。
和王蒂澂结婚时,周培源二十七岁,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同陈岱孙一样,他也是清华学堂选送的公派留学生,他的本科和硕士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就读于加州理工大学,并获得加州理工的最高荣誉奖。他的家世背景虽然不及“螺江陈氏”那么显赫,却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考取过前清的秀才。清华校史馆中曾经有过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周培源也是挺拔儒雅,与一旁的陈岱孙相比毫不逊色。
一样的名校出身,一样的英俊潇洒,一样的才华卓越,在这两个不相伯仲的男人之间,王蒂澂选了周培源不足为奇。她和周培源的婚姻极为美满,数十年后,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女儿说:“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他们的女儿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红过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