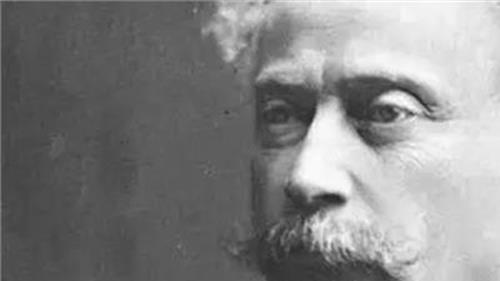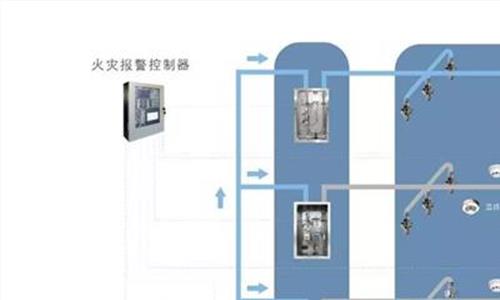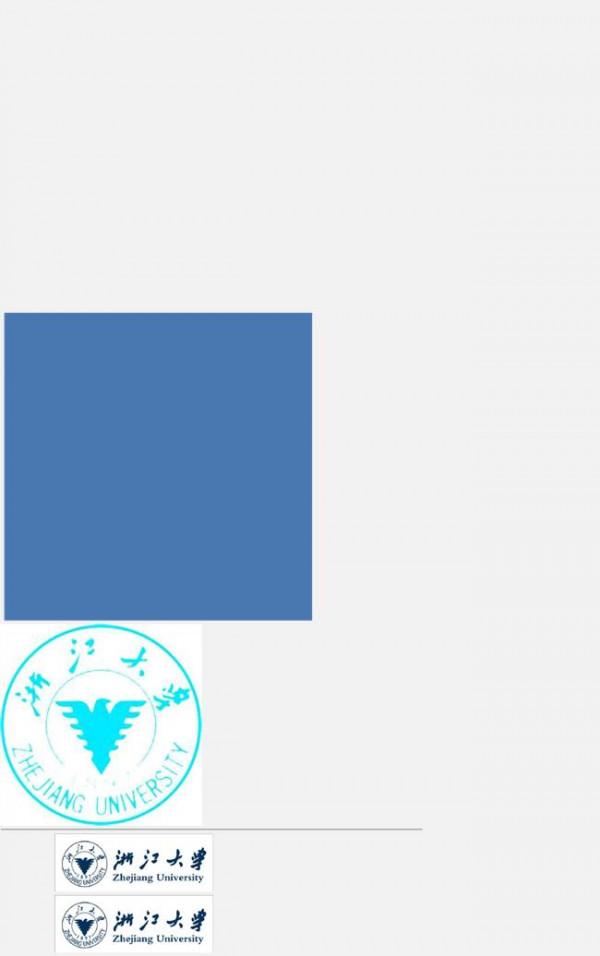邓晓芒神秘与信仰 邓晓芒二则:信仰与现代人
在现代,人们感到做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困难了。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所说的,“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
当代社会、包括其一切制度,都是建立在怀疑这一基础上的,既没有知识的、也没有道德政治上的绝对不可怀疑的权威。而一切怀疑最终归结为对自我的怀疑。笛卡尔从不怀疑他的“我”在怀疑,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果真是他的“我”在怀疑吗?或者,他的“我”真的是在“怀疑”、而不是仅仅在装作“怀疑”吗?这一切重又成了问题。
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病”,并为此而去请教专家(如心理医生)。这说明,现代人(或不如用时髦的说法:后现代人)力图通过某种制度化的机制来重新建立自己的信心和信任(信念、信仰),以确立自己的人格同一性。
“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
以前,怀疑就是不信任,信仰则是不怀疑;而现在,一切信念都只是以一种“姑妄言之”的“假说的形式”出现,同时人们又从这些假说中获得行动的信心和实际的好处,似乎那些怀疑的言论只不过是一种时髦的装饰。
人们热衷于大量阅读流行的“生活指南”之类的读物,明知其不可靠却毫不犹豫地冒险而行,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塑造着自己的形象(通过营养学、美容术和减肥术),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盲目地适应着媒体的忠告和时兴的潮流。
在现代性的信息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在摆脱了一切传统信条之后,仍在寻求着一种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或“纯粹关系”。但这一切都只是对自身的一种“自恋”吗?
对于森尼特和勒施等人把这样一种文化贬称为一种“自恋文化”,吉登斯并不赞同。他认为,现代人对自我的设计和塑造更多地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参与,而不是一种儿童似的向内退缩。因为现在人们遇到问题只有靠自己“自我治疗”和自我帮助,在人们的自我认同发生困难时,使他们痛苦的也不再是负罪感,而是羞耻感。
吉登斯当然知道,后现代文化的确使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处于一种儿童般的无依无靠状态,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除了宣布这种状态本属正常以外,更重要的任务在于从中找到一种进取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就此而言,吉登斯与那些激进的后现代哲学家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甚至回避“后现代”这一用语,而代之以“高级”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确,“后现代”在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更加近似于一种神话,它其实不过是现代性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罢了。
利用“后现代”的一系列话语魔咒来消解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在西方也许只是一种淘气的探索,在中国则很可能隐藏着某种陷阱,它倒真有可能使我们堕入幼儿般的既无责任能力、也无人格根基的未成年状态,却不使人感到焦虑,而使人觉得安妥。
用这种眼光去读吉登斯这本书,你会感到当代西方人的这种儿童式的焦虑实际上并不是幼稚,而是蕴含着令人羡慕的勃勃生机。当我们正在为“体制改革”而伤透脑筋时,人家已在考虑从“解放政治”进到“生活政治”的具体步骤了。克林顿总统的绯闻得到美国大多数国民的谅解也许正是这种“生活政治”开始出现的苗头。当然,我决不会希望超前地把这种政治的理念引进到中国来,我相信其他人也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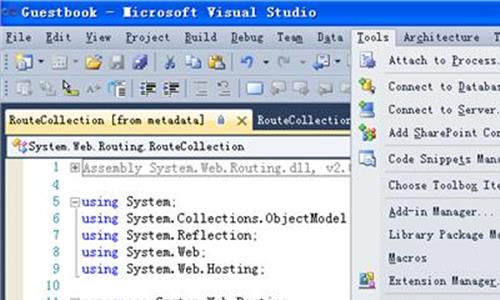

![邓晓芒文小芒 [邓晓芒]邓晓芒 dasein翻译](https://pic.bilezu.com/upload/2/1d/21d41a67c574fb350fbc0d6b9e4f0ca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