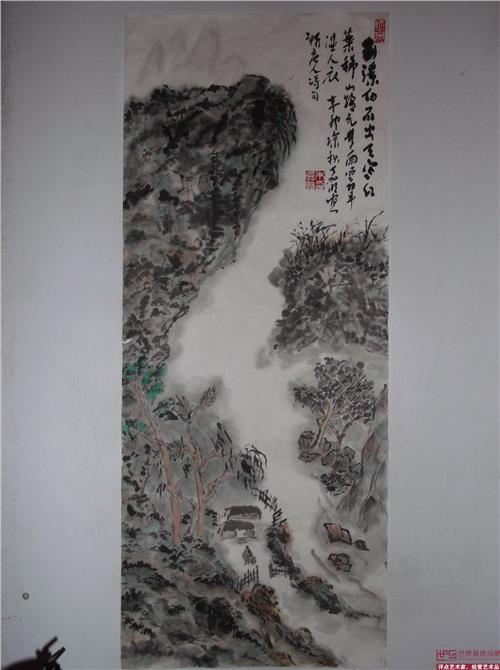朱嘉明与柳红 朱嘉明:《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序
[摘要]依我所见,并非所有“微历史”都值得记载,如同今天走在街上,让每一个人把他今天做的事记载下来,应该说绝大多数人今天的所作所为并无记载的意义。
【柳红注】《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东方出版社,2016年5月)是我的大舅孔庆普先生(1928年生人)近年来出版的第三本书。起因是在两年前,《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和《中国古桥结构考察》新书发布会上,来宾听他如数家珍地谈北京地上、地下,城里、城外之事,其中有人建议他一定要写回忆录。
不曾想,过了一年,大舅就写完了。而这两年间,他还编辑了《孔宪章及其子女书画集》、《孔庆普文集》、《忠恕堂家史拾轶》等几本自印之书。
一位耄耋老人用电脑写作、编辑,创造力和产量如此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因为前两本都是朱嘉明写序,这一次,大舅又希望嘉明来写。今年春节,嘉明读罢书稿,深为触动,写下这篇文字。出版社将其作为推荐序。
图片取自网络
现今中国,年长者写回忆录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要真正写出一本好的回忆录,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一本好的回忆录,必须满足以下一些条件:第一,显现个人历史和所处时代,特别是与历史大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关联性。
因为至少二十世纪以来,没有国人的个人命运可以摆脱时代的变迁;第二,需要有个性(个体)的独特历史记忆角度及其观察记录;第三,提供比较翔实和准确的历史文献;第四,叙述的话语自然、平和、简洁,而不是过度文学化,或者说教,甚至煽情的。
简言之,一部好的回忆录,并不取决于作者原本的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作者能否对自己所经历的特定时空有一种深沉的,却又是超脱和淡然的记录,在字里行间,给人留下思索的天地。这样的个人回忆录,不仅有历史价值且能存留于世。如今,具有历史价值和存留于世的回忆录其实少之又少,而孔庆普先生的这本不过十几万字的回忆录却充满历史价值,势必存留于世。具体来说,它有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历史跨度长。孔庆普先生出生于1928年,今年已经88岁了。他以个人所见所闻为主线,串联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直至1990年代长达八十年的历史。我们在书中看到:七七事变之前,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一个世家的方方面面;日本侵略及抗日战争使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被瓦解;抗战之后中央军如何进入北平,那时的货币经济、石景山钢铁工业、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解放军围城;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接连不断的运动,从三反运动、打老虎、大跃进、除四害、大炼钢铁、大搞技术革新、困难时期的粮食定量、职工停薪留职自谋出路、采取生产自救措施,直到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四五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完结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事件。
第二,以自己的职业生涯折射北京城的命运。孔庆普先生是学土木工程出身,一位典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终其一生与北京市自1950年代初期直到1980年代晚期的市政建设,特别是北京大部分城楼、牌楼、桥梁的修缮和拆除,还有少数为数不多的城楼、牌楼、桥梁的抢救紧密相连。
这本书告诉了读者:这个北京城在1950年曾经有过环城花园建设的规划;1951年曾经有过道路、桥梁、城楼等普查、建立了城里街巷名称档案、城墙城门技术档案,开始城墙修缮工程;1952年,刘少奇关于要把北京建设成一个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影响建设的障碍物的指示,置北京于拆毁老城墙、城门、牌楼的万劫不复之中。
当时,岂止梁思成,包括彭真在内的北京市领导人都不能理解。
彭真说:“拆城墙可是一件大事情,五百多年的北京城说拆就拆,恐怕老百姓都不同意”。然而,一切已经不可逆转,1954年拆除了宛平城城门、地安门、宣武门;1955年拆除了西长安街的双塔寺;1956年拆除了阜城门,切去了团城南边一片;1957年拆除东直门、1958年拆除中华门、崇文门;文化革命初期拆除了西直门。
书中也记载了拆毁和埋于北京城地下的各类古桥名单,例如:甘石桥、江米桥、玉和桥、望恩桥、宣武桥、崇文桥、三里和桥、正阳桥,等等,加起来二十六座桥。
读到这些,我自然是与孔庆普先生一样陷入难以释怀的悲哀和伤痛之中。为北京城悲哀和伤痛,为中国的历史悲哀和伤痛,为一部文明史和建筑史悲哀和伤痛。这里的每一座牌楼、城楼和古桥,每一段城墙,其实都是历史和文明的凝结,没有这些牌楼、城楼、城墙和古桥的北京,早已是一个残缺的北京。
可以不夸张地说,任何一座被拆除的城楼牌楼和古桥,其价值都超过我们眼前一片一片的高楼大厦。
如果说,梁思成先生与当时的决策者争论的是保留北京古城的意义,他为决策者无视自己的主张而痛心疾首,但是,梁思成毕竟没有亲手拆毁他衷爱的北京城。而对于孔庆普先生来说,他有着与梁思成先生一样地对北京城的那份情怀,那份眼界,直接参加了早期的修复,却又不得不参加接踵而至的持续拆毁,情何以堪!
第三,通过亲身经历的片断,让人们得以窥见已经消失的时代。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一些小环境的记录。例如:作者出生之地:
“府邸的总体布局是前宅后院,中间是一条巷路,巷子的南口有一座大门,西厢是老宅,东厢是新建的院落。西厢南北三进院,后院有一棵大槐树,据说是毓辈老爷爷栽种的,树干三人合抱,树帽遮满庭院。前院有一照壁,绘有松鹤图,前院朝南有街门,平时不开,每逢年节才打开。
街门洞里楣上挂一蓝底金字匾,书写‘雪志冰心’。东厢是新建的四合院,南屋五间,中间是穿堂门,门楣上有砖雕。东西配房各四间,北屋也是五间,高台基双楹廊。”
“街门外有一层石台阶,门扇和门框都是黑钯,门扇上有一对铜镣吊儿,门框下面有抱鼓式门墩石。进门迎面是东房的南山墙,是白底‘福’字照壁。院内靠近西墙有一棵枣树,树下有一个不大的鱼缸,养着几条小金鱼。东厦子前面有一个渗水井,刷锅水和洗衣裳水都是倒在渗水井里,因为胡同里的路面比院内地面高,院里的雨水也是流进渗井里。”
再例如,抗战之前的北京钟楼和鼓楼之间的小市场:
“南头都是卖小吃的布篷,也有卖饭的大罩篷。各种小吃多半是清真食品。卖饭的都是汉民,有抻面、烙饼、棒子面贴饼子和粉条豆腐杂烩菜。……中间是卖针线、绒花儿、花枕头顶和花鞋面儿的,卖小孩儿衣裳的,也有大人的衣裳。北头是说相声的、唱小戏儿的、唱大鼓书的等等。”
第二类,大历史下的小故事。例如,1949年镇压天桥的“南霸天”场景,包括这个“南霸天”的穿着细节:
“南霸天的模样是光头、大胡子,上身穿黑夹袄,前衣襟敞开着,里面套一件白褂子,挽着白袖口。下身穿黑裤子,扎着黑色绑腿儿,脚穿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斗争会开完以后,把南霸天押上一辆卡车,拉到先农坛西南角的城墙根儿,执行枪决。”
再例如,大跃进期间的“除四害”:
“城里家家户户的房上都有年轻男女,拿着洗脸盆等物件敲打,有人拿着竹竿儿上端绑一块布晃悠。眼看着麻雀在天空飞着飞着突然就掉下来了。捡到的麻雀都要交到街道。”
第三类,真实的经济生活。例如,困难时期调整粮食定量:
“1959年1月开始实行全民粮食定量制度,是年7月,调整粮食定量,重体力劳动者由每月40斤改成每月36斤,一线干部由每月36斤改成每月34斤,轻体力劳动者和后勤干部由每月34斤改成每月32斤,家庭妇女和学生等由每月30斤改成每月28斤半。
其中一半是细粮,一半是粗粮。1960年2月1日,调整细糖供应量,重体力劳动者和一线干部每月细粮6斤,轻体力劳动者和后勤干部,以及其他人员每月细粮4斤。” “每家每户发一个粮食供应证(俗称购粮本儿)和一个副食供应证(俗称副食本儿)。街道管粮食和副食的干部,每月月底到各家去发下月的粮票儿和油、糖、肉、菜、饼干等票儿。每年12月20日发下一年的布票儿。”
再例如,关于市总工会推广食品双蒸法:
“米饭双蒸法具体做法是,每碗2两米,先用水泡半小时,第一次蒸熟后,凉半小时,再蒸一次,二两米可以蒸出满满一碗饭。大家食用后说,这纯粹是自己糊弄自己,米饭的体积增大了,吃进肚进而当时显得饱了,一会儿就下去了。明知是自己糊弄自己,也得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呐。”
第四类,一一写出人生经历中有过这样或那样关联的人物名字。书中众多人名,或简或繁加以介绍。这些人物可以分成这样几类:
其一,家人30余位。对孔庆普先生有养育之恩、支持最大的是两位伯父,大伯父孔宪文(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系,是中国第二条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淮南铁路总工程师。)、二伯父孔宪武(1897-1984, 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博物系,植物分类学家)和二姑、姑父(曹经武,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授)。
其二,同事及有工作交往的230余人;
其三,彼此有工作配合和相互支持的人,比如单士元(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郑孝燮(建设部规划设计院顾问)、刘仙洲(清华大学教授)、茅以升(1896-1989, 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和他的助手罗英(桥梁工程师)、梁思成(清华大学教授、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候仁之(北京大学教授)、罗哲文(文物研究所主任)、赵迅(文物局研究员)、胡玉远(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以及对作者一生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许京骐先生(1919年生人,原北京市建设局局长);
其四,见过面,开过会的一些人物。像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当时(1951年)的北京市市长彭真(1902-1997)、副市长张友渔(1898-1992)、吴晗等等。
其五,一些虽无过多接触,但因“文革”而死的人。
我写到这里,感慨之至,人老了,能够记住和记载人生中那些遇到过、共事过、受过资助、得到帮助、特别是影响自己人生轨迹的,以及遭受不幸命运的人们,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感恩,也是一种情怀。
以上特点,并不足以反映孔庆普先生回忆录的全貌。每一位读者,只要认真阅读,都会因自己的背景、兴趣和价值偏好而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这就是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随便举个例子:孔庆普先生在跋中补充了1956年公私合营的一个情景:他所在的北京建设局有位工程师叫张连壁。
此人还有一个身份是“东升祥绸布店”的东家。党支部书记问张连壁对公私合营的看法,张连壁说,非常拥护。接着又说,他的叔和婶,白天上街敲锣打鼓,晚上回家老夫妻抱头大哭。寥寥数行,让我们看到了公私合营大历史背后一个小业主的真实情感。
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多年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反思、研究多是集中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上,而“文革”中间的市民日常生活,鲜有记录。本书提供了与“文革”期间“大字报”的两个片断。
其一是贴大字报的浆糊:“贴大字报和标语要用大量的浆糊,机械所北面是化工试验厂,他们研制成功一种合成浆糊。该厂有两派,他们分别和市政处的两派有联系,互称咱们是一家。市政处的两派职工贴大字报和标语用的浆糊,都是去化工试验厂要,各找各派要来的(无偿赠送)”。
其二是天安门前的旧大字报哪儿去了?“学校都停课了,孩子们都跑着玩儿,有两名工人利用公家的材料,为自家孩子制做垃圾车。用角铁焊成一个三角形,前端安装一个轴承,再车一根儿长轴,焊在后边,两端各装一个轴承,成为小车儿的底盘儿。
上面放一个竹筐,用铅丝把竹筐固定在底盘上。孩子的双手扶住竹筐,一只脚踩在车盘后轴上,另一只脚蹬着地,跑起来还真快。……这些孩子们每天晚上,结伙蹬着竹筐车到天安门去撕大字报和标语,第二天卖废品。” 人们难以想象,“文革”期间,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大字报竟然“补贴”了当时某些老百姓拮据的日常生活。
孔庆普先生历尽沧桑,而这本回忆录,从头到尾,如同一幅历史白描,无论写日常工作还是历史事件,决然没有文人墨客式的“抒情”,没有“意识形态”的说教,没有道德制高点,甚至没有评论,但是,却不放过细枝末节,笔到意到,一丝不苟。在平实的叙述中,显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内敛”,让你感受到一种历史“美学”,以及笔底流淌的深厚含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倡“微历史”,即通过一个人一件事的有限历史信息,集合成大历史,宏观历史。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微历史”,老百姓的历史是有其价值的。但是,在提倡“微历史”的同时,要避免“微历史”的庸俗化。
依我所见,并非所有“微历史”都值得记载,如同今天走在街上,让每一个人把他今天做的事记载下来,应该说绝大多数人今天的所作所为并无记载的意义。如果“微历史”仅仅是一个个体的记载,如同一本本流水账,不能折射出一个大历史,其意义和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再说一遍,孔庆普先生的这部回忆录,是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大历史。它将个人的一生和北京城数十年的变迁重合在一起,由一个个体承载如此沉重的“时空”,可谓“微言大义”。对我这个血液里流淌着北京基因,漂泊海外数十年的人来说,打开这本回忆录,就如同打开那沉重的北京城门;而当我合上这本回忆录,如同轻轻掩上北京城门。这之后,则是对那个消失的北京,难以消弥的怀念。(文/朱嘉明)













![演员朱宏嘉 [娱乐]南充籍演员朱宏嘉:从古装大侠到铁血硬汉](https://pic.bilezu.com/upload/3/74/37420c833a5d3232cf72a6c333fdca13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