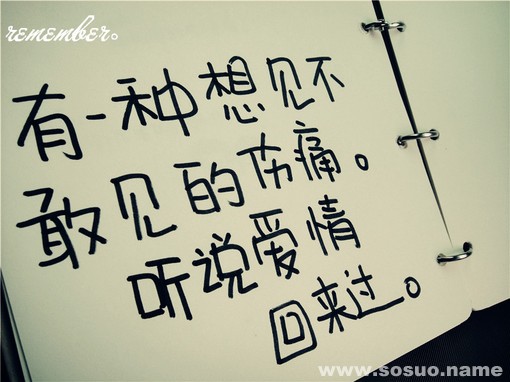吴增定尼采 吴增定:尼采与“存在”问题——从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谈起
摘要: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诠释一直是当代哲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因为它无论对于我们理解尼采的哲学,还是对于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本人的哲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概述了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的基本论点和思路,然后揭示出尼采哲学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向”中所起的作用,并由此从海德格尔的哲学返回到尼采哲学自身,就此澄清了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曲解和误解之处。
最后,本文尝试对两位哲学家的共同哲学关怀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一、 导论 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无论对于理解尼采的哲学,还是对于理解海德格尔本人的哲学,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尼采而言,在海德格尔之前,他一直被看成是一个风格怪异的文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影响也主要是在文学和艺术界,而不是哲学界。
正是海德格尔第一次系统地诠释了尼采的哲学,并且由此恢复了尼采作为一位哲学家的真正地位。而对海德格尔来说,尼采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被解释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对话者和争论者。
事实上,尼采的哲学不仅在20世纪30、40年代间成为海德格尔的兴趣焦点,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一直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潜在问题语境。 但是,如何理解并评价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尽管尼采一生的哲学思考都是以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为己任,但是非常具有反讽和悖谬意义的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读,尼采本人最终还是不幸落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成为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家”。
海德格尔的主要理由是,尼采用权力意志、价值遮蔽乃至取代了存在,从而导致了存在的遗忘。更有甚者,在海德格尔的眼中,尼采不仅是西方“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而且将这种形而上学推向了它的极端,也就是意志、价值或主体性的形而上学。
作为一种现代的“世界图景”,这种形而上学不仅追求“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而且在根本上预示着技术时代和黑暗时代的来临。 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这一解读当然非常富有启发性,因为他不仅揭示出了尼采哲学的内在统一性,而且也强调了尼采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关联。
但是,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显然也存在着很大的偏颇。因为不仅他的具体结论明显地不符合尼采本人的表述,而且他对尼采文本的引用和解读方法也很成问题。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自从有关解读尼采的著作和论文发表以来,海德格尔就一直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其中,尤其以德里达、福柯和德勒兹等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尼采并非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最后的形而上学家或形而上学的完成者,相反,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颠覆比海德格尔更加彻底。
问题是,后现代主义者在批评海德格尔的同时,却也错失了后者的根本洞见。因为无论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存在着多大的误解(哪怕是全盘的误解),但他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尼采哲学的独特视角,由此,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尼采哲学的根本意图。
这个视角就是海德格尔毕生所追问的存在问题(Seinsfrage)。
我们将会看到,尼采的哲学并没有像海德格尔所批评的那样遗忘了存在和存在问题,而是像海德格尔一样揭示了“存在论的差异”(ontologisch Differenz),即是说,尼采同样力图把存在同人对存在的理解、评价和设定区分开来,以使存在自身言说、自行显现和敞开。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概述一下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的基本论点和思路,然后揭示出尼采在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中所起的作用,并且由此从海德格尔返回到尼采哲学自身,最后尝试对两位哲学家的共同的哲学关怀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二、 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基本看法 海德格尔很早就对尼采的哲学产生了兴趣。现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足以证明,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学习和研究期间(1909~1914)就仔细地研读过尼采的主要著作。
在其教职论文(1915~1916)中,他明确地提到了尼采的哲学。[1](P290)而在《存在与时间》(1927~1928)中,他详细地援引了尼采《不合时宜的观察之二》(《历史学对于生命的用途和滥用》)中的三种历史观。
[2](P447~448)但总体说来,一直到了《存在与时间》时期,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理解仍然受制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如狄尔泰、李凯尔特和西美尔等)的解释框架,把尼采看成是一位生命哲学家。
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真正理解,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其大学校长就职仪式上的讲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海德格尔第一次明确地将尼采看成是“最后一位寻找上帝的德国哲学家”。
这一论断已经预示了海德格尔后来对尼采的整体看法,即认为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在1936年至1946年间,海德格尔在一系列的讲座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尼采哲学的观点。
后来,这些讲座结集为两卷本的《尼采》,并于1962年结集出版。除此之外,海德格尔还写过一系列关于尼采的重要论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和“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分别收入《林中路》和《演讲与论文集》中。
而在海德格尔其他后期著作中,有关尼采哲学的讨论文字更是随处可见。当然,在海德格尔的这些著作和论文中,尼采的思想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一直被定格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而他的哲学也被命名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主体性形而上学”和“价值形而上学”等。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3](P889)这一真理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方面,它揭示出存在者整体是什么(Was-sein);另一方面,它揭示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或如何存在(W ie/Daβ-sein);前者即拉丁文的“本质”(essentia),后者即拉丁文的实存(existentia)。
本质和实存就是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范畴。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显然更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因为它决定了存在者整体的实存或存在方式。由此,本质便被视为真正的“存在”,而实存则是变化无端的“生成”。
自柏拉图以降,西方的形而上学一直执著于本质与实存或存在与生成的两分,将“存在”视作某种永恒不变的理念、上帝或本体,相应地将“生成”视作虚假的感性世界、尘世和现象。
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所揭示的仅仅是存在者的真理,而不是存在的真理。因为它无视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存在论区分,将存在误认为是某种存在者,因此导致了对存在的遗忘。进而言之,造成这种对存在的遗忘的根本原因在于,形而上学将人关于存在的观念或表象(如理念、上帝或本体)遮蔽甚至取代了存在自身。
就此而言,任何形而上学在根本上都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Humanismus)。海德格尔说:“‘人类中心主义’意指一个与形而上学的发端、发展和终结休戚相关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人在各个不同的角度、但总是有意识地奔赴到存在者的中心部位,而又没有因此就成为最高的存在者。
……而随着形而上学的完成,‘人类中心主义’(或者‘以希腊方式’说:人类学)也就力求达到最极端的、同时也即无条件的‘地位’上。
”[4](P272) 海德格尔之所以将尼采的哲学看成是一种形而上学,甚至看成是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是因为他认为尼采的哲学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逻辑。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的哲学仍然试图在根本上揭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具体地说,在尼采那里:意志不断地作为同一个意志返回到作为相同者的自身那里。存在者整体的本质(essentia)乃是权力意志。
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即它的实存( existentia),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unft des Gleichen)。尼采的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词语是“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它们从自古以来对形而上学起着指导作用的方面来规定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也即来规定本质(essentia)和实存(exis-tentia)意义上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ens qua ens)。
[5](P243) 海德格尔认为,在尼采的哲学中,“‘权力意志’、‘生成’、‘生命’和最广义的‘存在’,乃是一个意思。”[5](P236)换言之,存在即生成,生成即生命,而生命则体现为追求权力或力量的意志。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所谓“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并非意味着权力是某种外在于意志的现成存在(Vorhanden),而是意志本身。既然“权力意志”是意志对自身的追求或“追求意志的意志”(Wille zur Wille),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它所追求的恰恰是自身的存在或自身的永恒轮回。
就此而言,“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原本就是一回事:存在即是追求自身永恒轮回的意志。
在尼采那里,这一意志的化身就是“超人”( Ubermensch):他意欲着自身的永恒轮回,由此给生成或意志本身打上存在的烙印。 尼采将存在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无常的生成、生命或权力意志,这难道不恰恰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吗?海德格尔并不否认这一点。
他甚至一再强调,尼采哲学的出发点就是克服“上帝死了”所造成的现代虚无主义的危机。在尼采那里,所谓“上帝”并非特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论人格神,而是代表了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一切超感性或超验世界,无论是理念、上帝,还是本体;与此相对,“上帝死了”则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
随着“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生命、生成、感性世界或尘世也相应地变得没有意义或无价值。
为此,尼采反过来强调要重新为生命创造或赋予价值,但这一意义或价值并不是外在于生命的超验世界,而是生命自身。也就是说,这是生命的自我肯定。 但是,海德格尔恰恰认为,尽管尼采将生成或感性世界变成了真正的存在(存在者整体的本质),而把超感性世界变成了现象或假象,但是,尼采同他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一样,仍然执著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本逻辑。
即是说,“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
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中,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
”[5](P224)换言之,尼采同他所反对的传统形而上学一样,在根本上仍然是将存在同某种存在者(生命、权力意志或价值)相混淆,因此仍然是对存在的遗忘。
不仅如此,海德格尔甚至进一步断定,尼采把传统的形而上学推到了它的极端,也就是一种意志、价值、主体性或技术形而上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最终实现,尼采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穷尽了形而上学的最后可能。
原因在于,尼采把存在变成了一种权力意志的评价或价值设定,变成了一种“价值”。换言之,存在在尼采的哲学中变成了对存在的设定和控制,存在的真理变成了人作为主体对于存在的信念或表象。在这一点上,尼采不仅继承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且更是将自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尼采的哲学不仅开启了技术统治的黑暗和贫乏时代,而且导向了“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
[3](P892~893) 问题在于,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尼采的本意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返回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本身。无论海德格尔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尼采的自我理解,但它无疑代表了海德格尔本人的哲学思考。
那么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对尼采哲学的解读意味着什么呢? 三、 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与他对尼采哲学的解读之关系 我们已经指出,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兴趣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
众所周知,恰恰是在这段时间,海德格尔开始了他的思想“转向”(Kehr)。他放弃了《存在与时间》第二部的写作计划,开始了新的思想尝试。他在1936~1946年间关于尼采的讲座和论文,便是这种思想尝试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海德格尔在此期间还对赫尔德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对尼采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对赫尔德林几乎是极尽赞美之能事。正是在赫尔德林的诗歌中,海德格尔看到了克服形而上学的可能。
因此,为了理解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实质,我们有必要首先回到《存在与时间》。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思考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 正如《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开篇所强调的,海德格尔在这本书中的主要任务是澄清“存在”的含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海德格尔选择了从作为“此在”(Dasein)的人作为思考的出发点。此在当然不是存在,但他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因为他的本质(essentia)就是去存在(Zu-sein)或生存(Existenz/existentia)。
他不仅对存在本身拥有某种“前理解”,而且他还能够筹划自己的存在。不仅如此,此在的存在还具有“向来属我”的特征( Jemeinigkeit),或者说总是“我”的存在。
故此,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对此在之存在或生存的描述来澄清存在的含义。 按照海德格尔的描述,此在的生存包含了三个要素,即生存筹划(“先行于自身的存在”)、被抛(“已经在世界中的存在”)和沉沦(“作为寓于世内之物的存在”)。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此在的整体生存或存在,海德格尔名之为“烦”(Sorge)。此在的存在或“烦”虽然向来是“我”的存在,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情况下,此在却遗忘和逃避自己的存在,作为常人(das Man)混迹于世。
这就是此在之存在的非本真性(Uneigentlichkeit)。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对其自身存在的遗忘和逃避反倒揭示出它的存在的有限性或终有一死的本性,或者说此在之存在的非本真性揭示了它的本真性(Eigentlichkeit)或真理。
在对死亡或有限性的“畏”中,此在听从良知(Gewissen)的召唤,决心承担起自己的生存。
惟此,此在方能不仅本真地去存在,而且选择自己的存在。 鉴于此,海德格尔将此在之存在或烦的意义揭示为时间性(Zeitlichkeit),“此在的一切行为都应从它的存在亦即时间性来阐释”。
作为一个整体,此在首先是先行向死的存在,“这一向死存在只有作为将来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即是说,此在的存在首先意味着面向将来去筹划自己的存在。其次,此在总是已经被抛入到世界之中,他对自己的存在负有罪责,因此必须承担自己的“曾在”。
最后,此在存在于世界中总是要同各种各样的世内存在者(物或人)打交道,让它们来照面,因此他总是生活在“当下”。对于此在来说,将来、曾在和当下既不是三个孤立的要素,也不是一个线性的矢量,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曾在-当下的将来”。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统一体即是时间性,无论将来、曾在还是当下,都是时间性的绽出(Ekstase)。作为此在之存在或烦的意义,时间性为我们澄清一般存在的意义提供了根本契机。
然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并没有开始实现自己的最初设想。他仅仅描述了此在的存在,却未能由此推进到对一般存在之意义的澄清。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是什么? 倘若参照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那么答案便是再清楚不过了。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思考方式同他所解读的尼采哲学几乎如出一辙。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我们将《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Dasein)变成“权力意志”,那么它几乎就成了海德格尔后来所大加批判的尼采哲学:如果说(海德格尔笔下的)尼采将存在变成了权力意志的设定或价值,那么(《存在与时间》中的)海德格尔则是将存在变成了此在对于存在的筹划;如果说尼采认为权力意志的存在方式是意愿自身的永恒轮回,那么海德格尔则将此在的本真存在看成是先行向死的存在。
因此,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40年代关于尼采的讲座和论文,与其说是对尼采哲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存在与时间》的批判,或者说是他对其早期哲学的自我批判。
姑且不论尼采的哲学是否符合海德格尔所界定的那种意志、价值或主体性形而上学,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界定如果用于《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却是再适合不过了。
所谓“基础存在论”的实质,正是用此在或人的存在遮蔽甚至取代了存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将传统的存在论或形而上学推向了极端,使之成为一种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
[6](P313) 这样一来,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批判如果不是有意的误解,那就是一场类似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游戏。事实上,尼采非但不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那样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反而在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无论是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现代主体性的解构,还是他对艺术与真理之关系的辨析、对前苏格拉底悲剧哲学的肯定,都已经预示了海德格尔后期的很多思想要点。当然,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尼采哲学的根本意义在于,他非但没有遗忘所谓的“存在问题”,反而非常自觉和明确地将存在同人对存在的设定或信念区分开来。
四、 从海德格尔的解读反观尼采哲学的意图 尽管尼采没有明确地使用过“存在问题”这样的表述,但毫无疑问的是,存在作为一个问题同样贯穿了尼采哲学思考的一生。
在一篇早年的未刊稿《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沦》(1873)中,尼采便已经深刻地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无论是科学真理、艺术真理还是宗教真理,甚至包括语言、逻辑和身体感官,在根本上都是一种隐喻和谎言。
尼采这样说到: 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
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7](P106) 也就是说,尼采在这一时期认为,人说到底完全生活在自己制造的隐喻和谎言的囚牢之中,固执地将它们等同于存在、现实(Wirklichkeit)或真理本身。
参照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和批判,我们很容易发现,尼采的一生中只有这个时期最接近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意志或价值形而上学。
因为在尼采看来,作为一个终有一死的有限存在,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必须完全遗忘自己终有一死的存在或真理,并且生活在隐喻和谎言之中。
“他忘记了原始知觉隐喻之为隐喻而把它们当作了事物本身。”[7](P108)基于此,尼采最终泯灭了真理与隐喻、存在与人对存在的设定之间的界限,并且将哲学看成是一种艺术形而上学。 不过,尼采很快就告别了这种艺术形而上学。
在几年之后出版的两卷本《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中,尼采对自柏拉图以来的所有形而上学都展开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这种批判一直贯穿了《快乐的科学》和《曙光》这两部著作,并且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超善恶》、《论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和《敌基督者》等著作中得到了清楚的表达。
在尼采看来,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在根本上都是一种“人性、太人性”的迷信、假定或想像,都是用人自己关于存在或“现实”的善恶判断和道德评价取代了存在或现实本身。
因此,若要澄清存在的意义或真理,那就必须对一切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价值重估(Umwertung)。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二卷“自我克服”这一章节中,尼采借古代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提出了“存在”问题。
查拉图斯特拉认为,传统的哲学家(即文中所说的“最智慧者”)总是自以为在追求真理,但事实上他们的求真意志(Wille zur Wahrheit)不过是一种权力意志;也就是说,他们想要“使一切存在者都变得可思考”(Wille zur Denkbarheit alles Seienden),并把他们的意志和善恶价值“置于生成之河流上”。
[8](P144)藉此以反观自身,查拉图斯特拉洞察到了这样一个真理:生命或存在本身即是权力意志的创造与毁灭过程。 但是,对于查拉图斯特拉来说,这一真理却是一个“致命的真理”。因为一旦我们洞察到生命或存在本身的真理,那么我们同时也就看到,包括这一真理本身在内的一切存在都将是一个转瞬即逝、变化无常的创造和毁灭过程。
更糟糕的是,这一创造和毁灭过程还很可能会不断地自我重复。这样一来,存在或生命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永恒轮回”。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二卷的结尾,查拉图斯特拉正因为无法承受这一致命的结论,才大病三天,并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传道事业。 但是,查拉图斯特拉却并没有因此像佛教和叔本华那样走向消沉或颓废。
相反,正是由于领悟到了存在或生命就是权力意志这一真理,他才能最终抛弃一切强加在存在或生命之上的幻觉、想像和善恶设定,直面存在或生命本身。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一真理变成了对存在或存在自身的无限肯定。
正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对于查拉图斯特拉来说,存在或生命尽管是一个变化无常、转瞬即逝的过程,但它并不因此变得没有意义。恰恰相反,生命不仅想要(will)自身的当下存在,而且想要它再来一次(noch einmal/ da capo),甚至想要它永恒地轮回,哪怕这种轮回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即是说,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unft des Gleichen)。
在《超善恶》一书中,尼采更加清楚地揭示了权力意志的真理从对生命的否定到对生命的无限肯定的转变过程。 假如谁像我这样怀着一种谜一般的渴望把对悲观主义的思考贯彻到底,并把它从半基督教、半德国式的、尤其在这个世纪以叔本华哲学的形态所表现出来的狭隘和偏执中解放出来;假如谁真正以亚洲和超亚洲的眼光深刻地洞察了一切可能思考方式中最彻底地否定世界的思考方式,并且高高在上地审视这种思考方式———这是一种超善恶的审视,而不再像佛陀和叔本华那样陷入道德的魔障和幻觉之中———那么他恰恰由此张开双眼看到了相反的理想(尽管他并非真正有意这么做):看到了那种最骄傲、最有生命力和最肯定世界之人的理想,后者不仅学会顺应和容忍一切曾在和现在(was war und ist),而且希望如其曾在和现在地(wie es war und ist)重新拥有一切曾在和现在,希望永恒地重新拥有它,永不知足地呼喊“再来一次”(da capo);他的呼喊不仅针对自己,而且针对整个剧本和戏剧,不仅针对一部戏剧,而且在根本上针对那些恰好需要这部戏剧——并且使之成为必要———的人:因为后者自己一再( immer wieder )需要这部戏剧。
[9](SS. 74~75) 因此,作为一个内在的统一体,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学说并非如海德格尔所说是对存在的设定、控制和征服,更是同所谓的意志、价值或主体性形而上学等等毫不相干。对于尼采来说,权力意志的顶点即是一种反观自身的求真意志,而在这种求真意志中,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意志都得到了无限的肯定。
这种无限地自我肯定的意志,就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超人”。作为存在或生命的祝福者(Segende)和肯定者(Ja-sagende),超人将万物“从目标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把“偶然”(Von Ohngefahr)———这个“世界的最高古老贵族”———“归还给万物”;他让万物“在‘偶然’之脚尖上跳舞”,“在永恒之泉边、在善恶的彼岸接受洗礼”;[8](P210)他使万物自行敞开,让万物如其所是地存在;他摧毁了一切“人性、太人性”的谎言或“沉重的精神”,“挪开大地上所有的界石(Grenzsteine),并且给它重新洗礼,命名为‘轻盈的大地’。
”用查拉图斯特拉的话说,“一切存在的语言和语言宝盒都在此向我敞开:一切存在都想要在此成为语言,一切生成都想要在此向我学习言说。
”[8](P236) 让我们再次返回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恰恰是在同尼采的对话、遭遇和争执(Auseinandersetzung)中展开了关于“存在”问题的重新思考。在《哲学论集(论本有)》一书中,海德格尔明确地放弃了藉由此在去追问存在之意义的思想道路。
对于后期海德格尔来说,存在本身无论如何不是人可以用表象或对象化的方式把握的现成存在者。存在即是自行显现、自身给出(es gibt)或自身言说,是神妙莫测的命运和馈赠。
惟有存在给出自身,人方能对它有所领悟和言说。存在同时意味着敞开和遮蔽,海德格尔称之为本有(Ereignis)。海德格尔不断地引用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名言:“技艺远远不如命运有力量”。
即是说,人不是存在的主宰者,而是它的守护者。因此,倘若以尼采的哲学为参照,那么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语言与尼采大相径庭,但他们的基本哲学精神却是异曲同工。
五、 结论 本文的意图既不是要对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作一个不知所谓的泛泛比较,也不是要介入二者孰高孰下之类的无聊评价和争执,而是希望从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解读中引出我们自己关心的问题。无论海德格尔在多大程度上误解甚至曲解了尼采的哲学,但在根本上,他的哲学关注同尼采的哲学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都看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都是用某种人对存在的设定取代了存在本身,由此导致了对存在的遮蔽、遗忘,或者说导致了虚无主义。
他们都认为,克服虚无主义的前提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价值的重估或解构。 问题在于,在颠覆和终结了作为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之后,哲学是否还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呢?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尼采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显示出了决定性的差异。
在尼采看来,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颠覆并不是对哲学本身的否定。毋宁说,结论刚好相反:只有在彻底批判和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之后,真正的哲学才能得以开始。在《超善恶》一书的“前言”中,尼采认为传统的哲学家看似在追求真理,实际上却并不知道他们所追求的真理不过是他们的权力意志或“求真意志”的设定。
尼采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具有彻底的反思精神,必须将这种“求真意志”转向自身,也就是说要对哲学家追求真理的这种权力意志进行追问。
唯其如是,他才能真正地跳出善恶的人为价值设定,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包括自身在内的这个生生不息地变化和生成的世界,洞悉关于“存在”的真理和智慧。由此,尼采将真正的哲学称为“未来哲学”,以示与一切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划清界限。
相比之下,海德格尔,尤其是后期的海德格尔,要走得更远。他明确地认为,哲学本身已经终结了。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或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历史的第一次开端,原本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某种特殊命运或天命。
之所以说哲学是“第一次开端”,是因为希腊人第一次提出了“存在问题”。但是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存在问题”却慢慢地被遗忘了。当然,所谓“存在的遗忘”,并不是哪位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儿或尼采等)有意为之,而是存在自身使然,或者说是存在的神秘“馈赠”。
现代虚无主义的命运不过意味着,西方文明已经彻底耗尽了“第一次开端”的全部可能性与生命力。
至于“第二次开端”或“存在”的 再次“敞开”,西方只能耐心地等待。[10](SS. 177~190)因此,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是西方本身的终结。海德格尔甚至明确地表示,西方文明的“第二次开端”不仅与“哲学”无关,甚至与“西方”无关,因为哲学作为第一次开端的可能性已经彻底“终结”了,而西方必须开始学会从非哲学的东方寻找自己的转机。
[11](P58~76) 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尼采的“未来哲学”,还是海德格尔的“第二次开端”,都未能变成现实。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现代主义者虽然继承了他们对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颠覆,但其结果却是,他们不但否定了哲学本身,而且一并抛弃了与哲学息息相关的“存在问题”。
在他们那里,“存在”仅仅变成了空洞的能指符号,没有任何具体所指;相应地,哲学也变成了一个无穷的能指游戏。倘若我们不想接受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回到尼采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同他们一道去认真地思考一个与哲学本身血肉相连的“存在问题”:哲学本身能否跳出人为的善恶价值设定,好让存在自行显现,自身说话? (收稿日期:2009-06-16) 【参考文献】 [1]Michel Haar.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Heideggerian reading of Nietzsehe [A]. Martin Heidegger. Critical Assessments II[C].
edited by Christopher Macan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06. [3]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6]Klaus Held. Heidegger and the principle of evidence[A].
Martin Heidegger. Critical Assessments II [C]. [7]尼采.哲学与真理[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8]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Nietzsche. Jenseits von Gut und Bse [A].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KSA) 5 [M].
edited by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aino Moninari. Dünndruck Ausgabe,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 Müehen: Walter de Gruyter, 1988. [10]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esamtausgabe, Band.
65 [M]. herausgegeben vo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9. [11]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