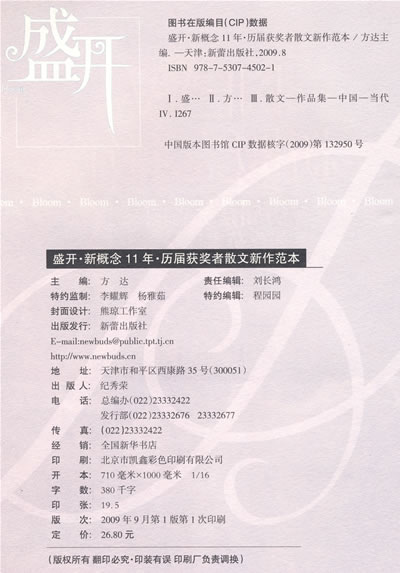任晓雯的婚姻 任晓雯:关注荒废的青春书写凋敝的生活
近日,作家任晓雯推出新作《生活,如此而已》。这也是时隔七年,继《岛上》《我们》之后,她重新执笔书写长篇小说。
《生活,如此而已》讲述了一个“胖女孩”的成长故事,与之前的作品相比,《生活,如此而已》不仅延续了她一贯的精细绵密,在对追求细节的精确与情绪的控制上,更显示了一种沉淀后的成熟与从容。文中所描绘的上海风情,让人联想起张爱玲语言的灵动与风致。
正如著名评论家张柠所说,“任晓雯的小说叙事,既有强烈现实关怀,又不囿于现实逻辑的束缚。她编织着叙事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引读者走进生活现场,并领他们穿越现实的泥淖,走向一片未知的光晕之中。”评论家杨早也称赞道:“这样的小说久矣不复见,通篇饱满,舒展,很多句子读时要停下来顿一顿,像橄榄需要回味。”
任晓雯告诉记者,“这次写作,与我平常写作不同。我并不从明确的情节构思出发,而是被情感引导,逐步虚构出人物。”主人公蒋书的塑造源于她遇见的一个胖女孩。“冬天的北京街头,两只红肿的冻手,捽一副煎饼果子。边走,边吃,边哭。
饼渣窸窣,落进羽绒服袖口。她留我一鼻子葱花气,和若干琢磨不清的感触。于是,两年后,有了这部小说。是那个没空停在路边,专门哭一哭的胖女孩;是每日上午九时,挤在办公电梯前,僵仰着脸,憋忍着尿,盯住层层停顿的指示灯的年轻人中的任意一个。”
近年来,任晓雯一直笔耕不辍,她的散文随笔也深受读者喜爱。对于这次首次尝试青春爱情题材,任晓雯坦言,“初学写作时,我曾告诫自己,不轻易写两桩事:爱情,青春。它们是低门槛题材,因而难度也大。就像最考验厨艺的,往往是原料烂俗的菜式,比如炒青菜。
没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不敢端上台面。” 然而,北京街头偶遇的胖女孩,“触动我的痛觉,触动我顺风顺水的生活里,隐秘而持久的挫败感。我忽想写写被荒废的青春,写写尚未展开、即已凋敝的生活。”
写的是普通人和当下生活中的痛苦
记者:《生活,如此而已》讲述了一个另类成长故事,主人公蒋书幼年父母离异,青春期孤独寂寞,大学毕业后又遭遇求职困难,父母老病,男友背叛等种种,这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年轻人,几乎是一个童年阴影、青春荒废、残忍生活等负面词汇叠加于一身的女孩。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故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失败”的小人物呢?
任晓雯:你说得很对,我也觉得我写了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你提的几个词汇,“荒废”是我在后记里说的,其他则可能出于读者和媒体的归纳。蒋书这么一个人物,的确是既普通,又充满挫败感的。
说到这个类型的人物,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阅读理查德·耶茨时的惊艳。《革命之路》把中产阶级婚姻与生活中隐秘的痛感,描写得如此入骨。包括我有阵子比较迷的雷蒙德·卡佛、约翰·契弗等等那一路美国作家,写的都是普通人,写的都是失败者。都是切口很小,却力道很足的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的强大传统,是写历史、写乡村。我们这个农耕国家的历史太丰富,历史中的苦难也太深重。相比之下,书写当下,书写城市,似乎显得过于轻巧了。写字楼小白领的痛苦,怎能跟政治风浪里一路颠过来的老人们相比呢。这是题材上的天然劣势。
然而,文学是没什么不能写的。柯罗连科在回忆录里曾说,契诃夫提及他是怎么写短篇小说的,“他瞅了一眼桌子,顺手拿了一样他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原来是个烟灰缸,把它放到我的面前,说:"如果愿意,明天就有一篇短篇小说……标题是《烟灰缸》。
"”难道现代都市小白领的精神上的痛苦,还不如一只烟灰缸值得写吗?历史有历史的难题,现实也有现实的困境。当我坦然告诉自己,不必每部作品都野心巨大时,也就能够坦然写写一个都市普通年轻人的经历了。
我所需要做的,是把这个小作品写得精巧准确,一举命中最核心的精神痼疾。《生活,如此而已》在我自己的写作中,算是一个异数。我的其他几个长篇,比如处女作《岛上》,是试图讲述普遍境况的寓言;《她们》是几十年泥沙俱下的历史中的众生相;现在手头修改着的一个新长篇《好人宋没用》,时间跨度则从1921年到1998年。
我自己感觉,用架空历史或者回顾历史的姿态去写作,会让人更“舒服”。因为时间上的疏离,让读者更容易承受其中的痛苦。
毕竟那是祖辈父辈的苦难,是过去了的苦难,看似不再能对当下造成伤害。而书写当下生活中的痛苦,是什么感觉呢?就像走路的时候,鞋里进了一块石头,硌着磨着,渐渐出血。你试图忘记疼痛,假装若无其事走下去。有人来提醒一下:喂,疼吗?你肯定感觉不舒服。我想这是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可能会产生的体会。
记者:蒋书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八零后所能遇到的各种生活难题,这样的窘困人生,其实一直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也都能从这个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但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直面这种困境。你为什么选择把这代人的隐痛撕开审视呢?而小说的结尾,没有答案,几乎是绝望的。
任晓雯:八零后的确有普遍的生活难题。他们是唯一一代独生子女,赶上了大学收费,房价高涨,养老负担重,婚恋压力大。如果不幸背景普通,资质家常的话,很可能成为被这个时代碾压在最底下的人。不管愿不愿意面对,这是一个事实。小说家不是兜售粉刷的,也不是贩卖糖果的。小说家要诚实。虽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类做不到完全诚实,但小说家至少应该努力趋近这个目标。
记者:蒋书生活的上海,市井,琐碎,阴暗,蒋书的生活,是一片跋涉不到头的现实泥淖,这是大都会小人物的故事。你使用了一种冷静、克制甚至谨慎的行文来描摹这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社会基础生活,通篇都是锋利的短句子。这种风格是针对这个题材有意而为的吗?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抽离的姿态?
任晓雯:不是针对这个题材的,也不是有意而为。这是我慢慢形成的风格。我觉得一个讲相声的,最好是自己冷面不动,却惹得底下哈哈大笑。一个写小说的,也最好收敛动作,不必使足老劲掴打读者,不妨伸到读者最怕痛的那个地方,吊起丁点皮肉,轻轻拧他一下。只有最不动脑筋的电视连续剧,才放任里头的人物大哭大闹,嘴巴张得连小舌头都露出来。
人物和历史都活在细节里
记者:有部分读者试读后的第一反应是:有点王安忆的感觉。有读者感叹:这样好的文笔让人想重读一遍,这么悲的人生却又让人不忍心再重看一次。这种“美和毁灭”让人联想到同样写上海题材的张爱玲。你受她们的影响大吗?还是因为同样一方水土,养育出有同样文学触感的作家?
任晓雯:我行文方面的老师是福楼拜,他的冷静克制为我所喜。对于我,上海只是个随手取用的背景,地域从来不是写作重点,人才是重点。其实仔细辨析,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等写上海闻名的作家,文笔是各有不同的。但因书写同一方水土,又同得沪语补养,肯定会有气息相通之处。
记者:《生活,如此而已》情节性并不强,几乎是各种细节的描写推动了小说的走向。你最近在南方周末上的一个专栏:《浮生》,里面的每一篇就是一个小人物。很好奇,你的这些材料都是从哪里来的?有虚构的成分吗?
任晓雯:《浮生》的素材来自当面采访和翻阅口述材料。《浮生》系列写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不是非虚构,也不是小说。在我看来,不存在完全非虚构的写作。所有语言都是主观的,经过遴选和组织的,被情感、记忆、自我维护的本能所洗刷的。事实一经说出,即被窄化和扭曲。在不同叙述人口中,在各个记录者笔下,呈现不同面目。
基于这种认识,《浮生》的写作,在历史细节上,是以还原的方式— 即所谓“非虚构”,来趋近真实。在人性细节上,则不过多倚赖当事人表述。人性是幽深的,摇曳不定的,难于概括的。我更愿借助体察与怜悯,去捕捉其间微妙。体察源于自己,怜悯及于他人。由此而生的想象力,往往更趋近人性的真实。
这也是我一贯的写作原则。我希望我的写作中,人性细节是丰富的,历史细节是准确的。既然是走冷静克制的风格,没有大喧哗高调门,就更该把细微中见奥妙的功夫做足。
这本《生活,如此而已》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人性细节。我手头快完成的下一个长篇《好人宋没用》,从1921年写到1988年,历史细节简直查瞎我的眼。纸质书资料买了百来本,网络资料和电子书就找得更多了。尤其自上世纪50年代以降,生活各方面的细节因为形势变化而迅速变化。
比如发型服饰的流行,有时两三年就翻一翻。忽而刘胡兰头,忽而红卫兵头,忽而柯湘头;忽而中山装,忽而布拉吉,忽而海魂衫;忽而工装吃香了,大家把帆布衣服洗得褪色,配个小喇叭口裤子,裹个拉毛围脖;忽而军装吃香了,又纷纷把衣服染蓝,换一排“八一”塑料纽扣。
再比如小说里出现个日用物品,也得小心考证,几几年这个东西是买不到的,几几年又能买到了。几几年是什么价格,几几年得凭票买。查资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人物在细节里,历史也在细节里。虽然我重点是写人物,但细节往往能一举多得,一些更大更深远的东西,会在细节背后若隐若现地浮动。
你说到“细节推着小说的走向”,我很喜欢这个表述。小说的速度感要靠细节牵引。细节的疏密,决定了小说速度的快慢。细节的布局,决定了有所写有所不写。读者好比火车里的乘客,文字则如窗外风景。叙述速度决定了读者几时慢观或快览,哪处模糊或清晰,如何疏略或细致。
甚至,作为列车长的作者会突然刹车,迫使读者逗留于某格风景,作停顿的凝视。高明的作者,会把这一路的转折、停顿、渲染、铺陈,做得不露声色。读者会以为或仓促或从容的景色交织成的“窗外印象”,是自己获得的,而非被安排和要求的。这就是速度的魅力,也是细节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