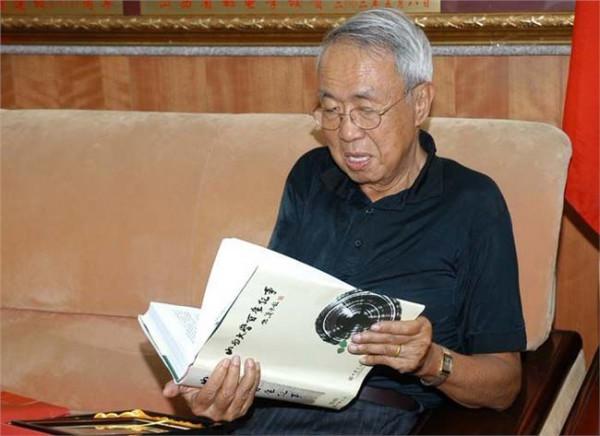《邓小平时代》:“告诉西方 一个真实的小平”
《邓小平时代》:(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傅高义
一位年过八旬的美国学者,在10年之前,立下志向要写一本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图书。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邓小平身上。他认为,亚洲的重点在中国,而对中国现代进程影响最大的,正是邓小平。他花掉了10年时间,写出来一本《邓小平时代》。这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傅高义毫不掩饰对于邓小平的钦佩之情。他写道:“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与‘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我希望中国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
近日,《邓小平时代》在京举办新书发布会。当天,记者采访了傅高义。这是一位瘦小、斯文的美国老头,面容清瘦,西装革履,用流利的中文与我们交谈,声音很轻,语调舒缓。
“他的智慧与能力,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记者:您写《邓小平时代》的初衷,是想帮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那么,现在的美国人是怎么看待当代中国的?
傅高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的确非常了不起,只用了30多年时间,就超越日本、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发展速度举世罕见。如果按照这个步伐,中国可能会在未来不久,在总产值上超越美国。有的美国人认为这将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也有人非常担心这种超越,担心中国如果超越美国,会不会成为危险的因素。不管是哪种人,他们都开始关注中国。
我觉得,要了解亚洲,就得了解中国,要了解当代中国,就得了解邓小平。毕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源于他领导的改革开放。但是,当前的美国人,对中国30多年前启动的这场变革、对于其领导者邓小平,评估显然不足。我必须告诉他们:需要重新认识邓小平。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邓小平有着了不起的智慧与品质。
记者: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写成,十年的时间,您对邓小平的认识有没有变化?
傅高义:当然有。我陆陆续续收集到各类资料,采访到各种人,然后从这些资料与谈话里获得信息,进行分析,不断丰富乃至调整自己对邓小平的认识。写到后来,我发现,他考虑的事情比我预想的要多得多、复杂得多。他在应对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时,显示出来的智慧与能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比如他处理人民公社问题,就表现出难得的政治智慧,我没有料到他会这么出色。
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我发现这个少言寡语的人,却思想开放,具有世界眼光。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和他相处愉快。1972年中日建交,邓小平在1974—1975短短两年里,就见了几十次日本客人。1978年,改革开放头一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有12位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
记者:在书中,您坦言对邓小平充满钦佩之情,最钦佩的是他的哪种品质?
傅高义: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坚定地搞改革开放,没有前路可循,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实验一边推进,这是非常需要胆略的!他需要承担最后责任,需要做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和他共事的核心班子,他要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在一起有效地工作。
他要给人们希望,同时又要向干部群众说明实情,不断调整变革的步伐,使之能够被人们接受,使国家保持稳定。他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在此之前,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有着十几亿人口、正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国。
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很值得钦佩的。试想,在改善这么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中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在20世纪,有哪个领导人对世界历史产生这样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力?
“我要写的,不只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
记者:写这本书,对您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傅高义:了解邓小平的想法最困难,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我也无缘跟他当面交谈,所以一切只能依靠间接的材料。《邓小平年谱》出版以后,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不少方便,但也仅仅局限于知道他在某个时间做了什么事。至于他为什么那么做,当时的考虑是什么,却不容易搞清楚。
记者:您怎么解决这个困难?
傅高义:我只能尽可能多采访一些曾经在他身边生活过、工作过的人,以求尽量走近他。我多次到中国做短期访问,也曾经较长时间住在北京,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一些中国的党史专家、高干子女,以及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干部。
10年来,受访者估计有300多位,其中还包括李光耀、卡特、基辛格等一些中外政要。这些人里,很多人都对邓小平评价很高。卡特总统评价说,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李光耀则告诉我,在他见过的人里面,没有人能超过邓小平。
我还走访了邓小平曾生活过的地方,如太行山区、四川广安、江西瑞金,以及他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重庆与成都。从当地学者与干部的口中,以及当地博物馆的资料与实物里,我获得了更丰富的信息。走访的过程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记者:如果不能确定邓小平当时的内心想法,您如何在书中向读者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邓小平?
傅高义:我采取尽量客观的方式,收集更多的资料,试着把当时的环境、背景、各种因素尽量真实地呈现出来,帮助读者来理解,他当时为何要这样做——当然,最终还是需要依赖读者自己来判断。我想,在没有资料直接证明他的具体想法时,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作为一名学者,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客观地写作。
记者:这本书里还涉及很多其他历史人物,您对他们做过研究吗?
傅高义:写作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现新课题,催促我去了解更多的人。比如在开始写作后一两年,我发现陈云对邓小平的作用很重大,于是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去研究陈云,阅读关于他的资料。
这本书虽然名字叫《邓小平时代》,但是我要写的其实不只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我更想告诉读者的是:3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伟大变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由谁主导的,影响又如何。
“‘传世’两个字,是我写这本书的‘野心’”
记者:这本书本来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具体是哪一个层次的读者?美国的学者、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又或者是所有的美国人?
傅高义:我心中的读者,是那些受过一般教育的美国普通老百姓。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当时跟我一起念书的小镇上的同学,后来大多并没成为专家,也没成为知识分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有兴趣来读我的书,并能喜欢它。因此,我不使用太专业的术语,不想谈得太深邃,因为我必须保证如我小镇同学一样的读者能读懂这本书。我曾把这本书拿给同学们看,他们看完后告诉我:“你写得太详细了!”
与一般的哈佛大学教授不同,我从小就有一批很平民的朋友。我自信比其他的大学教授更为了解美国社会的底层,也许他们不乐意为这些底层人士写一点东西,我却很乐意。
记者:您对自己这本书评价如何?
傅高义:尽管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学习,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如果以后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人,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我会不断修订与完善这本书。我的一个愿望,是几十年后,那时的人们如果想了解这个时代,了解这个时代的中国,他们会觉得读《邓小平时代》是个不错的选择。“传世”两个字,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全部“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