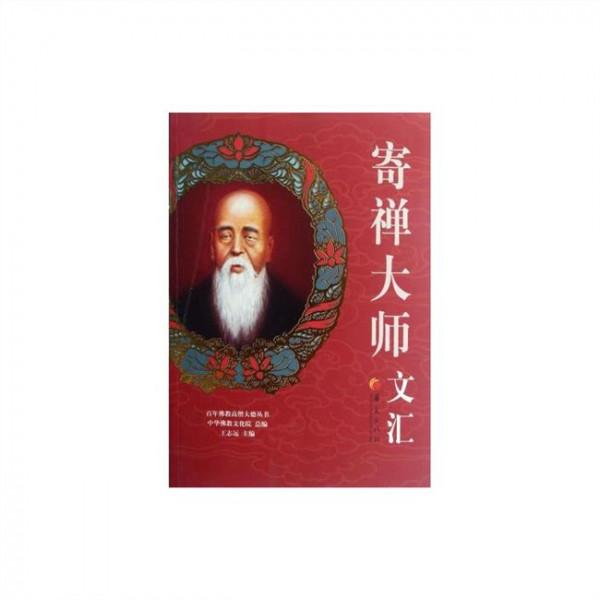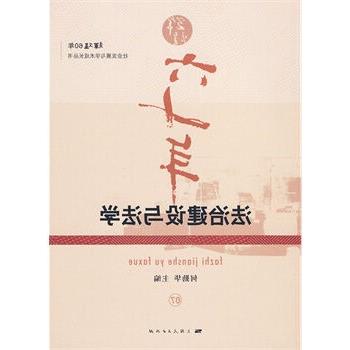中国法学精英的百年命运
这是一群早在青年时代便已蜚声海内外的法学精英,他们影响着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他们的遭遇折射出中国法学百年来的兴衰起伏,他们——就是这部法学巨著的主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编著者。
走向法治的中国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张友渔、潘念之、王铁崖、李浩培、韩德培、江平、关怀、高铭暄、沈宗灵、吴家麟、王名扬。
翻开相隔二十多年的两个不同版本的法学卷编委会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无法让人忽视的名字:
张友渔, 《法学》卷(第一版)编委会主任,原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潘念之, 《法学》卷(第一版)编委会副主任兼宪法分支主编,中国法学会顾问,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
王铁崖,《法学》卷(第一版)编委兼国际法分支主编,国际法研究院院士,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
李浩培,《法学》卷(第一版)编委兼国际私法分支主编,原外交部法律顾问兼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专门委员,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
韩德培,《法学》卷(第一版)编委,《法学》卷(修订版)顾问兼国际私法分支主编,原武汉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
江平,《法学》卷(第一版)编委,《法学》卷(修订版)主编兼民法、商法分支主编,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关怀,《法学》卷(第一版)编委兼经济法、劳动法分支主编,《法学》卷(修订版)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分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
高铭暄,《法学》卷(第一版)编委,《法学》卷(修订版)副主编兼刑法分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沈宗灵,《法学》卷(第一版)编委,《法学》卷(修订版)副主编兼法理学、外国法与比较法、外国法律思想史分支主编,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总干事;
吴家麟,《法学》卷(第一版)编委兼宪法分支副主编,《法学》卷(修订版)编委兼宪法分支主编,原宁夏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理事;
王名扬,《法学》卷(第一版)特约编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时光飞逝,沧海桑田,再次追忆这些法学精英,才发现岁月并没有抹去他们的闪亮,尽管他们的命运跌宕起伏,尽管他们步履维艰,然而他们却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人们朝着法治社会前进。他们的命运已经紧紧地和“法”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和整个时代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
1901-1949,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民众来说,这是个不幸的社会。然而对于中国的法学界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因为许多后来成为中国法学的脊梁的人物都生于这个时期。在那炮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们一步一步地追寻着自己的法学理想。
韩德培教授1911年2月出生于江苏如皋县,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出国研究生(庚款是上世纪初“庚子事变”后,各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后因美、英等国的所谓“退还”而形成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的留学活动及相应的留学群体),先后求学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
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当时是世界上声望最高的法学院,韩德培当时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在那里做了3年的研究。他能用法文、英文、德文3种外语看书学习研究。对于这3年,韩德培教授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在那3年里,我读的书非常之多,不但读国际私法方面的书,还读国际公法、法律学。
哈佛大学的书在全世界所有的法学院里边是最好、最丰富的,什么书都有。所以这个3年对我一生可以说是收获最大的3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韩德培的眼界和学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正是在那时,他定下了自己的理想:将来也要写出一部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巨著!
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世界史学家吴于宽一起被戏称为“哈佛三剑客”。
1945年,他受著名国际法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教授的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成为武大法律系最年轻的教授。1947年,年仅36岁的他出任法律系系主任。
曾经在武汉大学法律系读书,现在是武汉大学法学教授的梁西说:“现在的韩先生是我们武大最年长的教授,当时的韩先生是我们武大最年轻、最漂亮的教授。他穿着整洁的西装,步伐稳健,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这和我们原来的一些老先生穿着长袍比较起来,我就感觉到韩先生是一种新派的风格。”
在韩德培担任系主任期间,武大法律系名师云集,成为抗战后全国最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之一。但此时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却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从1947年起,他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表达他对建立法治社会的希望和建议。
高铭暄先生是惟一自始至终参与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和韩德培相比,高铭暄的求学之路显得有些曲折。1928年5月,高铭暄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鲜迭”的小渔村里。
1944年春季,高铭暄考入温州中学高中部。其间,由于战火不断,温州中学也不得不搬迁办学,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搬回原址,高铭暄终于能够安心读书了。
由于父亲从事的是司法工作,因此在大学选择专业时,高铭暄的第一想法就是报考法律专业。
当时,各大学都是分别招生,分别发榜。于是,高铭暄就在杭州报考了浙江大学法学院,然后去上海报考了复旦大学法学院。因为国立武汉大学在杭州有招生点,高铭暄回到杭州后又报考了武汉大学法学院。
结果,由于他的成绩优秀,3所大学发榜时,都录取了高铭暄。
经过认真考虑,高铭暄决定选择到浙江大学法学院读书。在他看来,父亲在杭州地方法院当推事,自己在杭州读书,能和父亲住在一起,经常聆听父亲的教诲。而且,浙江大学也是非常不错的学校,由进步人士、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担任校长。
不久,浙大法学院就聚集了一批很有声望的法学家,如宪法学家黄炳坤、法理学家赵之远、讲授政治学的周子亚等。
1947年秋季,高铭暄进入浙大法学院读书。在诸多名师的教诲下,高铭暄受到了严格的法律训练,也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不久,由法学院院长李浩培讲授的刑法课,将高铭暄引上了刑法学之路。李先生说:“因为当年没有聘到刑法学教授,所以自己来讲刑法。”他所教的刑法学逻辑性很强,使高铭暄对刑法产生了兴趣。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省军管会文教部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通知的精神,决定撤销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学院的学生既可以转系,也可以参加地方工作。
而此时的高铭暄既不想转系,也不想就此参加工作,他把继续学习法律的想法告诉了李浩培先生。为了支持高铭暄,李浩培就把他举荐给了自己在东吴大学上学时的同学——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费青教授。费青教授是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哥哥。
费青教授同意接收高铭暄。1949年9月16日,高铭暄告别父母北上,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读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关怀,1927年6月生于河南偃师。解放前,关怀曾在朝阳大学读书。那时的朝阳大学是很有名的政法方面的大学,和东吴大学齐名,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在当时法学界更有“无朝不成院”的说法,就是说只要有法院,就会有朝阳大学的毕业生。关怀在朝阳大学学法律时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
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群最懂法律的人,在法律最需要他们的时刻,他们大多数却被迫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情。
再翻开《法学》卷编委名单一看,不禁唏嘘感慨,27位编委中逝世已经过半,未逝者中还在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者已寥寥无几。”
我们的民族还有这样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只要我们能重视和崇尚我们的精英,中国的法治进程必将加快。
1948年8月,“国统区”的一大批进步学生被逮捕。在党的帮助下,关怀化装辗转到了解放区,在解放区的大学——华北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北京解放后,关老回到北京,接管朝阳大学,参与创建“中国政法大学”(与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同一概念)。
王名扬教授1916年出生于湖南衡阳,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能靠宗族的资助读书。因此,他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一边放牛,一边刻苦学习,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五师范。师范毕业后一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1940年大学毕业后,又考入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张汇文先生。
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因为当时法国正处在战后的恢复时期,1947年未能成行,直到1948年才去法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废除了国民党旧统治的全部法律,新法的制定就成了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诞生,这一年成为新中国新法制的标志年。这意味着国家制度和法律基础的正式确定,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真正全面开始。
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很多后来的《法学》卷的编著者,都在那时临危受命,开始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奉献才华。然而在建国最初的几年,群众运动接连不断,在这种极不稳定的环境中,法制建设的进程受到了严重干扰,一些法学前辈们竭尽全力所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法学前辈们的命运也随着各种运动的起伏而一波三折。
1953年8月,高铭暄毕业后留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任教。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5个组织法通过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组建起草班子。经与中国人民大学联系,法律系领导就把高铭暄派到刑法起草班子工作,包括草拟条文、收集资料等。
高铭暄对《法制早报》说,我国刑法的起草准备工作,早在1950年就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开始,并写出了2个稿子,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只是由于处在建国初期,颁布的条件还不成熟,就搁置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立法岁月里,高铭暄为刑法典的出台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学识、热情、心血和汗水。作为自始至终参与刑法典创制的惟一学者,他提出了数不清的立法意见和建议,搜集整理了不知多少资料,对每一个条文不知作过多少次的草拟、修订和完善。
从1954年冬天到1956年11月,经过2年的努力,刑法第十三稿已经被写了出来。
不久,党的“八大”召开,这次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
在“八大”精神的鼓舞下,刑法起草工作加紧进行,到1957年6月28日,起草班子已经拿出了第二十二稿,这个稿子经中央书记处审查修改,又经过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并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这次会议曾作出决议,授权人大常委会根据人大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第二十二稿进行修改后,公布试行。
但不久,反右派斗争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展开了,“左”的思想盛行,社会上否定法律、轻视法制、认为法律可有可无、甚至认为政策就是法律、有了政策可以不要法律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滋长,刑法起草工作就中断了。从此,高铭暄个人也经历了无数风雨。
1951年底,因工作需要,吴家麟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任教,并担任中国国家法教研组组长,主讲中国国家法课程。1954年,国家首批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吴家麟被评为讲师。就在这一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新宪法的热潮。
吴家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敏锐地意识到普及宪法教育对于新中国至为关键。于是,他挑灯夜读,奋笔疾书,在新宪法正式颁行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论著——《宪法基本知识讲话》,积极宣传新宪法的精神和意义。这本宣传小册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于是新宪法颁布前第一本系统宣传宪法的专著,深受读者欢迎,印刷发行了90万册。
此时的吴家麟对建立法治国家满怀憧憬,他大声疾呼:“现在民主和法治的阳光已经照射出来了,理性的王国已经开始出现了。”
然而,吴家麟没有想到,就在他准备大显身手时,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不但给他带来了无法预料的灾难,甚至一度中断了他钟爱的宪法学教育和研究。
1953年,在导师埃赞曼(EiSemann)的指导下,王名扬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公务员的民事责任》。接着,他又一口气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3年的俄语和日语。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这成为当时轰动整个欧洲的头条新闻。
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这段经历也被王名扬自己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为荣的事情。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958年,王名扬暗自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国后,他志愿教学,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然而,时逢政治运动,他非但没有能够走上法学教育讲台,而且不得不接受了4年的“洗脑”。
“1957年是中国命运急速转弯之年,中国法制与法学也被迫走向低谷。”(引自《中国百年法变》——《南方周末》2004年5月13日B9版)
同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法学前辈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和其它领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被下放者有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者有之,被批判、被打倒、被拖去游行示众、被迫害者有之。然而最让他们痛心的却还是不让他们从事他们热爱的事业,不让他们“亲近”法律工作。难以想象,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群最懂法律的人,在法律最需要他们的时刻,他们大多数却被迫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情。
从1957年开始,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也成为了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他被称为“山中宰相”,意思是他虽没有出面,实际上是武大右派分子的总后台。被称为右派大染缸的武汉大学法律系也被撤消。
韩老的儿子韩铁回忆说:“1957年的时候,我父亲被打成右派。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还非常小。我那时候好像11岁,我妹妹9岁,我弟弟比我小5岁,仅6岁。我母亲曾经试图让父亲到学校找当时的负责人,做一个检讨,承认一下错误,能够有所挽回。可是我父亲没有那样做,那时候他还跟我母亲发脾气,说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头砍了碗大的疤,他都不在乎。”
被打成右派后,韩德培的工资被停发,家里从此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收入。妻子一直是家庭妇女,没有到外面工作过,3个未成年的孩子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无奈之下,韩德培想到了他在武大的挚友桂质廷教授,在离开武大去沙洋农场之前,他拜托这位好友尽可能地给自己的家人一些帮助。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只有好友的资助和家人的温情让远在沙洋农场劳动的韩德培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把这些‘资产阶段右派’不当人看待,生活也是非常艰苦,劳动强度也非常大。我还好,我还顶得住,为什么呢?有人问我,说您以前吃了苦,顶过来有什么病没有,我说没有,就是我心胸开朗,不灰心,精神没有垮,所以我撑下来了。如果我精神一垮,还有许多人会上吊自杀,我绝不上吊,绝不自杀。”在回忆往事时,法学家韩德培用平淡的语气描述他当时的处境。
高铭暄:无奈之下请求上级让他搞医学研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斗罢“牛鬼蛇神”,再斗走资派和“臭老九”。高铭暄也受到了冲击。1969年10月,高铭暄被指派到京郊的一家炼油厂劳动锻炼。一个月后,中国人民大学更是被撤销,高铭暄和学校的大多数教师一样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但无论处于怎样的逆境,他都没有改变研究刑法的信念。
上世纪70年代初,因北京一些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导致师资力量缺乏,1971年,高铭暄等90余名原中国人民大学中青年教师被调回北京,分配到北京医学院工作。
当时,高铭暄担任教务干事和宣传干事,就是跑跑腿、写写简报、放放电影。做了几年行政工作之后,高铭暄觉得这样的工作实在乏味,就向北京医学院革委会一位领导请示:“我原来是搞法学研究的,现在,法学用不上了,能不能让我搞点医学研究?”
经领导同意后,高铭暄开始研读中国医学史教材和法医学著作,并撰写了《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王安石对我国医药事业的贡献》等文章,分别在有关报刊上发表。
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高铭暄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学校。
张友渔:群众叫你低头,你低头就是了,完了再抬头嘛
曾经参与主持起草两法的张友渔先生在“文革”期间,成了被揪斗、被游街示众的对象。
由于有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面对眼前的浩劫,张友渔先生倒显得十分豁达。每天中午批斗完回来,他吃两个窝窝头(他是山西人)后,马上就睡着了。开批斗会的时候,也从来不和群众硬顶。他对他的夫人韩幽桐说,现在是群众运动,是抵抗不了的,群众叫你低头,你低头就是了,完了再抬头嘛!
张友渔先生是平反很晚的一个法学大家,曾担任过中国法学会会长的王仲方在《出狱》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许多受迫害的同志都陆续平反,张友渔却因一段历史问题耽搁下来了……于是我去找了薄一波。薄老非常认真负责,做出有力证明,使张友渔同志得到平反。”
王铁崖:在恶劣的条件下,他与其他人一起,竟然全译了一部经典性的国际法世界名著《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
中国少有的几个国际大法官之一、被称为国际法学界“长青树”的王铁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后,被错划为右派,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到图书馆整理资料。虽然身处逆境,他仍怀着对国际法的热爱,编辑了一本《海洋法资料汇编》,又与他人合作翻译了《海上国际法》。他还自己翻译了著名国际法学者凯尔森的著作《国际法原理》。这些得之不易的学术成果,都在日后获得了它们应有的学术地位。
“文革”期间,王铁崖被下放到南昌鄱阳湖农场劳动两年。回到学校,仍被分配干体力劳动。但在恶劣的条件下,王铁崖竟然与人一起,全译了一部经典性的国际法世界名著《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
王名扬:“国家不会让一个博士总是挑大粪的”
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党支部于1960年11月21日列举了王名扬“极其反动”的几大“罪状”:一,回国后从未主动交代其国内外社会关系;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抗、抵触;三,对各种运动抵触不满,对政治十分抵触;四,听资本主义国家广播,可能是美国之音,而且听时将门关上,有人找他也不开门;五、差不多每天吃晚饭后出去,干什么不清楚,11点才回来;六、对工资待遇级别不满;七、对党的各项措施均不满意;八、暑假中有紧急翻译任务,领导叫他参加,他说暑假是他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文革开始后,因为他与法国友人通信,被怀疑“里通外国”,送进“牛棚”隔离审查,多年积累的书稿也被付之一炬。1969年,又被遣送到河南固始和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去就是10年。
对于在农村长大的王名扬来说,种菜、挖水渠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不在书海泛舟却在“牛棚”面壁思过,无论如何都是一段痛心疾首、不能忍受的经历。“再忍一忍吧,国家不会让一个博士总是挑大粪的。”妻子千里迢迢从东北赶过来看他,止不住泪如雨下。
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也是江平先生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在这一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他陷落到命运的低谷,一年内经历三大挫折。第一是陷入“政治地狱”。在当时的“引蛇出洞”的政治政策下,他以赤子之心坦陈意见而落入圈套,成了第一批“右派”分子。
在那个一切以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这个帽子对一个满腹才学、充满理想的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第二是家的离散。江先生与前妻在留苏期间相爱成婚,双双返国,却在政治风暴下,婚姻不能保全,导致家庭离散。江先生受尽世态炎凉的折磨。祸祸相连,江先生在心伤之际,又遭第三个厄运。在西山改造的一次劳动事故中,隆隆驰过的火车碾碎了他一条腿。
同样受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法学家还有很多:
沈宗灵,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后来因需要回校从事编译工作,但十年动乱间仍遭隔离审查,直至1977年才正式重返讲台。
潘念之,1953年受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1955年后,任华东政治学院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
吴家麟,1957年5月因为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发言,被打成了右派,并被发配到北京南苑农场劳动。
陈盛清,1957年因建言调动法学界旧专家教授的积极作用,被批判“为旧法人员鸣冤叫屈”,划为右派,1958年初夏被发配到大别山区鄂东麻城进行劳动改造。文革后经受了“触及灵魂”的肉刑批斗。1978年冬平反。
受到影响的不只是法学家本身,还祸及妻子儿女。陈盛清告诉记者,“文革”时他们的孩子被称为“***”,在升学、工作、婚姻上都受到歧视,不齿于人。
陈盛清教授在《在“反右”的狂风暴雨下》中曾指出:“20年后,包括我在内,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被改正的达54万多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99%以上。”
令人感慨的是,这些昔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前辈们后来却很少谈及那段历史,就是在写回忆录时也是轻描淡写,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豁达的胸怀,或许是他们不希望再让世人看到那场灾难,毕竟,这样的回忆是一件太过残酷的事情。
1980—2006: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世界
1980年以后,社会趋于稳定,各项事业也开始按正常的轨道发展。许多法学大家不计个人得失和过去的遭遇,纷纷复出,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这二十多年里,《法学》卷有了第一版,又有了修订版。然而就是从第一版到修订版,世事变幻,时光流转,物是人非。曾经为一本辞书而奋战在一起的战友,在同一个时代被不同的命运分隔在了不同的世界里。
“再翻开《法学》卷编委名单一看,不禁唏嘘感慨,27位编委中逝世已经过半,未逝者中还在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者已寥寥无几。”《法学》修订版主编江平先生在修订版问世时不无感慨。
1988年3月10日,法学家潘念之在上海病逝。
1992年2月26日,法学家张友渔在北京逝世。
1997年11月6日,国际法研究院院士、国际大法官、周恩来总理任命的外交部国际法顾问,与韩德培齐名的“两培”之一的李浩培先生在海牙遇害去世。他逝世后,联合国的旗帜为他徐徐而降。
2003年1月12日,国际法学家、前南战犯国际法庭法官王铁崖在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90岁。吉林大学法学教授邓正来在纪念王铁崖先生的文章中如此评价他:王铁崖先生的成就是世界性的,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整个世界。
逝去者和在世的人自然是天人永隔,令人伤感惋惜,而在世的许多前辈们也因为年事已高身体不便等原因已不能进行相关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法学界的巨大损失。而既健在又还在从事法学研究的前辈已少之又少,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泰斗。就连他们的许多弟子,也已是所在领域的大师了。
《法学》卷编委中一些健在的前辈们不顾年老体迈,依然在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进行着法学研究或教育工作。
关怀教授在退休之后被学校反聘,一点也没有闲着,除了在学校指导博士论文以外,他还担任着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北京市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即使这样忙,他还是丝毫没有放松学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社会学卷》的主编就是他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他还抽空为《工人日报》写专栏,为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理论指导。
吴家麟从宁夏大学退休后回到老家福州颐养天年。但他退而不休,仍然天天关注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情况。
1993年即已退休的沈宗灵,直到2000年还亲身教导着一批研究生的学习,学生们常到沈老家中来登门请教,两杯热茶,一句问候,师生相对而坐,促膝长谈。
并不是所有的老法学家都还在从事法学研究和教育。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也不是他们不爱法学研究。而是时间——对于这群耄耋老者来说,上苍留给他们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尽管他们心底无法忘掉自己的法学事业,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为了提携后学,2001年,高铭暄不再担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他说:“我希望年轻的学人更快地成长和成熟起来,担当起组织和推动中国刑法学发展的重任。”
2003年,高铭暄也不再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暨法学组召集人。他说,他想利用余生做一些有利于中国法学发展的事情。
当记者再次和高老联系时,他委婉地拒绝了采访。他说:“现在我病了,很多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休息。我已经辞掉了所有的工作,也不方便接受采访了,请你去采访其他的法学家吧。”
在有着110多年历史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园里,95岁的韩德培是最年长的教授。这位几乎与20世纪同行的法学家,一生之中,见证了法律科学和法学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兴衰沉浮。
如今,他已是公认的我国国际私法学权威,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法学教育家。当记者通过电话与他联系时,他告诉记者:“我的身体不好,听力也不行了,咱们还是通过写信交流吧。”听筒的这边,记者分明听到的是韩老吃力的喘息声。
被誉为中国行政法学的“普罗米修斯”的王名扬先生,在1985年作了一个个人的学术计划,打算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5本行政法学的作品,即《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
但是,时光流逝,5部作品的蓝图看来难以实现:1987年出版《英国行政法》的时候,他已经71岁;两年后,又出版《法国行政法》。等到1995年出版《美国行政法》,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在第四本书《比较行政法》的书稿写完4章时,由于身体的原因,王老感觉到“力不从心”了。他不无遗憾地对人说:“也许,另外两本不能完成了。”
郁达夫说过:一个民族倘若没有伟大的人物是悲哀的,倘若有了伟大的人而不去崇尚,则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法学》卷的编者们对于中国的法学界来说,无疑都是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伟大不只是他们编了多少辞书,出了多少著作,更重要的是留给后辈们的精神财富——
在艰难困苦之时尤能潜心研究学问,在内忧外患之时不顾个人安危,在颠沛流离命运起伏之时不坠青云之志,为自己热爱的法学事业而穷毕一生的经历。
前苏联著名诗人布留索夫说:如果可能,那就走在时代的前列,如果不能,就同时代一起前进,但是决不能落在时代的后面。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似乎并不具备走在时代前列的能力,但是至少我们的民族还有这样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只要我们能重视和崇尚我们的精英,中国的法治进程必将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