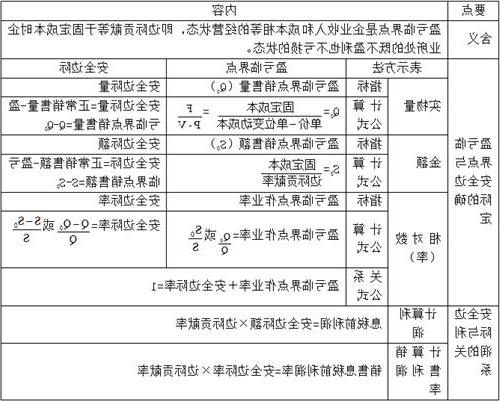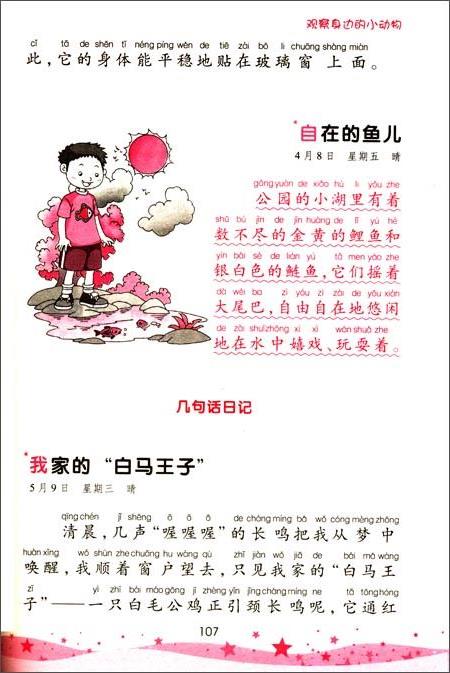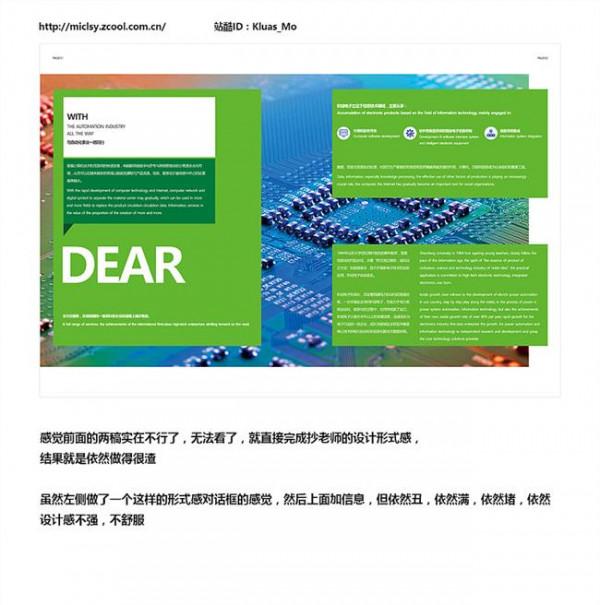俞吾金老师的审美 【逝者】我与俞吾金老师的几件小事
“其实(俞吾金老师)手术后医生就说不乐观,不过术后恢复情况一度比较好,能讨论哲学问题,思路很清楚。没想到突然就去了。不过去得比较安详。”
今晨,一位同学在微信群里如是说。
对于一位智者而言,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还能讨论哲学问题,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举办,“狮城舌战”成为那一代学子的共同回忆。1995年,我入中学预备班。班上的大队长天天捧着一本《狮城舌战纪实》翻看。她说自己的偶像是姜丰,理想是成为中国的“奥尔布赖特”。
2001年,我在复旦大学专业介绍手册上看到了哲学系。模糊记得当年载誉而归的复旦大学代表队有一名来自哲学系的总教头。大概就是这种好感推了我一把,稀里糊涂在志愿上填了哲学系。命运使然,一不小心,进了。
后来才知道,曾经数年,还真有不少热爱文科的孩子,因为狮城舌战考了复旦,选择了复旦的国际政治系、哲学系。
很多同学听说俞老师近年痛失爱女(与我们年龄相仿),夫妇俩极度伤心。同学们达成默契:作为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要尽量避免让俞老师触景伤情。万一在校园里撞到他,一定要低调再低调,不可露半点轻佻。碰巧,那几年,俞老师没有给本科生开课。我们内心悬着的警报自动消除了。只是,每一次系里的各种大会上,大家禁不住在主席台或前几排搜寻俞吾金老师的背影。似乎看上一眼,知道他过得还不错,就是好的。
·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解放日报》的记者。因为所在版块关注学术,反倒跟俞老师有了交集。
还记得我和他之间的第一次深谈。那时,我关注到他在复旦附中给学生讲了一次哲学。考虑到报纸上的学术演讲栏目必须能够深入浅出,我估摸着这样的演讲会适合在我们这里发表。
但俞老师毕竟是大学者,注定是事务缠身,研究的又是精深艰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讲稿涉及繁杂的口语化转化、重写,还要依然确保一定的学术含量和底蕴,他会有时间这样折腾吗?
没想到,一个电话过去,俞老师欣然答应了。
稿子很快来了。字里行间,处处有听众意识,一看就是给中学生讲哲学的启发式口吻,用语讲究,却丝毫不给人距离感、玄乎感。我这个编辑都没再做多少后续的工作。
此后多次合作,发现俞老师有一颗很愿意给大众讲哲学的心,而且他总是能够深入浅出,我们有了邀请他在《解放日报》上开专栏的想法。惴惴不安的去跟他商量,他爽快地答应了,栏目取名为“哲学随笔”。
由于哲学思考几乎就是俞老师生活的一部分,而他又热爱观察和思考,我们很少需要刻意去催稿。慢慢地,跟他聊选题,也不再担心自己出语幼稚可笑。反正,俞老师从不跟我们计较。
在读俞老师来稿的过程中,发现他非常喜欢引用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的“人生四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人生三境”。他一直认为,这背后的“超越思维”是拥有丰富多彩、卓尔不群的人生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之一,因而时时向公众介绍。我想,这也是他为自己立下的追求。
数周前,我邀请鲍勇剑教授在我们的“思想者”栏目发表讲稿。这位如今以文风纵横捭阖著称的学者,早已是沪上知名的专栏作家,行文一贯“穿越”;唯独有一个章节的开始,引用了俞吾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出发对“做了才知道”的解释。
而在稍后收到的鲍教授的个人自述中,他提到自己“也是1988年复旦大学新加坡亚洲大专辩论会冠军队成员。(正因为这个好成绩,国家教委决定本届及今后各届的这一比赛均由复旦大学组队参赛。也才有了如今成为经典回忆的‘狮城舌战’。)”
是怎样一种念念不忘,让一个当年的复旦学子、今日早已拥有自己的学术成就的学者在多年后,依然在自己的简历上记上这样一笔,又引用老师可能在多年前与他切磋过的某个观点?
我小心翼翼地保留下了这段对俞吾金教授观点的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