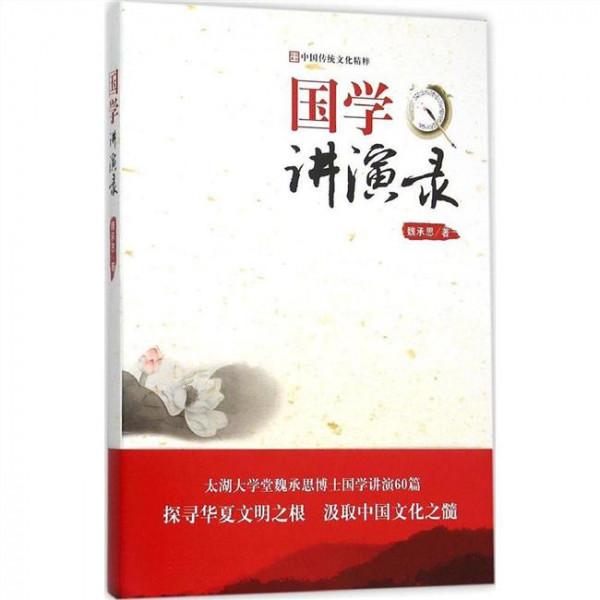俞吾金讲演录 《汇演》:俞吾金:走出观念主义的怪圈
据复旦新闻文化网报道,2014年10月31日凌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俞吾金教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6岁。就在今年7月13日,俞老师完成了他给一篇博士论文撰写的序言,《走出观念主义的怪圈》,7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刊发了此文。
在文中,俞先生这么写道:“要走出这个观念主义的怪圈,或许应该记住马克思下面的教诲: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汇演在此全文刊登俞先生的这篇作品,以饕读者,并借此怀念俞先生。
记得中国古人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事实上,在文字与作者之间做比较,本身就富有诗意。当蒋小杰把他厚实的、沉甸甸的博士论文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放在我的桌子上时,我油然而生的,正是这样的感受。
与某些思想上缺乏定力、观点上随波逐流的博士生不同,蒋小杰从一年级做开题报告起,就明确表示要把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有趣的是,他一条道走到底,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真有郑燮所说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味道。
蒋小杰治学,不光有明确的意向,也有顽强的意志。众所周知,施特劳斯的研究资料浩如烟海,要从中理出头绪来已属不易,更遑论形成自己独立的、批判性的见解了。然而,蒋小杰并没有知难而退,他集中思想,心无旁鹜,一本接一本地阅读着相关的资料,终于找到了“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个重要的切入点。
事实上,近年来哲学博士论文的主题越来越多地聚焦到实践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上,因为人们在探讨任何哲学问题时都无法回避以下双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第一重关系又是以第二重关系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因为人并不是赤裸裸地、直接地面对自然界的,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媒介才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
而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尽管经济关系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真正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和高度的却是政治关系。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利普塞特所说的,人首先是作为政治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蒋小杰之所以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的主题聚焦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上,其目的正是要把握这个最重要的思想维度,并通过它,进一步探寻并守护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究竟从何处着手去探寻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珍宝呢?经过深入的阅读和反复的思索,蒋小杰决定把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置于现代性语境中加以考察,他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一方面,要对政治哲学获得整全式的理解和把握,就应该找到一个与之相匹配的观念,毋庸讳言,“现代性”(modernity)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整全性的观念。
事实上,施特劳斯正是把以进步观念为引导的观念整体理解并阐释为现代性的。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危机也深藏在现代性危机中。只有从价值的层面上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合理元素,恢复启示与理性或哲学与政治的平衡,才能告别虚无主义、走出现代性的危机。
毋庸讳言,在“观念主义”(idealism)[在英语中,idealism这个名词通常拥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唯心主义”,它主要关涉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第二个含义是“理想主义”,因为ideal可以解释为“理想”; 第三个含义是我们在文中使用的“观念主义”,因为idea 可以解释为“观念”,而观念主义就是试图完全撇开现实,只从观念(包括文本上的思想)的被接受、被批判或被抛弃来阐明现实生活的变化。
马克思曾经辛辣地嘲讽过这种观念主义:“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溺死,是因为他人的策略的思想迷住了。如果被他们的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它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的语境内,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的理论似乎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或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理论,就像马克斯•韦伯倡导的“新教伦理”、雅斯贝尔斯推重的“轴心时代”理论一样,作为观念主义的代表作,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
然而,观念主义者正是以黑格尔所主张的“现实和观念的同质性”(homogeneity of actuality and idea)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的。
换言之,他们把观念上的东西与现实生活中的东西直接地等同起来了,以为在观念上或书本中出现的东西,也必定会在现实中出现。
事实上,要拨开观念主义的迷雾,看清楚现实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并揭示出现代性的秘密,就应该从黑格尔所主张的现实和观念的同质性返回到康德所主张的“现实和观念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of actuality and idea)上。
其实,只有认可这种异质性,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东西才会向我们敞开。遗憾的是,施特劳斯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异质性,并视之为自己反思的出发点,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在观念主义的旧靴子里打转。
首先,像其他近代政治哲学家一样,施特劳斯也喜欢侈谈natural right 这个含糊不清的观念(natural right这个英语词组有各种不同的译法,如“自然法”、“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蒋小杰和另一些学者主张把它译为“自然正当”。
毋庸讳言,right确实蕴含着“正当”的含义)事实上,在我看来,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并翻译这个词组,只要他们把“自然”与“法”、“权利”或“人权”放在一起,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法”、“权利”或“人权”这类观念永远不可能在“自然”中形成,因而也不可能在自然的语境中被使用,而只可能在“社会”的语境被构成并被使用。
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法”、“自然权利”或“自然正当”,就像说“方的圆”或“木的铁”一样,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自洽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
其次,施特劳斯试图通过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来挽救现代性面临的危机,然而,这种回归也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就像柏拉图在叙拉古的遭遇一样。即使从政治哲学家的理念上来看,柏拉图关于“哲学王”和共和国(republic)的理想也是不切实际的,犹如马克思所批评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5-406页。)
由此可见,无论是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回归,还是他对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的丰富性”或“埃及的肉锅”的留恋,都无法真正地破解现代性的困局和危机。
最后,我们发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分析还未深入到人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在我看来,要使这个维度向当代人的意识敞开,就必须先行地区分“人性”(human nature)和“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这两个内涵殊异的概念。
前者指人的自然属性,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饮食男女”; 后者则指人的社会属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毋庸讳言,人性作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不会变化的,但人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会变化的;与此不同的是,人的本质是在后天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会变化的,也是可塑的,而这种可塑性正是借助于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和审美观念等才得以实现的。
于是,我们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又通过对人的本质形成机制的反思而转化为对上述领域中流行的观念的批判。诚如康德所指出的:
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宗教想借口它的神圣立法、想借口它的尊严,试图避免批判,可是,这样一来,它们恰恰就引起别人对它们的正当的怀疑,而不能要求人家真诚的尊敬了,因为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开考查与考验的东西,理性才给以真诚的尊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Aⅹⅱ)
尽管康德自觉地意识到了现实和观念的异质性,从而为破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新的思维进路,然而,我们发现,康德所倚重的始终只是单纯思想领域里的批判活动(critical activities)。也就是说,这个思想上的巨人归根到底仍然是观念主义的囚徒。正如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所写的:
我是你的囚徒,
我和我的一切都必然任你摆布。(参阅《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十四行诗),朱生豪译本)
在我看来,要走出这个观念主义的怪圈,或许应该记住马克思下面的教诲:
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我们应该学会把“武器的批判”(weapon’s criticism)与“批判的武器”(critical weapon)严格地区分开来。归根到底,真理既不在柏拉图所创立的“理念论”(theory od idea)中,也不在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实践智慧”(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中,而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唯物主义”(practical materialis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