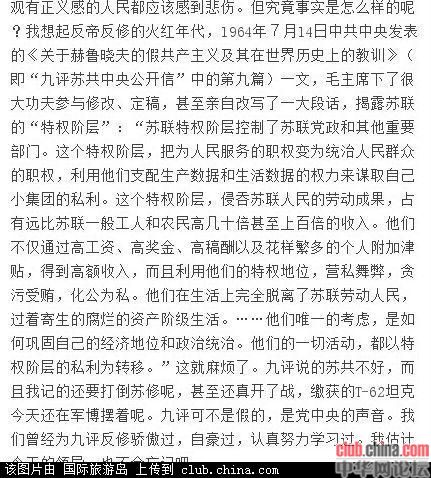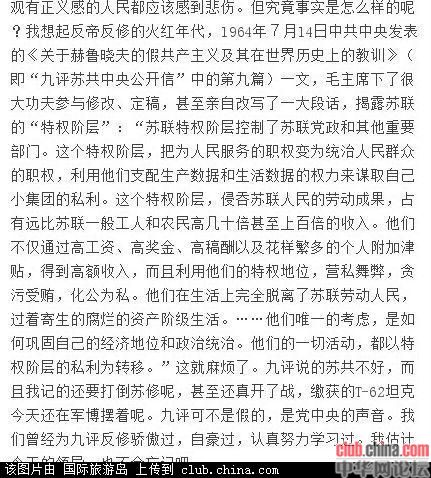胡德华孔丹秦晓 秦晓回忆:我和孔丹质疑文革 戏剧性被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高一的学生刘辉煊成立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绌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近观毛泽东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站在金水桥前面维持秩序。头一天晚上都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中待命,第二天一早就站到金水桥前面去了。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准备。后来,有些还不是首领的人也上去了,队伍里好像很多人都有意见,就乱了。
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有上去,我们就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照了相。我们在旁边,总理在中间。金水桥那么长的一溜儿,总理就一段、一段地跟我们照相。后来,我是跑到新华社要的照片,现在还保留着。
"八三一"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刚走下天安门,有一个外地学生拦主席座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任,威胁了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个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是从八一学校来四中的。以前上课经常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老师说,你讲的什么呀?我都听不懂,把老师倒给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争执中,他扇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成"英雄"了。
我是"九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上的天安门。记得上天安门的时候,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去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毛主席走过来的时候,举着手看着我们。当时,我们离得很近,见到主席很激动,欢呼声很大,但秩序还好。不过,我看到主席目光是一个不很喜欢我们的目光。当时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感觉,就感到主席不喜欢,或者是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就这么看着我们。面对这么疯狂的场面,我觉得他也担忧了。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我的这个感觉。
第二件事就是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头,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俩的长谈主要是主席讲,刘听。主席讲的时候还打手势,像是个认真的谈话,超出了在这种场合上谈话的时间。
我知道的"西纠"
"西纠"(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经关闭了。成立宣言上把西城几乎所有的中学名字都写上了。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
"西纠"总部最早也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所以经常是一帮子人,一窝风似的到我们家去。我妈妈是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住下两个"连"的人,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了某种权威。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送啊?于是反映给我们。"西纠"就发了第一号《通令》,说《毛选》可以卖。
那时,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抄家的方式我们是不主张的,所以,专门发了道《通令》去规范。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
一些红卫兵就把他们都给赶到北京火车站了。而原籍所在地不接受,北京也不接受,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混乱一片。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的人跑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这事。
"西纠"也就存在了三两个月吧。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总理帮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串联去了。
当初成立"西纠",并不是要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主张讲政策。面对红卫兵中出现的越来越不讲政策的现象,我们也感到担忧。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起来后,必定会出现这种现象,觉得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
"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里,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因为,红卫兵纠察队毕竟是那四五十个学校共同认同的组织。但是,"中央文革"认为"西纠"有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就硬是把我们给搞垮了。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是很严重的。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是抄家,然后是扫地出门。搬家的时候,我正在外地串联呢,是家里几个孩子和一帮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家。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我爸妈一间。
我妈妈是睡在柜子上的,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陈毅之子)谈恋爱的时候,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也不是要看我们家怎么样,只是表示她应该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
还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出来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总理也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时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就站起来了。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也是心知肚明。
从质疑到抗争
1967年上半年,孔丹被放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很理性地去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去了。我们认为中国这事是让"中央文革"搞坏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那么深,也没想直接去质疑毛。后来,我们就办了个小报,起名《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去调查。
第一篇社论是孔丹主笔的,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很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现在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文革"中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
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都没有反省,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
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
那天,正好是学校副校长在广播室播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孔丹主讲,刚开始讲,就被他们掐断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管会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是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江青的,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抓孔丹的时候挺戏剧性的。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跟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他长得瘦瘦的,像个螳螂样。他进来一看,本来奔着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这里,一下紧张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那个院子是个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人听到有人正在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赶紧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然后,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管会决定对我拘留,还搜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的草稿。
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要经受铁窗烈火、戴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升。我以为会把我往囚车上一押,我那感觉就出来了。结果出门一看:没车?我还想,怎么没车呀?结果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了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
就这样大概关了有两个多月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还是不允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我们也没理睬他们,后来就自己去内蒙古插队了。
当时对离开北京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很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那时候,对理想主义的改变和破灭,仅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想很多问题,想文化大革命、想毛泽东,林彪出事后想林彪的事。还有,我们和一帮朋友通信讨论,看书、学习,当然也看些小说。
当时的内部书籍: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我们都找来看。黄皮书是小说。优秀的作品有《冬天的童话》、《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娜娜》等,还有一本是苏联的《这位是巴鲁耶夫》,那是很现代的、意识流的作品,用的全是现代语言。灰皮书是一些政治类的书籍,像《托洛茨基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篇非共产党宣言》等,也看了不少。白皮书是一些史料。
大概是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从1968年底到1972年5月,插队的时间已近四年,那时已有不少知青返城了。可能是内蒙古的知青少,地方大,国家给的招生名额就少一些。当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年,华国锋搞了"洋跃进",燃化部进口许多设备,需要懂外语的工程师。
于是,就到我们学校里招学工科的去培训外语。我被招上了,集中到北京学外语。当时因为可以解决进北京户口,请的老师也都很好。实行听、说领先的口语化教学,以应对将来跟外国专家打交道。集训了大概一年半,每天就是听啊、说啊,老是在练习。等我出来的时候,燃化部已经分成好几个部了,我1976年被分到煤炭部。
两次大惑,走出乌托邦
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没有哇哇地哭,但心里总觉得总理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四五"事件时,我也到天安门广场去了。那时候去天安门的人真不少,大家都很激动。广场上的花那么多,越堆越高,而且,还有不少人在广场上演讲。每个人都在议论、思考。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想到今后的国家命运,不只是悲痛,还有理性。
至于红卫兵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什么,我觉得,就是被打到最底层后的反思。我首先要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思想是比较幼稚的,可能跟别人比,还没那么疯,但也是头脑发热。如果说还有些理智,但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所以,首先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但我们在"文革"中对"四人帮"是有抵制的,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也是难以理解,甚至是怀疑的,在这场运动中也受到了迫害。
我自己一生有两次大惑,一次就是我21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直到林彪事件出来了,对主席有了新的认识,慢慢把这个"惑"破了。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先从经济领域看社会问题,然后,又慢慢接触一些所谓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论。
看的东西多了,就开始琢磨:不对啊,现代化和现代性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惑起来了。这第二次大惑就是对现代性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大的转变。
我们这代人有"文革"和改革开放两次大的反思,反思留下科学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有经历,参与了中国走出乌托邦的社会变迁。我今年六十多岁,我戏称自己是"60后"的一代,其实是在唤醒、鼓励自己保持活力。因为我知道学习、思考、探索还要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