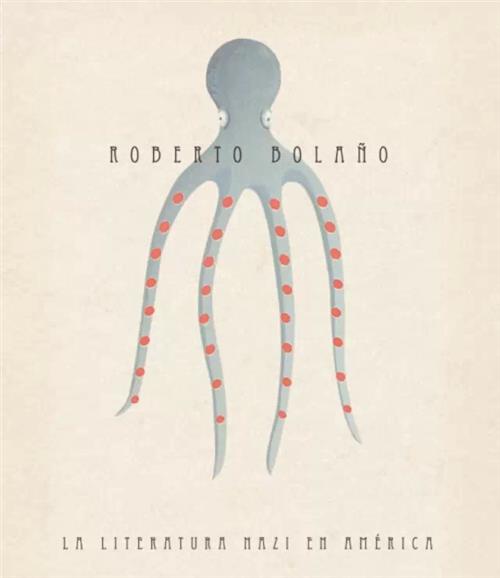巫昂译本控 巫昂︱读外国书 你得先成为“译本控”
某光头教授在自家朋友圈吐槽黄灿然翻译的布罗茨基《小于一》,说译得不好。我凑巧买了这本书,翻开里面去张望了一下,说不好是对的,语言太细碎,气场不够大。好的译作,需要译者与原作者气质登对。但是,布罗茨基不是普通人,而黄灿然是翻译界的劳模,是个勤奋踏实工作的普通青年。
再看封底,这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大师批评译丛”有六本,黄灿然译了一半儿,除了布罗茨基的这个随笔集,还翻译了库切的《内心活动》和希尼的《希尼三十年文选》,勤奋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黄灿然已经算好的了。”我跟光头教授最后达成共识,都知道翻译这行当,说着轻便,做起来特别难。有一阵子,我跟朋友们在一起重新读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我所买的上海译文版的《都柏林人》是王逢振的译本,读起来磕磕巴巴,怪不舒服。
这样的译本读完,会觉得乔伊斯浪得虚名,就这也能算作是当代小说短篇小说集里坐头排的?后来朋友手里有个老版《都柏林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译者为孙梁和宗博。我们坐在一起,有人朗读了一篇,相对而言,舒服多了。
于是,推荐外国小说,要连带推荐译者,这成了朋友们互相荐书的常识。小说家阿丁特别推崇胡安·鲁尔福,他专门指出,如果读他的《佩德罗·巴拉莫》,就一定要读屠孟超的译本。鲁尔福是个奇怪而又特别天才的小说家,在他的世界里,人物一会儿是活的,一会儿又是死的,在时间与空间上,总是让人先一头雾水而后恍然大悟,他好像是个顽皮天使,来回穿梭。翻译他的作品得有多难啊,结构没搞清楚,首先就是不行的。
豆瓣有个可爱的小朋友叫做“地中海的鱼”,他会读西班牙语的原著,而且写了个技术贴,分析说如何读懂《佩德罗·巴拉莫》的结构。他将全书每一大部分编号,从1编到69,然后使用六种颜色的记号笔,来分别标注:1.胡安的经历;2.
佩德罗·巴拉莫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3.关于米盖尔·巴拉莫;4.害死阿尔德莱德;5.苏珊娜的故事;6.苏珊娜死后,佩德罗·巴拉莫死前发生的事。这才能够将整个小说的结构梳理清楚,再去翻译,恐怕才算是找到了门径。
作品同样是以结构复杂,穿插错落,出场人物众多著称的,是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是鲁尔福的弟子,他可能从鲁尔福那儿得到了启发。在《百年孤独》的不同译本里面,我对黄锦炎的译本有感情,那是1991年出版的,虽然早在1984年,高长荣就翻译了这本书。
1991年我刚上大学,班里同学集体在读《百年孤独》,掀起大讨论的热潮,黄锦炎翻译得还是挺不错的,至少读之不觉得硌。我记得小说家王安忆给我们上小说分析课,她详细地分析了《百年孤独》的结构和人物,条分缕析,饶是不易,拿的就是黄锦炎的译本。
我读过的,觉得翻译得特别好的,还有柳鸣九所译的加缪的《局外人》。加缪那种满不在乎又敏感的劲儿,被柳鸣九拿捏得很好。
提到卡夫卡,自然叶廷芳先生的译本是最好的,单向街做“卡夫卡之夜”,叶老先生在场,一头白发,稳重深沉,他用德语读卡夫卡写给密伦娜的情书,那声音应该录下来作为史料。
在翻译大家里,见着冯至、董乐山、傅惟慈、王佐良、汝龙、杨宪益跟李文俊的名字,基本上是信誉保证。比方说,汝龙已经得了契科夫的魂,不读汝龙的译本,契科夫在汉语世界里就跟不存在一样。而读董乐山翻译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那叫一个驾轻就熟啊,俨然让开惯悍马的司机去开个QQ,如果《1984》不选择董乐山的译本,奥威尔少了多少神气。
再比方赵德明翻译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几本书,我读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护身符》和《美洲纳粹文学》,一再赞叹波拉尼奥,将他尊为我新版的文学偶像,赵先生的功劳,应该是不能泯灭的吧。
翻译家,当跟作家融为一体,自身也是个作家的底子,这才能撑得起,衬得起,担得起。
而读者要读到好的外国书,不做“译本控”恐怕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