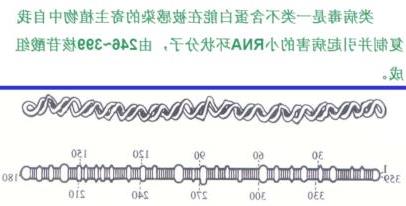田浩江专辑 杨澜工作室专访:田浩江放歌纽约(附图)
杨澜:名剧《唐-卡洛斯》是上海大剧院成立三周年一个特别的安排吗?
田浩江:对,上海大剧院这次是纪念成立三周年,所以推出这个戏。我觉得别有意义。《唐-卡洛斯》是一个名剧,世界名剧,威尔第的名剧。
杨澜:你在其中还是演"菲力浦国王"是吗?(田浩江:对。)你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也演过这个剧的这个角色。当时在意大利演这个角色,人说就像在孔庙前卖文章一样。
田浩江:意大利这个地方因为是歌剧的故乡。我们都这样叫它,所以说,在那个地方演歌剧,他们非常挑剔,尤其是对外国人,尤其是对亚洲人去演他们的歌剧,他们是非常非常挑剔,一字一句,你的声音,你的表演,你的手势,你的眼神,他们都要评头论足一番。
那么,意大利的观众也很不客气,如果他们不喜欢你的话,那一定是要哄你,要哄你下台,所以在我去演的时候,我想我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演这个角色的中国歌唱家。所以在演之前我是很紧张的。
因为这个,种种因素,我刚才说的,所以说做了很多的作业,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演出不错,效果我自己基本满意,我演过40多部歌剧,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为低音来说,我是个base,唱低音的,演的角色大多数不是国王,就是大祭祀,不是大祭祀,就是祖父,不是祖父,就是年迈的父亲,不是父亲,就是一个什么或者是个坏人什么样的,所以很多角色性格都非常复杂。
杨澜:我想起你在媒体上谈过很多从中国到国外去的歌唱家往往是声音条件非常好,而在国内也受过非常严格地系统的训练,但是,在对国外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学,还有比如说他们的宗教、历史这些的修养往往不够,这成为他们发展的很大的一个障碍,那你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障碍?
田浩江:那当然会遇到这个障碍。其实我走过的路可以说是很长的,因为根据距离今天的学声乐的学生们来说,我的经历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我长在文化大革命,做过工人,做过几年工人,然后又去学唱歌,又去到美国,这样一步步走过来,首先我现在很理解这种差异。
因为这是个文化的差异。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走进西方的文化,那么作为歌剧来说,又是像文化中的精品一样,是个金字塔,走进这个里面确实是要付出很多代价。对我来说,首先就是说语言障碍首先要克服。
杨澜:你十五六岁的时候还在北京锅炉厂当工人是吗?
田浩江:对。
杨澜:那个时候去唱歌是不是一种出路?就是离开工厂?
田浩江:我想……,生活当时确实是…有一种压抑的成份。原因大家都知道,对我来说音乐其实是一直在支撑着我向前走的动力。我在学唱歌之前,我就喜欢拉手风琴,喜欢弹吉他,喜欢唱一些地下的流行歌曲,比如说前苏联的歌曲。邓丽君还太早了。当时有一本歌集叫《外国名歌二百首》,很多歌都是从上面来的。所以今天同时代的人听一些从苏联传过来的歌曲很亲切。另外,当时学唱歌也很偶然。
杨澜:听说你去找朋友的时候喊了一嗓子被别人听见了?
田浩江:对。找朋友,骑着自行车去找朋友,当时不想去爬5层楼,就在楼外喊,当时也不懂礼貌。当时正是午休的时间,好像只有知了在叫,我就在院子里大喊这个朋友的名字。朋友不在。另外一个窗户就打开了,一个人探出头来说:"你谁呀,你找谁呀?"我说我找谁谁谁。
他说:"你是唱歌的吧?"我说:"唱歌的?不是。为什么?"(杨澜:人家听出来了!)他说:"你的嗓子不错嘛!来来来,上来跟我聊一聊。"他就把我叫到他家去。这实在是很有意思。
因为这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非常非常的奇特。因为到今天我也记不住他的样子。整个就跟他谈了5分钟话,当时只知道他是某文工团的一个专业唱歌的,他只是告诉我,你的声音不错,应该去找个老师学一学。也许你在这方面可能有所发展。但是现在想想非常感谢他,不晓得冥冥之中不知他是谁派来的,然后给我指出一条路来(杨澜:往那边去!)去吧!
杨澜:你后来其实也跟自己的童年伙伴有在一起吧!包括你那个时候在工厂里一块挥锨抡锤的这些在一起,他们会很奇怪吗?你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歌唱家。
田浩江:我想每个人都有一条路走嘛。所以,去年我记得回到北京来,很有意思的一个聚会,就是跟我5个当年一起跋山涉水去背着个破背包去山上发疯,然后一起谈诗歌,一起谈音乐,一起唱歌的朋友们,工厂的朋友们,又聚在一起,整整谈了12个小时,吃饭、喝酒、谈当年的事儿,一起唱歌,大概歌就唱了至少有5个小时,全是当年我们那些歌,他们都离开了工厂,每个人都做不同的事情。
也有百万富翁,也有作家,也有国家的干部,所以说大家很感慨,因为这么多年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道路,那样很有意思。
杨澜:说到唱歌,你在美国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歌要引起共鸣是要来自同样的一个社会和历史的环境,你比如说你要唱一些苏联的歌或者是唱70年代的歌曲。大陆来的人就会很有反应,但是你要唱邓丽君的歌,可能是台湾人比较有反应,那香港人也有他们的明星,你在这儿会发现,你过去唱的那些歌曲能有知音吗?
田浩江:会有的,会有的。尤其是身在异国他乡,听到自己熟悉的歌曲,这种感觉是特别地丰富,会非常感动。我曾经在美国开过一个独唱音乐会,我叫它"一代之歌",就是说,我唱了从小的时候的歌,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什么这种歌,一直到今天的大家熟悉的一些歌曲,全部都是中国歌曲,台下的观众有台湾人,大陆人,香港人,国内来的,那么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也很喜欢邓丽君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什么这种歌,唱起来,台下的台湾观众坐得就会更直一些,那么唱起我们小时侯熟悉的歌,那么国内来的人就是想跟我一起来唱。
我记得当时我唱了一首歌"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我记得当时我唱了两句唱不下去了。因为自己很激动,所以在掉泪。
我就记得安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全部从国内出来的人一起,异口同声开始接着我的歌来唱,把这歌唱完。当时真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你想我演过这么多歌剧里的一个人,在大都会剧院,在欧洲演出,台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观众,那么这种交流,很多都是艺术层次上面的,给我们自己的同胞中国人唱的时候,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一种,有一种真情的那种可以交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特别好。
杨澜:而且据说过去特别是儿时的歌曲还能够帮助你舒缓上台时的紧张,是吗?
田浩江: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习惯,那就是在演出之前,尤其很重的角色,我在化妆间弹点钢琴,弹一点小时候的歌,比如"北京的金山上",什么"王小二放牛郎",弹点这种歌,弹过十分钟,十五分钟我觉得我的情绪稳定了很多。
杨澜:为什么呢?
田浩江:我觉得,第一音乐有一种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所以我记得当时多明戈敲门进来说:"田,你在弹什么东西呀!怎么这么好听呀!"
杨澜:谈谈你最早到歌剧院试唱的情况?
田浩江:歌剧院试唱?我想如果作为歌剧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在90年大都会歌剧院的试听。当时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正在挣扎的年轻歌者,家还谈不上。当时安排了一个大都会歌剧院试唱,当时我这个钢琴伴奏是弹十个音,错八个音!
(杨澜:为什么会找这么个人来伴奏?)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纽约有几百个钢琴伴奏可以选择。我当时找人找不到,而临时大都会来了电话让明天来听,所以完全没有选择。这个人紧张得要命。
一弹错了声音就非常小,然后不但声音小,还整个趴在钢琴后面看也看不见。有时要与伴奏的人交流,呼吸…..他这么一躲起来,声音又小,你想,第一次试听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出来,完全放弃了,没想到第二天他们打来电话说很喜欢我的声音,再给我安排到大剧院的舞台上给所有的领导听,对于我来说,我是750度的近视眼,摘了眼镜以后什么也看不见。
(杨澜:你不紧张?)紧张!但你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浑浑噩噩的,完全不知所措。当时我记得在一个朋友家借宿,放进了一个隐形眼睛,第二个还没放,掉地上了。三个人趴在地上找了20分钟也没找到,最后就一支眼睛去了。
杨澜:对于田浩江来说,有一件小事使他久久不能忘记,那时在文革后期,与一个落魄的老先生在小酒馆里喝酒,酒过三巡之后,老先生告诉他,他本人曾经是一位歌唱家,因为唱错了革命歌曲的歌词,被人打掉了整整一排牙齿,不仅不能唱歌,连风都挡不住,对于命运多蹇的艺术前辈来说,田浩江当然是幸运的,在国际的大舞台上,他也正实现着几代中国艺术家的梦想。(摘自《文化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