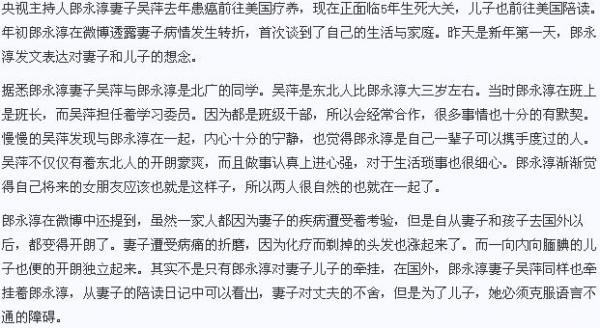郎景和有时去治愈 郎景和:有时去治愈 总是去安慰
郎景和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很大的林巧稚的画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是影响了他一生的人。一生未婚的林巧稚是中国第一代妇产科的专家,也是郎景和的老师。
在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后,郎景和填报了三个志愿的科室——外科、内科和妇产科,虽然填报了妇产科,但郎景和并没有对之有任何特别的情感,直到林巧稚将他留在了妇产科。林巧稚是个很西化的人,每年都从当期的驻院医师里挑选出个男生,而郎景和自己又填报了妇产科室,选他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于是“这一干也五十多年了,我觉得挺好。过去国内还有封建思想残留,病人还会不好意思,现在可不了。要知道,欧美和日本的妇产科大夫几乎全是男的,我们早已克服了歧视。”
其实,在郎景和的办公室里,比这张被镶嵌在玻璃框中的林巧稚画像更显眼的是随处可见的各式各样的铃铛。郎景和曾经说过:“医学是我的职业,哲学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爱好。”后来他又加上了一句——“铃铛是我的收藏”。
在他的家和办公室里,汇集了共计两千多个不同材质、不同样式、不同大小的铃铛,当起风的时候,铃儿响叮当,大概也是一首别有风味的乐曲吧。关于铃铛的故事,始于30年前,当时郎景和在挪威奥斯陆待了一段时间,他是如何与铃铛结缘的,他也写在了《一个医生的故事》这本书中。
执业
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听听郎景和更早的故事吧。
1940年出生在吉林的郎景和是家中独子,家境殷实,唯一的遗憾是母亲是个“病秧子”。每次母亲发病,他都要负责去请小镇上一个姓于的郎中来家里看病。“他总是和蔼可亲,随叫随到。我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郎中后面,看着他给我母亲号脉诊断,每次都能见他拿出一个铝制小盒,里面装着药品、针头等,消毒酒精散发的味道让我觉得很舒服,一剂针打下来,我母亲的病就好了很多,我觉得做医生真是太神奇了。”
这位姓于的郎中,在不经意间成了郎景和的“引路人”,但这并不代表一切就都顺理成章。报考大学的时候,郎景和最初的心愿其实是吉林大学文学系,他其实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高中时就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最高拿过单笔十几块钱的稿费,在当时的年代,绝对是一笔不菲收入,那会儿学校里的甲等助学金才八块钱。
其实郎景和的文艺情怀到今天也依然存在着,但他在当年听从了父母建议该报了医学。“那时候觉得医科好歹是一种‘术’,用以立身比较踏实。那个年代,还是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作祟。”不过在从医多年后,郎景和曾经说:“科学家也许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也许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医学将这两种情感的融合,多少也弥补了他弃文从医的遗憾吧。
病患
医生更多应该给予的是人文关怀
今年已是75岁高龄的郎景和,从医51年来却从未离开手术台,上周他还刚进行了一台盆腔包块的肿瘤手术。有人劝他年纪那么大,其实没必要继续开刀,可老当益壮的郎景和却认为,手术是外科医生的天职和本分。他笑言自己现在常常有三种情况要“站台”,第一,遇见别人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第二,年轻大夫技术已经过关,但是他们需要有他上台才能心里‘有底’;第三,医学是有风险的,遇见有现实复杂情况的手术,为了有个主动担责的人,他也要上手术台。
然而,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失败”是每个外科医生都要学会面对的课题之一。曾经有一台不成功的手术,至今都刻在郎景和脑中,“有一次我们去洛阳办妇产科学习班。有一个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她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马上手术,但是当地的医生、病人家属和她本人都觉得,我们应该给她立刻手术,家属几乎给我跪下了,说等我们离开了洛阳,病人几乎就只能等死了。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虽然时机不好,但我们还是同意了。手术持续了七八个小时,几乎把所有瘤子都切除完了,应该说手术本身是不错的,但在最后关头,这个病人终因为身体太虚弱无法承受这么大规模的手术,还是去世了。”
对于这场最终失败的手术,虽然预估了所有能想到的风险,病患家属全程也都很通情达理,但郎景和还是非常难过,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尽力了。美国名医特鲁多有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成为郎景和的“金句”,“你必须了解,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治好的,这个世界上已知的有三万多种疾病,能完全治好的非常少,很多时候,医生更多应该给予的是人文关怀。”
如何消解从医时的挫败感?郎景和选择闭门自省。每天下班他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一小时独处,回顾一天里自己做过的手术,查过的病人,他的很多篇手术笔记都是在这些间隙中写成的,包括最新的《一个医生的故事》也是。他经常劝年轻医生们,快快走路,快快做事,但一定要有慢慢思考的时间。
当了一辈子的医生,郎景和却坦言自己“做医生越做越怕”,书里亦有一篇文章《医生的“戒、慎、恐、惧”四字诀》,文中剖析了他从医路上的“胆战心惊”。这个四字诀出自一代医界宗师张孝骞,他时常告诫后辈做医生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生都在从医路上战战兢兢的郎景和,自称只是个普通医生,以医德为根基,做着一个合格医者该做的一切事。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本版部分图片摄影/新京报记者柏琳
【选读】
《我给牛接生》
我当然不是兽医,但我给牛接过生。
时间是1966年,我大学毕业两年,做妇产科住院医生。中央卫生部组织“四清”工作队,我成了队员,一方面是参加工作,一方面是接受锻炼。
“四清”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对农村干部进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昆山石碑公社红星大队。当时昆山无法与今日相比,比较落后,又是血吸虫病疫区,虽是江南水乡,却是穷苦之地。
有无牲畜是贫富的重要决定因素和标志。我所在的五小队就是没有牲畜,是出名的落后队。乡亲们颇费周折,让一个老母牛怀上崽,据社员讲,这相当于五十多岁的女人怀了孕。不管怎样,也是喜事。
老母牛临产,进展困难。这可是队里的大事,工作队员要“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忧贫下中农之所忧”。我也赶到牛棚,看到母牛体力不支,得用粗绳绑在棚梁上才能站住。工作队要求不暴露身份、职业,可是情况紧急,咱毕竟是妇产科大夫,接生还是有点经验,就主动“上场”了。
已经到了后半夜,宫缩很差,我从卫生所找来催产素,从牛肚皮的静脉穿刺点滴宫缩剂。我还提出做剖腹产的准备,社员们很同意,积极响应。我开了一张手术器械清单,两位社员连夜冒雨划船去县医院取器械。
宫缩加强,产程进展,出血破水,准备接生。我从未给牛接过生,硬着头皮上,一位老农告诉我,你手进去先抓小牛后蹄,然后将屁股、身子和头拽出来。噢,人是应先出大头后小臀,牲畜是先出大臀后小头,才会顺利。如法操作,接生顺利。小牛出生,众人欢呼!
老牛没奶,小牛嗷嗷待哺。社员们要到常熟牛场去买奶,我又承担起喂养工作。将牛奶装入葡萄糖盐水瓶,加热消毒,温度适合后塞上橡皮奶嘴给小牛吃。怎么喂也不吃,令人焦急。小牛一会儿扑到母牛身边寻找乳头,一会儿到我的胯下乱拱,我灵机一动,将奶瓶挟在两股之间,小牛从我屁股后边正好叼住奶嘴,畅快吮啜。
还挺有劲,顶着我到处转圈。如此喂奶,真为奇景。每次喂奶,社员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赶来围观,“看郎同志喂奶了……”小牛长大了。我裤子后面一片奶渍、泥巴,常有大人小孩跟着看,嘻嘻地说笑。















![郎昆刘岩离婚 刘岩跟郎昆离婚了吗]郎昆刘岩牵手照](https://pic.bilezu.com/upload/9/21/921d7efab5eb8813bd25c7f7ab8294c7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