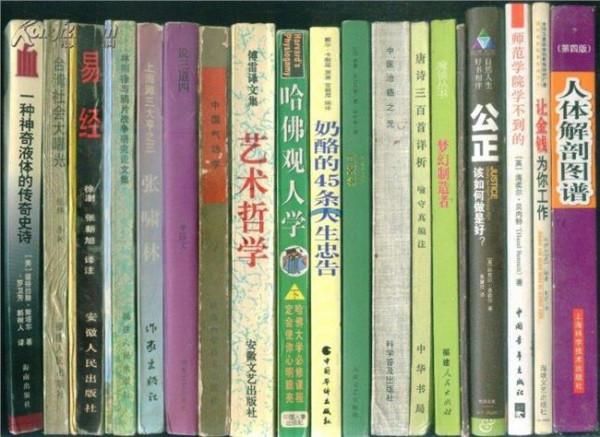淡之美李国文 李国文:短促的美丽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短促的美丽,像焰火一样炽烈地照亮了大半边天;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快就凋谢的花,一眨眼工夫,就熄灭得无影无踪,一地落英,遍地泥泞。桐花开的时候,总是赶上凄冷的春寒,而到收拾桐子的初冬,天又该冻得人瑟缩了。这是如匆匆过客的桐花的命运吗?还是耕作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坚强写照?来了,又去了。下一次辉煌,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寒料峭时。
对风雅的人来讲,在鉴赏艺术方面显得较有品位的,应该说是赏花。然而我对于大自然赏赐给这个世界的美丽,通常一看了之,仅此而已,有点儿辜负这一番万紫千红的美景,甚是惭愧。
看花,或者赏花,需要好兴致,需要好心情。我想起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忘记了,但还能记得起故事。海因里希·伯尔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也大都着眼于“二战”以后德国社会的形形色色。
故事说,他的叔叔从部队复员了,回到他们那座基本上已是废墟的小城镇,找不到工作。这是可想而知的,凡战争,必然都会有这样的结局。他的叔叔因而得不到帮助,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不幸,大家都在为每天的面包发愁。
虽然不再有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但生活的熬煎,却让这座小城镇的居民,日子过得相当沮丧。他的叔叔,自然也要为生计奔波。因为没有人再雇佣他,他就只好在墙倒屋塌的断壁残垣之间,搭起来一个小小的铺面,准备开一间小店。
终于,他的叔叔拥有了一间临街的铺面,而且,经过简单的粉刷装修以后,准备开张了。人们通过擦拭得干净透亮的玻璃窗,才知道他的叔叔开的是一间花店。接着,整座小城都沸腾了。成百上千的居民,有的甚至特地跑来,就是为了看一眼这家花店。
这就是说,经受战争创伤的人们,更需要得到心灵上的抚慰。固然,物质需求是第一位,不可须臾或缺的,但精神上、文化上、美学意义上的需求,也是人生很重要的部分。他叔叔那间小小的花店,竟然开得下去,竟然生意不错,因为,有的人宁肯在面包上撙节一点,也愿意买一束鲜花,放在眼前,而得到怡神悦目的美感。这片废墟上绝无仅有的花店,给那座疲惫的小城镇,给那些乏累的居民们,带来了难得的一点美丽。
这家小小的花店,既象征着生存下去的希望,也兆示着更美好的,即将到来的明天。
花,点缀着这个世界,虽然有它也可,无它也可,但人们生活的物质空间里,之所以五彩缤纷,千姿百态,正是鲜花的色彩作用于人们眼球的结果。而万紫千红的鲜花,更是让每一双眼睛忙不过来。假设人们生活的空间里,只有一种颜色或者没有任何颜色,那是无法想象的。
在我记忆中,再没有哪次出行,像那一年春天的洛阳之行,使我对于颜色或者色彩,有如此深刻而全面的认知了。
那一年,以中国作协葛洛同志为首的一行人,本是去洛阳参加一次文学评选活动。因为赶上了“倒春寒”,牡丹花晚开了几天。评选完了,主人盛情雅意,请参观者们一定等到盛花期以后再离开。老天真是成人之美,就在那两天,艳阳高照,煦风徐来,那些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儿,都张开了笑脸,以抢眼的最美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实在此以前,我打过退堂鼓,再三说明我只是一个看花人,而不是赏花人,看不看无所谓,准备打道回府。葛洛同志是1938年从家乡奔赴延安的老革命,他是汝阳人,与洛阳一山一水之隔。他劝我说,洛阳牡丹始自唐宋,是值得留下来欣赏的。
现在,葛洛同志已经离开人世好多年了,他的长者风度,他的谦和精神,至今犹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主编《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时,我也是得到过这位老同志提携的。好吧,我便多留一天。这样,得以在洛阳市中心的王城公园里,有生以来,第一次观赏到像海洋一样无边无际的鲜花,而且清一色都是盛开的牡丹。
看到那些绽放的姚黄、魏紫、欧碧、赵粉等名品,又看到后来培育出来的新秀,心中不由涌上来唐人刘禹锡的诗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你没有爬过高山,就不知山外更有高山;你没有渡过黄河,就不知怒吼吧黄河的雷霆万钧;你没有放眼望去,满眼皆是牡丹花的世界,就不要奢称自己是赏花人。宋人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说:“是洛阳者,是天下之第一也。”你没有看到洛阳牡丹之前,也许觉得这位“六一居士”,话说得武断一点,结论下得太早一点。然而,在你来到洛阳,看到每一朵牡丹,都在争取你的注意力时,你就知道他此言非虚了。
洛阳牡丹,天下第一。其实至名归之处在于:第一,得天独厚。此水此土,特别适宜牡丹生长。“则均洛阳城围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第二,得人钟爱。“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风气所及,“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也许最为主要的,还在于第三,背负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
而在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说道:“牡丹,前史中无说处,唯《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成式捡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
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又房相有言:‘牡丹之会,琯不预焉。’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移于城中。”
由此可见,国色天香的牡丹,那雍容自若的枝叶,那层出不穷的花瓣,那婀娜多姿的花蕊,那千变万化的颜色,这一切,总是与帝都的富贵气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我结束那次洛阳之行,乘夜车回京途中,冲着车窗外的黑夜,我不禁想起另外一幅图画:那是早些年,我刚刚来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寂寞深山里,正好是春天刚来,冬天还没离开的季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春天里最早开放的桐花,那么放肆,如同喷泻般开放,不管冻雨,不管冰霰,开得那么热烈,白得那么堂皇,那么晶亮,那么炫目。
那浩瀚的花海把我镇住了。凡是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全是雪一样白的桐花,满天砌玉,花瓣飘零,冷雨霏霏,那季节里,天和地,全都是白的。
当时,我在那土地贫瘠、生活艰困的山区修过铁路,一年四季,从生到死,是不会有任何辉煌的,也就是在斜风冷雨中的这些桐花,造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声势。可惜,花开得那样旺,但几乎无人欣赏,更无人赞叹。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短促的美丽,像焰火一样炽烈地照亮了大半边天;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快就凋谢的花,一眨眼工夫,就熄灭得无影无踪,一地落英,遍地泥泞。桐花开的时候,总是赶上凄冷的春寒,而到收拾桐子的初冬,天又该冻得人瑟缩了。这是如匆匆过客的桐花的命运吗?还是耕作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坚强写照?来了,又去了。下一次辉煌,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寒料峭时。
那一晚,在车轮的咣当声中,牡丹的艳压群芳,人尽赞美,桐花的耐着寂寞,花开满山,无论有人关注,还是无人呵护,不管游人如织,还是乏人问津,花开花谢自有时,这倒是对我这样一个看花人的莫大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