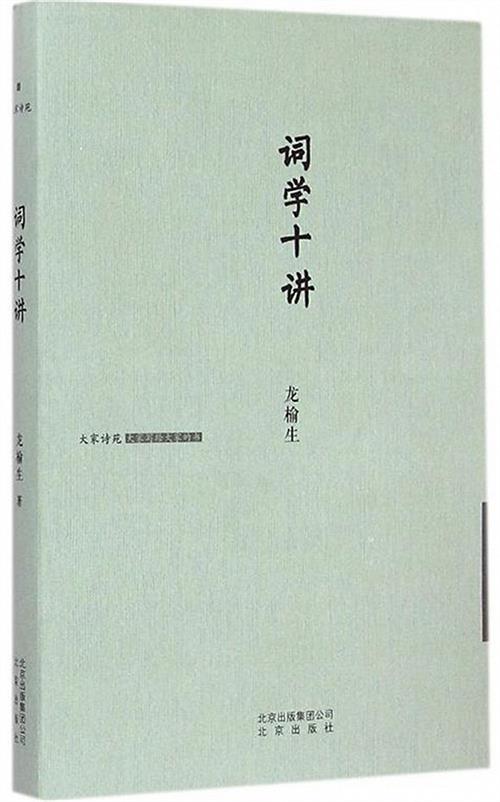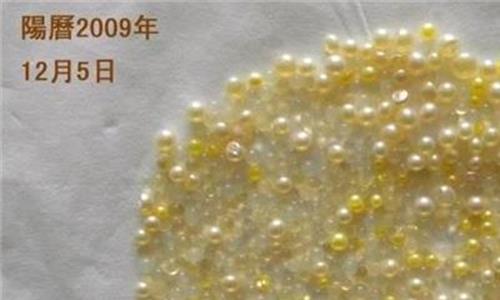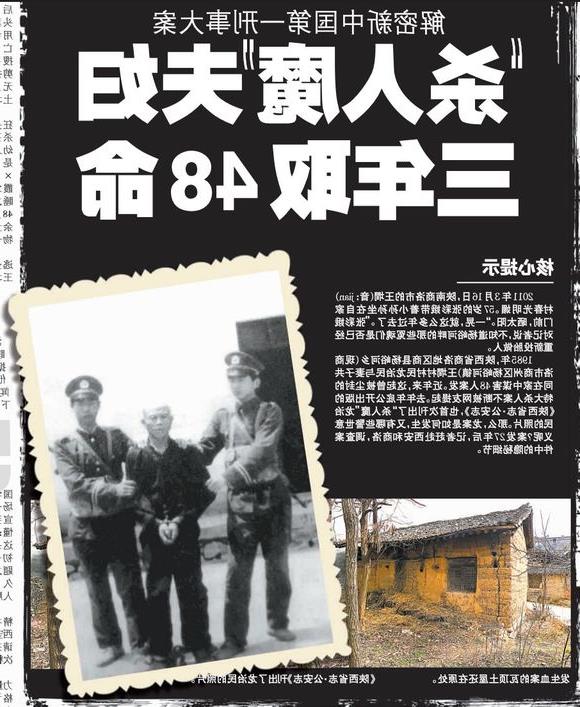龙榆生先生 【龙榆生逝世50年】忍寒词客风雨飘摇的一生
在北京香山的万安公墓里,龙榆生在此已长眠了近半个世纪。这位与夏承焘、唐圭璋齐名的20世纪词学大师,在人世走过了64个春秋后,于50年前的今日在上海病逝。墓碑上,只有一句话——"西江忍寒词人龙七,1902——1966。"
龙榆生出身名门:他的父亲龙赓言与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同榜进士,并在安徽和湖北等地做过多任知县和知府;母亲杨玉兰出身于万载世族,身世显赫。6岁时,龙榆生母亲的早逝使他性情逐渐变得孤僻,身体也大不如前。
也正是因为身体差的原因,龙榆生那"从中学毕业后就到北京大学进修"的愿望落空。好在,在父亲的指导下,龙榆生小学时就学会了诗词骈文,并经堂兄沐光介绍,在1921年的春天前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师从黄侃学习声韵、文字及词章之学。
1933至1936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了《词学季刊》,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这是当时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三年里,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的《遍行堂集词》、劳纺《的织文词稿》及《强村老人评词》等作品,受到了词学界的广泛支持。后来,龙榆生又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虽说刊物登载的文章的题材有扩宽之势,但稿件水准却大不如前。
除了在词籍整理方面的努力,龙榆生更致力于词学研究。上世纪30年代,除了在《词学季刊》上发表论文外,他还著有《词体之演进》、《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等书,对词这一文体的发展追源溯流,并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与阐述。
同时,龙榆生对诸多既成的理念又抱有自己的看法。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的他,对苏轼、辛弃疾的词作颇为喜欢,并先后撰写了《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苏门四学士词》等著作。从明代开始,学者常以"豪放派"形容苏、辛二人,而龙榆生则主张应以王鹏运提出的的"清雄"二字来概括。
毕生研究词学的龙榆生,还花了诸多精力去推广、普及词学。常年任教与各大学校的他,在写下一本本词学的研究著作的同时,也一直不忘整理概论和选本。前者中,最典型也最易懂的,当属《词学十讲》。在这本由讲义组成的著作中,龙榆生深入浅出地向词学爱好者阐述了词的对偶、结构等基本知识,专业而不失趣味性。
细读《词学十讲》,看龙榆生分析词调,不禁惊叹于他说的很多道理,都精微而细致。选本方面,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可惜的是,解放后,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调整巨大,丧失了原有的特色和味道,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从1933年在自己创办的《词学季刊》连续发表关于词学的多篇论文开始,龙榆生本人及其研究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议论。他一改过去点评词的形式,从词的起源、发展、创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将重点放在唐宋词的研究上。
正如他所说那般——"对任何艺术,想要得到较深的体会和理解,从而学习作者的表现手法,进一步做到推陈出新,首先必得钻了进去,逐一了解它的所有窍门,才能发现问题,取得经验,彻底明白它的利病所在。"
自抗战期间开始,龙榆生的生活便不再平静。1945年11月8日,他被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几经辗转,才被夏承焘的弟子潘希真等人在三年后保释出来。1958年,龙榆生又被打成右派,职称也从原来的三级降到了五级。
文革时,龙榆生的家遭造反派查抄,书房"风雨龙吟室"中的书稿、文物都一一被清空。这对他本人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以致于肺炎复发,高烧不退。在这时的《春晚杂诗》中,龙榆生写下的"自从省愆来,门真可罗雀。寂寞良自甘,闻声总欢跃。"亦是自身苦难境地的写照。
在辞世的13年后,龙榆生的名誉得以恢复。也许,这样的际遇,早在他那"忍寒词人"的别号中就已注定。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晋代杰出诗人陶潜告诉我们的经验之谈。我们要想欣赏"奇文",就得首先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才能彻底理解它的"奇"在哪里,从而取得赏心悦目"欣然忘食"的精神享受。孟轲曾以"以意逆志"说诗,他所说的"志"也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思想感情。
正确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是要靠巧妙的语言艺术表现出来的。把读者的思想感情去推测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得到感染,取得精神上的享受,是要通过语言艺术的媒介才能做到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词是最富于音乐性的文学形式,而这种特殊形式之美,得就"色"、"香"、"味"三方面去领会。正如刘熙载所说:词之为物,色、香、味宜无所不具。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借色每为俗情所艳,不知必先将借色洗尽而后真色见也。王国维也有所谓"生香真色"的说法(见《人间词话》卷下)。也如严沧浪云:"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水中之月,镜中之像。"此皆论诗也,词亦以得此境为超诣。
像这类"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美在酸咸之外"的词境,以及所谓"色"、"香"、"味"等等,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我们要理解它,又非经过视觉、嗅觉、触觉等等的亲身体验,是很难把它说得明白的。由于词的语言艺术最主要的一点是和音乐结着不解之缘,所以要想去欣赏它,首先得在"声"和"色"两方面去体味。
"声"表现在"轻重扬抑、参差相错"的基本法则上面,"色"表现在用字的准确上面。我们要初步理解和掌握这两方面的手法,就得先从读词做起。近人蒋兆兰说:作词当以读词为权舆(始也)。
学填词必先善于读词。一调有一调的不同节奏,而这抑扬高下、错综变化的不同节奏,又必须和作者所抒写的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恰相适应,才能取得内容和形式的密切结合,达到语言艺术的高峰。
谈到用字的准确,也得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炼声",也就是张炎所说,"要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一方面是"侔色",也就是陆辅之所说的"词眼"(见《词旨》)。这和《词人玉屑》所称:"古人炼字,只于眼上炼,盖五字诗以第三字为眼,七字诗以第五字为眼",有所不同。刘熙载说得好:
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专求字句,纵争奇竞巧,岂能开阖变化,一动万随耶?
不论是通体的"眼"也好,数句的"眼"也好,这"眼"的所在,必得注意一个字或一个句子的色彩,须特别显得光辉灿烂,四照玲珑,有如王国维所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又如柳永《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可算是通体的"眼",著此一句,而千种风情,万般惆怅,都隐现于字里行间,玲珑透彻,言有尽而意无穷。
但这种境界,非得反复吟讽,心领神会,把每一个字分开来看,再把整体的结构综合起来看,着实用一番含咀功夫,是不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