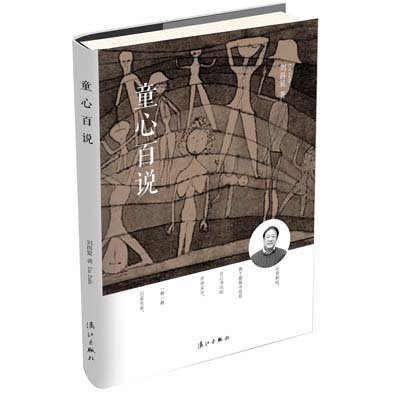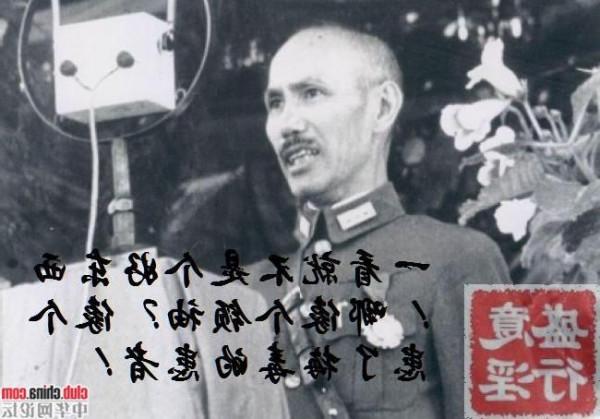刘再复童心百说 [转载]刘再复《童心百说》(上)
对着稿纸,我于朦胧中觉得自己书写的并非文字,一格一格只是生命。钱穆先生把生命分解为身生命与心生命,我抒写的正是幸存而再生的心生命。心生命的年龄可能很长,苏格拉底与荷马早就死了,但他们的心生命显然还在我的血脉里跳动着。
此时许多魁梧的身躯还在行走还在追逐,但心生命早已死了。都说灵魂比躯壳长久,可他们躯壳还在灵魂却已经死亡。不是死在老年时代,而是死在青年时代。心灵的夭亡肉眼看不见。我分明感到自己的心生命还在。
还在的明证是孩提时代的脾气还在,那一双在田野与草圃寻找青蛙与蜻蜓的好奇的眼睛还在。不错,眼睛并未苍老,直楞楞、滴溜溜地望着天空与大地,什么都想看看,什么都想知道,看了之后,该说就说,该笑就笑,该骂就骂,一声声依旧像故乡林间的蝉鸣。无论是春的蝉鸣还是秋的蝉鸣全是天籁。
我真幸运,和明代的异端思想家李卓吾竟是同乡。他走过的许多开满野蔷薇与映山红的乡间小路我都熟悉都感到格外亲切。他在流浪中飘落散失的基因说不定有几粒潜入我的血液。要不我怎么会那么喜欢曹雪芹笔下那些自我放逐的“槛外人”?七十年代,当我穷得“囊无一钱守”的时候,还是买下他的《焚书》与《藏书》。
他的《童心说》成了我人生的一部伟大的启示录。因为读他的书,我才发现我的家乡有一颗太阳般的迸射着思想的灵魂。这颗灵魂的名字就叫李卓吾。
从少年时代到今天,我在冥冥之中一直听到他从万物之母的怀中发出的呼唤:同乡兄弟,我的童心说献给我的同一代人也献给你的同一代人,特别是要献给你。你的生命快要被堆积如山的教条窒息了,你的天真快要被浓妆艳抹的语言埋葬了。
你正在被概念所裹胁,正在迈向布满死魂灵的国度。救救你的天真,救救你的天籁!往回走,返回你的童心,返回你的质朴,返回清溪与嫩柳滋润过你的摇篮。你是无神论者,云中的天国不是你的归宿,但地上的天国属于你。地上的天国就是你的天籁世界,童心就是这天国的图腾。
准确无误,我听到伟大同乡的呼唤,如同天乐般清晰而响亮的野性呼唤:努力做一个人,努力成为你自己。家乡的思想家在黑暗的年代里像高举星辰似地高举过人类的本真本然之心。温柔的、亮晶晶的心灵把拥有百万大军的庞大帝国吓坏了。
帝国的监狱在京城的郊区堵住他的嘴,困死了他的生命,妄图一举消灭他的熊熊燃烧的思想。然而,帝国失败了。当帝国溃灭的时候,我老乡的学说却跨越时间的边界走进曹雪芹的眼睛,还走到今天,一直走到我的笔下。
让我礼赞你,《焚书》与《藏书》的作者,英勇的老乡,童心说的第一小提琴手。你孜孜求真,厌恶“假人”和假人的把戏。假人胸中只有本能的心脏,没有本真的心灵。假人有声,但不是心声,而是肉声。道学太沉重,对人的要求太多,太多而做不到,就伪装,就作假,就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
你发现王朝中有个假人国,你的童心对着假人国跳着、笑着、骂着,文字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旗帜站立着飘拂着,哗啦啦在高空天宇中响动着,响了将近五百年。
堂堂正正。心中无邪,身外无求,形上无垢。顶天立地向着假人国挑战:谁敢邀堂堂而击正正?何等气派!童心就是力量。童心是比权力帝国更有力量的力量。
回归童心,你启迪我两个向度:一是回到从母腹中诞生下来的那一刻,回到刚降临人间时那一脉黎明似的柔和的目光;二是回到故国文化的精神家乡,回到《山海经》那一片蓝苍苍与绿茫茫,还有苍苍茫茫所负载的最本真、最本然的故事。
我的形而上假设,不在天上,而在地上:在第一次张开的婴儿眼睛之中,在母亲赋予的原始混沌之中,在女娲、精卫、夸父等英雄的大气与呆气之中。修炼修炼,不是修向成熟,而是修向鸿蒙时代的勇敢与傻乎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诗正在被权力所凌辱,被道学所歪曲,被金钱所欺压,被语言所遮蔽。
文学正在失去真思真想真情真性,诗就要死了。面对文学的枯竭,诞生于家乡的异端思想家大声疾呼:回归童心!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不妨痛痛快快地叙述;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不妨痛痛快快地倾吐;口头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不妨痛痛快快地说出。发狂大叫,流涕恸哭,向人世掷出响当当的真言真语真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但句句发出热腾腾的内心。
秘鲁作家胡安.拉蒙.里维罗(1929──)如此表述:作家不可能成熟,他们应当永远追随孩子。 “岁月使我们离开了童年,却没有硬把我们推向成熟。……说孩子们模仿成年人的游戏,是不真实的:是成年在世界范围内抄袭、重复、发展孩子们的游戏。
”(引自《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拉美卷》第2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我喜欢这句话,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和今后可能所作所为,全是人生的初稿。初稿而已,一切都不成熟。我害怕成熟的圆猾,成熟的虚伪,成熟的世故,成熟的“瞒和骗”。
到处寻找天才,却常常忘记身边有一群天才,这就是孩子。“孩子是未被承认的天才”,俄国的诗人沃罗申(1877-1932)早就这样说。他在1903年写的一首无题诗常让我吟诵:让我们像孩子那样逛逛世界/我们将爱上池藻的轻歌/还有以往世纪的浓烈/和刺鼻的知识的汁液/梦幻的神秘的吼叫/把当今的繁荣遮盖/在平庸的灰暗的人群中间/孩子是未被承认的天才。
(引自《俄国现代派诗选》第208-209,上海译文出版社)孩子是天才,天才又都是孩子。
“圣人皆孩儿”(《道德经》),天才更是皆孩儿。不错,天才是永远不知世故和拒绝世故的孩子。孩子的眼睛不被权力所遮蔽,也不被功名、财富所遮蔽,一眼就能看穿人间厚重的假面,所以是天才。
鲁迅说王国维老实得像条火腿。20世纪初期的先知型天才,却像个傻子。王国维说,诗人乃是赤子。他自己正是个赤子,正是个婴儿。他投进昆明湖,不是被历史所抛弃,而是把历史从自己的生命抛掷出去。婴儿最傻,但感觉最灵敏。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俄国诗人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明斯基(1855-1937)用他的诗表达了一种人生感受:给予辛劳不已的人生以安慰的,不是来自哲人的著作,不是来自诗人甜蜜的杜撰,不是来自战士的赫赫功勋,也不是来自禁欲者的苦苦修炼,而是来自美好生命的回归:“心灵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循环/看,我又回到童年的梦幻。
”(引自《俄国现代派诗选》第97-98页)在诗人生命的循环链中,晚年不是落入衰朽,而是与朝日般的童年重新相逢。
在《远游岁月》中,我写了“二度童年”,感受到的是,人可以有数度童年,可以有多次诞生。每一次诞生都会给生命带来新的黎明与朝霞,新的生命广度与厚度。每一次内心的裂变都给人带来两种方向,一种是走向衰老,一种是走向年轻。能够走向童年,是幸福的人。在裂变中扬弃过去,告别主体中的黑暗,及时地推出一个再生的内宇宙。
人的最后一次诞生与死亡相接。然而,如果最后一次诞生是回归童年,那么,它首先是与儿时的摇篮相接。许多死者在临终前看到儿时那个赤条条的自己,遥远的过去的自己,而那正是诗人的未来。一个在世俗势力包围中的诗人,他所响往的未来,正是过去,正是幼年时代那个未被世俗灰尘所污染的生命的黎明。
流亡到美国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说:诗天然与帝国对立。人类的童心也天然与帝国对立,尤其是与强大而不诚实的帝国对立。帝国的基石是权势与权术。人间最无诗意的也正是权势与权术。古罗马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还有斯大林的革命大帝国,都已成了废墟,但诗还在,人类的童心还在。
诗与童心在人类行进史上至少已凯旋了三回。当第三大帝国进入墓地的时候,诗与童心却依旧在大陆与大洋中吞吐着黎明。天下之至柔与天下之至坚的较量永远不会停止,但胜利总是属于至柔者,因为人类毕竟是热爱诗意的栖居。
把呼唤生命之真的童心说视为异端,那是帝国的界定。知识的背后常常是权力。被视为异端的未必是邪说。所以我要像茨威格那样呼吁:给异端以权利。那怕你不同意异端的内涵,也该保卫异端的权利。灵魂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我常念着俄国思想者赞米亚亭的话:异端是人类思想之熵唯一的救药。尽管这药是苦涩的,但它对人类的健康是必须的。尤其是对于灵魂的健康。如果没有异端,也应当创造出异端。然而,权势者总是砍杀异端,连我的伟大同乡李卓吾也给扼杀了。
童心并不只属于童年。形而上意义的童心属于一切年龄。我喜欢老顽童,他们至死还布满着生命的原始气息。歌德到八十岁还热烈地爱恋着。诗人的生命永远处于恋爱中,永远处于追求中。没有恋情不会有诗情。广义的诗歌都是恋歌,包括对山川土地蓝天的眷念。
道德家们只会对着歌德摇头。摇动的眼睛看不见白发覆盖下那些活泼的精灵。诗人最可引以为自豪的,便是他永远是个沙滩上拾贝壳的孩子,到老也带着好奇的眼睛去寻找海的故事。痴痴地寻找着,以致忘了世俗世界的逻辑与秩序。
常常想起《末代皇帝》最后一幕:溥仪临终前回到早已失去的王宫。经历过巨大沧桑之后的溥仪已经满头白发,然而,他的童年却在沧桑之后复活了。他最后一次来到无数眼睛羡慕的金銮殿。此时,他没有伤感,没有失去帝国的悲哀,没有李后主的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慨叹。
他一步步走上阶梯,走近王座,然而,他不是在王座上眷恋当年的荣华富贵,而是俯身到王座下去寻找他当年藏匿着的蟋蟀盒子。盒子还在,蝈蝈还蹦跳着,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间。
一切都已灰飞烟灭,唯有这点童趣还活着。小盒子里有蝈蝈,也有他自己。当别人在欣赏王宫王冠的时候,他,皇帝本人,却惦记着大自然母亲给予他的天真。这活生生蹦跳着的蟋蟀比镶满珍珠的王冠还美,一切都是幻象,唯有孩提时代的天趣是真实的。人生要终结了,一个帝国的皇帝最后的梦想不在天堂,而在藏匿于王座下的蟋蟀盒子。小小的蟋蟀盒子,拆解了世俗世界的金字塔,拆解了权力与财富的全部荣耀。
秦王朝的丞相李斯,原是上蔡的普通百姓,后来却登上朝廷的尖顶,拥有天子之下最大的权力与荣耀。他自己身居相位,而几个儿子也跟着无比显赫,并且都娶秦公主为妻。当了三川郡守的大儿子回家省亲时,他大摆酒宴,朝廷百官争先朝贺,停在门前的车架有千数之多。
可是,在政治较量中他因为败给赵高而落得腰斩咸阳,死得很惨。临死之前,埋藏在他记忆深处的天真突然醒来,他对儿子说:我想跟你再牵着那条黄狗,同出蔡东门去追野兔,还能办到吗?他在人生的最后瞬间,才发现生命的欢乐并不在权势的峰顶上,而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怀抱之中。
陪伴皇帝在宫廷里用尽心机,不如陪伴着狗在原野上追逐野兔。李斯在死亡时刻,突然意识到生命最后的实在,可惜已经为时太晚。
丰子恺一辈子研究孩子,他说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拐弯。艺术家的眼光如同孩子,但需要有一点弯曲。孩子眼里直射的光芒能穿透一切,包括铜墙铁壁。什么也瞒不住孩子的眼睛。安徒生笔下的孩子眼睛最明亮,唯有他,能看穿又敢道破皇帝的新衣乃是无,乃是空,乃是骗子的把戏。
王公、贵族、学者、论客、将军、官僚,眼睛都瞎了,装瞎也是瞎。孩子在瞎子国里穿行,孩子在撒谎国里穿行,像太阳似的照着瞒和骗。一旦发现瞒与骗,孩子的眼睛鼓得圆滚滚,然后发呆,然后迷惘,然后惊叫,然后呐喊。我们要给孩子的眼睛以最深刻的信任。
贾宝玉含着那一块通灵宝玉和带着女娲时代那一双原始的眼睛来到人间了。宝石亮晶晶,眼睛亮晶晶,于是,眼睛看见朱门玉宇下生命一个一个死亡,钟灵毓秀一片一片破碎。那些最真最美的生命与权贵社会最不相宜,死得也最早。世界的老花眼,怎么也看不惯晴雯和林黛玉。
无端的摧残,无声的吞食,贾宝玉看见了;情的惨剧,爱的毁灭,贾宝玉看见了。世人的眼睛看见金满箱,银满箱,帛满箱;宝玉的眼睛却看见白茫茫,空荡荡,血淋淋。宝玉的眼睛直愣愣,满眼是大迷惘,满目是大荒凉。贾宝玉其实是个永远不开窍的混沌孩子。
贾宝玉看见金钏儿投井死了,看见晴雯含冤含恨死了,都是被自己母亲逼死的。本该是大慈大悲的母亲,本该是温情脉脉的母亲,本该是拥抱天下一切儿女的母亲,这回也逼死无辜的孩子。母亲也杀人。贾宝玉亲眼看到母亲也杀人!
这是比一切凶残更加令人恐怖的凶残。他绝望了,发呆了,他不能在母亲的府第里再居住下去了。他不能生活在一个连母亲也变成凶手的人间。告别故园,告别自己爱恋过的土地,他远走了,逃亡了。逃亡者身内还有天真,天真者承受不了那个简单的事实:母亲也杀人。看过母亲杀人的眼睛永远带着大迷惘。
一直记得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nxley)的大困惑和他对世界所发出的提问:为什么?为什么人类的年龄在延长,而少男少女们的心灵却在提前硬化?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少男少女刚走出校门心理就已僵冷?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年轻的孩子在动脉硬化前四十年身心就麻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类尚未苍老就失落了那一颗最可爱的童心?赫胥黎面对着的是人类生命史上最大的困惑。
他写着写着,写了《滑稽环舞》,写了《知觉之扉》,还写了《美丽新世界》,什么是美丽新世界?那是少男少女以及整个人类的童心不再硬化的世界,那是童心穿过童年、少年、青年时代而一直跳动到老年时代的世界。
人们只想到动脉硬化、血管硬化,有多少人想到童心硬化、青春硬化、灵魂硬化呢?“童心不再硬化”,变成诗人的梦与呼告。让我们回应这诗的呼告。
十八世纪思想启蒙家卢梭发出警告:人类正在提前堕落,青春期野蛮而残酷。青春生命本是最慷慨和最善良的生命,他们既最爱别人,也最让别人爱。然而,青春王国正在崩溃,青春的眼睛变得阴冷,瞳仁里散发着寒气。二十世纪菲尔丁通过他的《蝇王》再次警告:世界正在失去伟大的孩提王国。
一旦失去这一王国,那是真正的沉沦。然而,人类忽略了卢梭与菲尔丁的警告。所以此刻我们不得不又敲响警钟:人类的童年正在缩短。不仅枪械、毒品入侵了孩提王国,而且堂皇的“科技”也在吞没人生的黎明,孩子已变成电脑的附件和电视屏幕的随从。二十世纪的孩子们,赢得了机器,却失去了星辰、月亮、山脉、河流和整个大自然。
莫言的《酒国》里有一种婴儿的宴席。酒国的名菜是孩子肉制成的“红烧餐”。肉里伴着许多令人心醉的香料。香喷喷的婴儿肉使酒国金满天下银满天下誉满天下。这个酒肉泛滥的城市,公民们培育婴儿,然后拍卖婴儿,然后杀戮婴儿,然后烹饪婴儿和烧烤婴儿,然后制造具有酒国特色但没有血色也没有血痕的婴儿盛宴。
来自四面八方的高等食客们品尝着婴儿肉,唱着醉醺醺的酒歌。歌声里带着人肉味。醉着的歌者不知道是婴儿肉,法律上没有罪。所谓忏悔意识,就是要他们知道自己无意中进入共犯结构进入吞食婴儿的筵席,在良心上应有罪的感悟。
孩子无需包装,孩子无需面具。我喜欢金庸《射鵰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永远不知人间势利的老孩子。他拾到一个面具,像拾到一个玩物,高兴极了。他不知道面具是什么,只觉得好玩,人的脸面还需要遮拦,好玩;人的真相还需要掩盖,好玩。
面具是人的异化物,它对于老顽童永远是陌生的,奇异的。他不知道,人间已布满面具,连庞大的学说也成了面具。没有面具就不能存活,在政治塔尖上左右逢源的风流人物,至少有一百副面具。可惜中国的周伯通快灭绝了。想了好久,想不出几个老顽童的名字。
“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这是瞿秋白临终前的精彩话语。瞿秋白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完全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坦白说:“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
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应当祝贺你,从赤都回到赤子之乡的瞿秋白!你在一个充满包装、充满面具的国度里喊出“揭穿假面具”的赤子之声,并赢得赤子无所遮拦、无所顾忌的大快乐。你生命最后的瞬间是真实也是美丽的。
在波罗的海宁静的水滨,站立着安徒生的美人鱼,在风涛中凝固的故事与雕塑。两度和她见面,每一次都是生命的重新相逢,每一次我都呆呆地凝望着她。我知道自己生命中最隐秘的内核与她相通,这内核,便是对爱的期待,一切怅惘都因为爱的失落。
面对着她,我还想到民族的脾气与性格。一个名字叫做丹麦的国家,竟然以童话中的美人鱼作为民族的图腾,不怕人们说它幼稚。这样的国家是幸运的,它将永远拥有梦与天真。难怪哥本哈根这样甜这样浪漫。我的故国太老成了,它早已远离童话。高挂的图腾,曾是孔夫子,曾是诸葛亮,虽是圣人与英雄,但缺少天真。我更喜欢美人鱼,更喜欢紧连辽阔沧海的童话。
回归童心,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凯旋。
当往昔的田畴重新进入我的心胸,当母亲给我的最简单的瞳仁重新进入我的眼眶,当人间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继续颠倒,我便意识到人性的胜利。这是我的人性,被高深的智者视为浅薄的人性,被浅薄的俗人视为高深的人性。此刻我在孩子的“无知”中沉醉;不知得失,不知输赢,不知算计。
大地的广阔与干净,天空的清新与博大,超验的神秘与永恒,还有那个没有任何归属的自己,这一切,又重新属于我。凯旋是对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的重新拥有。凯旋门上有孩子的图腾:赤条条的浑身散发着乡野气息的孩子,直愣愣的张着眼睛面对人间大困境的孩子。
斯皮尔伯格制作的电影《太阳帝国》是我最喜爱的影片之一。每次看完之后,都忘不了男主角,那个英国孩子jim。总是忘不了那双迷惘的、困惑的、发呆的眼睛,那双在战争结束后垂挂在肩头上的和黑发间绝望的眼睛。
Jim用孩子的眼睛战争,看到的不是正义与非正义,而是整个世界的不幸,战争双方都不幸,失败者不幸,胜利者也不幸。而他自己,一个孩子,在战争中不仅失去双亲,失去欢乐,也失去全部生活。战争中的世界没有路,战斗不得,逃亡不得,连投投降也没有接受。
他从小就做着在蓝天里飞行的梦,也被战争粉碎,尽管空中到处都是飞机。战争制造了废墟,也制造了心灵的废墟。战后的jim,只剩下一双无言的、发呆的眼睛。眼里只剩下一片白茳茳。
孩子的眼里没有敌人也没有坏人。唯有孩子真的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敌对的双方都是兄弟。然而,战争却在孩子眼里展示出比野兽还凶狠的厮杀。Jim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太阳帝国日本的一方,有让他恐惧和憎恶的战神,也有救援他的、和他一样只做着飞行梦的年少朋友。
但朋友又惨死在密集的枪口下。朋友的鲜血染红了太阳。梦破碎了,战争的神话破碎了,唯有死亡是真实的。唯有孩子的眼睛看清了真实,看清了战争乃是蓝天下的一片血淋淋。
看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E·T·》,便知道最能与陌生的在宇宙相通的是孩子。孩子的心灵如同音乐,能破语言之隔,直达天际。人类对假设的外星人充满了恐惧,只有孩子对他们没有防范。孩子心中没有碉堡,没有设防。人类通往地球之外的智能生物世界的唯一使者是儿童。儿童的目光,是投向天外的曙光。天使在哪里?天使就在身边。天使就在你的屋里。
成年人喜欢寻找神世界,希望神能帮助自己进入不朽不灭的永恒。孩子则喜欢进入鬼世界。鬼很丑,但活泼、真实、没有架子。孩子没有力量,但也没有邪恶,所以他们不怕鬼。如果真有鬼世界,孩子也能和鬼对话。美国的鬼节,其实就是儿童节。
如果说“从一粒沙可看出一个世界”这句话还有些夸张,那么,说“一颗童心可以看清一个民族”就绝非夸大。童心这面镜子才足以照明世界是否衰老。在将死而未死的世界,童心总是彷徨无地。如果童心渴望逃亡,那一定是世界太世故,太苍老了。
让人间的暴君最感到头疼的是提问。孩子最喜欢问,孩子的天性就是提问,《十万个为什么》的书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书。十万个提问之外还有最简单的提问,这也使暴君感到恐惧:你为什么杀人?你杀了人之后为什么不承认杀人?这是最简单的的属于孩子的问题。孩子的天性并不排斥自己的回答。孩子往往能回答学问家无法回答的问题。“暴君三餐的食物就是人。”孩子可能这样回答,简单而明了。
萨特说,他永远希望着,但不打扰别人的希望。我设计不了希望工程,但我可以护卫孩子的希望视野,如果让孩子们看到,前辈用功读书、勤奋工作最后的结果是走进牛棚和精神裁判所,这就摧毁了孩子的希望视野。也无所谓希望工程。希望工程不是金钱累积的,它是从儿童时代开始展示的前方景观。希望视野如此预告:未来的美好世界是为诚实的孩子准备着的。
尼采说人生必经骆驼阶段,狮子阶段和婴儿阶段。最后是婴儿阶段,我仿佛正在经历这一生命的第三个旅程。婴儿不是长不大的生命,而是崭新的心灵存在。在第三旅程中,我所做的是“反向努力”,不是朝前征战,而是向后回归。骆驼把自由化作沉重的责任,背着责任跋涉沙漠。之后,便如狮子去争取自由,为自由而战斗得遍体鳞伤。这之后,便是反向回归,努力创造一个婴儿般的布满黎明气息的新的生命本体。
应当救救自己。全部感觉都被改造过了,连眼睛也麻木,连手脚也僵硬,连哭泣也有点走样。全部理念都被冰冻过,同化过,连反教条的文字也带着教条的尾巴。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最后的地狱,黑暗聚集在地狱里。带着这沉重的地狱,怎么去救孩子?难道要裹挟孩子一起入地狱?明白之后,只想救救自己,只想孩子救救我。
童心像天天的日出,天天都有光明的提醒;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不要忘记那个赤条条的自己。你不是功名的人质,欲望的俘虏;你不是机器的附件,广告的奴隶;你不是权力的花瓶,皇帝的臣子。你是你自己,你赋予自己成为自己的全部可能。你是山明水秀大地怀抱中的农家子。与高山、流水、田野还有山花山树山鹰关系的总和,那才是你。
眼睛的进化是从畜的眼睛和兽的眼睛进化成人的眼睛,并非是从儿童的眼睛进化成老人的眼睛。努力保持一双孩子的眼睛,并非退化。孩子眼睛的早熟,使人悲哀。当我看到孩子疲倦的眼神时,总是惊讶,而看到他们苍老世故的眼神时,更是感到恐惧。我喜欢看到老人像孩子,害怕看到孩子像老人。
俗气覆盖一切的人间找不到一块可以存放心灵的净土。眼泪是为无辜的孩子流的,但无处存放;忧伤是为洁白的生命燃烧的,但无处存放;呐喊是为冤屈的灵魂叫响的,但无处存放。
聂绀弩在赠予我的诗中,把我比作哪吒,莲化的化身。这一比喻是人间给予我的最高奖赏,我再也不需要别的奖赏了。自从这一首赠诗出现之后,我的生活便有了路标;往莲花的方向走去,用生命的事实抹掉比喻,让自己真的成为浊水难以染污的莲荷,然后脚踩双轮驰骋于高远的蓝天和平实的大地,切不可在精神雪崩的时代里,让天赋的品格与灵魂崩塌者同归于尽。
常常在书桌旁坐不住。窗外是金色的秋天,九月的菊花开得那么动人,白桦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像孩子好奇的眼睛。五十岁之后,我每天都伴随着小花小草小树生活,稿纸上的每一个格子都被花木的芳香所浸润。能生活在这些大自然的婴儿群中真是幸福。我和小花小草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都生活在庄子的《齐物论》中。平等的世界,哲人的乌托邦,就在眼前最平常的园地里。
人类伟大的母亲,无论是西方的夏娃,还是东方的女娲,都是赤条条的,她们美丽得无须任何装饰。她们的生命永恒地静止在青年时代,多从未见过她们苍老的脸孔。既然原始母亲如此年轻,那么,我自然可以永远是个孩子,如果额头上长出了皱纹,躯体内也该有一双孩子的眼睛。
人类下体遮羞物愈来愈精致。开始是叶子,以后是麻布,现在则是绸缎、金环、玉饰,还有名号、地位、桂冠,而最精致的遮羞布则是称作“主义”的各种学说体系。有个庞大的遮羞物,苍白、贫乏、专横都不要紧。遮羞物的进化是人类进化的一节故事。我喜欢孩子,孩子不需要遮羞布,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很美,连撒尿也是美的。我就看过许多孩子撒尿的雕塑,精彩得很。
谋杀生命的凶手也许可以找到,但谋杀天真的凶手永远找不到。人类正在用自己发明的电脑、电视、计算机、香烟、书籍谋杀孩子的天真,剥夺孩子的童年,但人们看不到凶手,看不到无罪的罪人。也许,某些时候,我也是谋杀孩子的“共谋”,只是自己不知道。
在美国中学校园的草地上,我看到金发少女们在抽烟。烟雾弥漫着,我看到“雾中人”的眼睛非常苍老而且充满倦意。老师只管传授知识,并不留意孩子的眼睛和弥漫的烟雾。美国的学校非常自由。自由带给学生许多快乐,但自由的滥用也抢走了少年眼睛中黎明的亮光。我害怕,害怕看到孩子眼睛里的黄昏景象。
我所居住的城市Boulder,发生过一个谋杀女孩的著名案件。电视屏幕上常常出现这个被谋杀的小姑娘美丽的头像。面对照片,我感到双重震惊:天底下竟然有人忍心谋杀这样的孩子;这孩子的眼睛竟然如此成熟。成熟得像她母亲,成熟得仿佛早已看透这个将要谋杀她的世界。这付眼睛传达给我的信息是:她的眼睛没有童年,在她的整个生命被剥夺之前,她生命中的一个部分,生命的天真,早已经被剥夺。
回到童年,回到割草砍柴的山冈,回到长满青苔也布满幻想的大榕树下。想着想着,觉得自己真的实现了一种梦,真的步入了人类思想的山峰,真的在那里漫游,真的在那里吸取芬芳。当年采掇映山红的时候,我只想到以后要在另一些山脉里遨游,没想到竟然来到这样的山峦,竟然可以采掇人类思想的鲜花嘉卉。这是多么好的人生,想到这里,我对一切都不抱怨。
当年轻人海子自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比谁都要更理解海子。海子即孩子。他太单纯,与一个布满心机的世界完全不相宜。在需要生存策略的时代里,海子的心灵注定束手无策。与其被时代窒息而死,还不如自我了断。忘记是谁说的话:要抹去孩子眼中的泪水,霪雨洒在蓓蕾上是有害的。
只能热爱孩子并用整个身心护卫孩子的世界,不能爱那个践踏孩子的世界。我常用加缪《鼠疫》里那个约医生的话表白自己的心迹:“我至死都拒绝那个让孩子们受到折磨的世界。”
一个民族最隐秘的心灵,很难通过书本去寻找,也无法从外部世界去观察,但可以从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一切。五四运动时,文化先驱者们发现中国孩子照片上的眼睛是呆滞的,没有光彩。这一发现使他们把拯救孩子的声音喊得更加响亮。今天,我虽看到孩子的眼睛不再呆滞,然而,却看到孩子眼光成熟得太早,甚至已带上成年人的狡黠。我害怕看到孩子眼睛里也绷着一根弦,比当年鲁迅看到闰土眼里的麻木还要震撼。
争取人的权利,首先应是争取孩子权利。而对于我来说,首先是争取童心自由的权利,这一权力就如安徒生笔下那个孩子:可以道破皇帝新衣乃是骗局的权利以及道破之后不受皇帝制裁的权利。对于我,灵魂的主权就是像孩子那样直言直说即童言无忌的权利。
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刚诞生时他的母亲就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多么丑,我又多么爱你。”不管孩子有多少缺陷,但对孩子的信赖不可改变:开始于生命的第一页,而无最后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