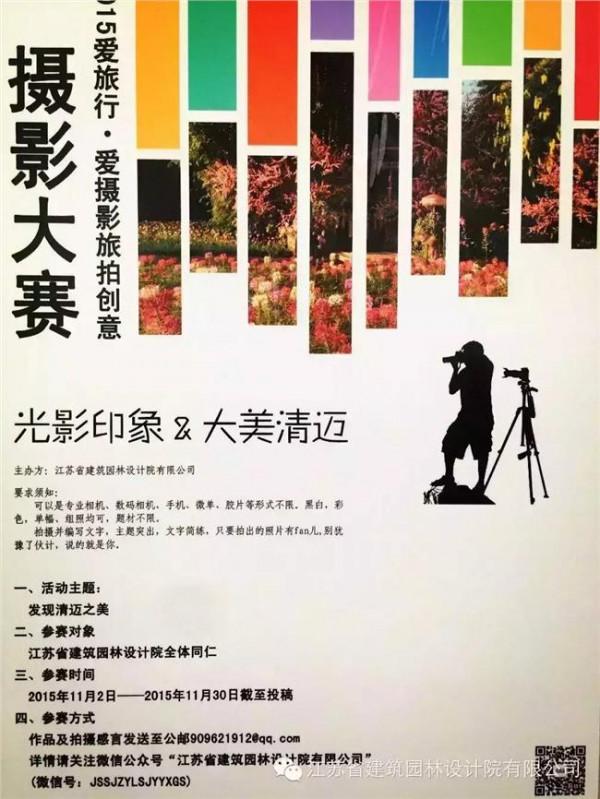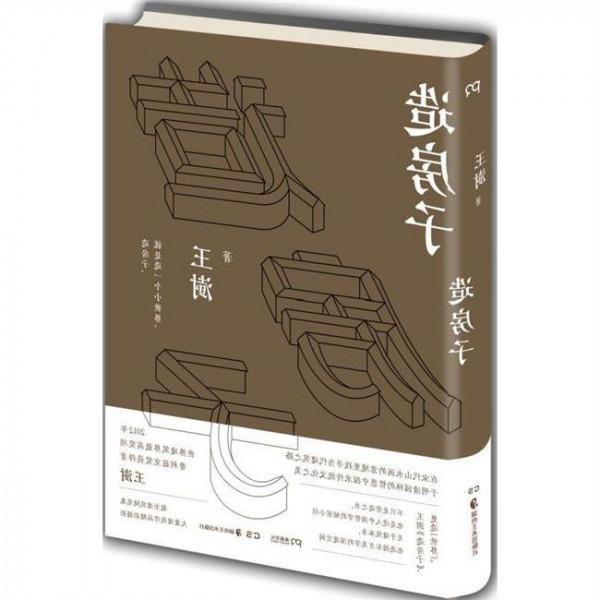转载:砖房·园林·设计起点——建筑师董豫赣访谈
引 子 从2002年至今,董豫赣历时四年在北京郊区设计了一座别墅——清水会馆。清水会馆全部用砖建造,因此也被称作砖房。起初设计砖房时,董豫赣尝试通过局部的片断性来消解通常意义上的建筑整体性。这可谓他对建筑设计起点的一次探索。
随着设计的深入,也同时随着他中国园林研究的深入,董豫赣感悟到一种不同于西方建筑学的新标准——强调建筑是包括建筑在内的更大范围内的关系而非实体本身。这可谓他对建筑设计起点的又一次探索,一次现代建筑中国性的探讨。
建筑标准(自明性)和设计起点,是董豫赣一直思考的问题。这贯穿了他早年的家具建筑研究和当前的中国园林研究,而这也反映了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当代中国,考虑文化、地域因素,如何进行建筑创作?通过中国园林研究,董豫赣认为:建筑创新必须超越形式,因而首先必须是建筑标准和设计起点的创新。
清水会馆既是一个砖房,也是一种园林化的当代北方“大院”,还是一个探索设计起点的建筑案例。因此,本文通过清水会馆设计及建造过程中一些问题的讨论,揭示了董豫赣多元建筑“言说”背后的一贯思考。
砖房·设计起点 问:砖在清水会馆中有两个层次的作用:其一,作为一种承重结构,它本身有一种力量感;其二,它同时又是作为一种维护结构,是一种面层装饰。这里我想与你讨论一下顶棚用砖装饰的问题。顶棚用砖作面层是一种最极端的维护方式,因为它最反常,最违反力学性能。
对此,我并不怀疑太多,因为它毕竟已经做出来了。我感到疑惑的是另一个相关层面,即由于顶棚和墙面浑然一体的处理方式会让人怀疑砖墙作为结构的真实性和力量感。
而路易·康的许多建筑在材料使用上是很分明的,如该用混凝土梁的地方就用,该用砖的地方就用砖,所以整体的力量感很强。 董豫赣:这个问题,在我写《极少主义》的时候已经想过很多了。在西方建筑传统中,真实性问题是从道德价值转变过来的。
它就是要把一切原本的东西表达清楚——原来是结构的就让它显出力量;原来是屋顶的就让它轻盈,诸如此类。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悖论:如果一切东西都自明了,那就意味着你这个房子就只是表达结构。
然而建筑不只是结构问题,你在结构之上一定还有其他东西要表达。路易•康有他的信仰,比如犹太教什么的。我觉得我想表达的东西和他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与其假装某种信仰去理解别人,不如很真实地对待自己。
同时,我和学生们讨论过这个真假问题。比如说,你给顶棚抹灰大家不会认为有问题;而你给顶棚贴了瓷砖,就突然出来一个结构问题,说这是一种装饰。可如果我不关心材料和力量的话,我就觉得讨论抹灰、贴砖跟贴瓷砖到底有多大区别并不很有意义。
事实上,我有另外一套价值标准。你可以认为我回避了。可是这另外的标准告诉你建筑不只是表达一个结构,表达受力。比如李渔做窗户就是追求一种混淆真假界限的状态。区分真假在文物建筑保护里面特别需要,但在设计中未必。
问:我们建筑馆的顶棚就贴的是瓷砖。但是前两天,瓷砖松了,掉下来了,这就很危险。尽管在建筑中不存在功能或者结构的绝对性,但建筑可能还是存在着某种自律的因素。而这会导致我们大家选择不同标准时不那么平等,会有高下的差别。
就像李渔模糊真假的做法,也总会有模糊得妙或者拙的分别。 董豫赣:李渔在谈到窗格子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求坚固。不过在坚固之上一定要有别的原因,否则,这就变成了经济学而不是建筑学——这是我的学生张翼阅读李渔时发现的。
我同意你所说的等级,但我觉得那不是惟一的。比如顶棚用砖,这固然抵触到了建筑学一个重大原则的边缘。可是我有另外一套标准,并不太关心结构的清晰表达或真实性什么的。而且我能够实现这种做法,能够让它不塌,所以这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也许我现在强调我的另外一个标准,所以会都用砖。可能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那么重要时,我反而不一定用砖。恰恰因为它现在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你就必须选择。
问:是否说你是在采用一种反讽的方式,通过故意挑战常规来表达你的立场? 董豫赣: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故意挑战。故意挑战常规是因为你在这方面极其厉害。如果我的结构非常厉害,我同时又是一个建筑师,我可能会去挑战。可是我不是,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我做建筑的一个重要起点。
问:实际上,您是在超越一个固有的标准,在为建筑创新寻找一个新的起点。我想问:您觉得这种新的起点和创新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比如说密斯的柏林国家美术馆,我们看了以后会被感动。不管密斯是出于力学的还是哲学的考虑,它的效果是能打动人的。
所以我会想,如果创新是一种个人主观的东西,那我为什么会被它打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密斯不就成为完全孤立的一个人了吗? 董豫赣:我们之所以欣赏密斯,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从密斯这一体系上来的。
我们相信结构的清晰性,有时候甚至是迷信。密斯相信阿奎那哲学,阿奎那的意思就是通过理解可以接近上帝。所以密斯认为:通过结构力学的极端真实表达,他也能接近上帝。那我们的迷信在哪儿呢?我们有时候对别人的哲学未必真的理解,可我们就是相信那个形式。这就是训练的结果。没有这个训练,密斯的方式未必能打动你。
问:可是一个外国的普通游客,他不一定有很强的中国建筑知识背景,但他在苏州园林里也会被打动。这种打动又是源自什么?我在想:建筑中是否有某些人类共通的东西,即建筑中是否有自律性的一面? 董豫赣:一定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做的东西就没有必要跟人家交流了。
你完全是自己说,自己听。这是一个绝对民主的可怕现象——每个人都有说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听的权利。 外国游客他们可能会对中国园林感兴趣。但是,你要意识到,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基于他们知识背景的。
举一个例子,王澍带我去杭州文澜院看一堵墙,被雨霉得不成样子的一堵墙。在我眼中,它就像一幅北宋山水画。而王澍说赫尔佐格他们也十分喜欢这堵墙,在那儿猛拍照片。不过我想他们之所以感兴趣和我肯定不一样。
所以交流是需要平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老说“小众”。“小众”意味着一小群人对共同在做的事情有一个基础性的了解。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可能是非常个人的,可是他必须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平台。
这样才构成了交流。否则的话,我根本不认为是一个交流。那如何获得这个平台呢?作为一个教师,我更相信教育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我们对西方建筑学的那个平台看来已经非常熟悉,而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平台却不是那么熟悉。
我们其实有这个平台,只是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所以要自觉地找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李兴钢他们拉着我一起看园林的缘故。我觉得在当代,自觉性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没有一条清晰的道路可以寄托,既然没有了先启,所以要靠自觉。自觉至少是对麻木的一个刺激。
园林·设计起点 问:对于清水会馆,王欣说只要用砖就会有一种整体性。这是一种物质层面的整体性。除此,清水会馆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整体性? 董豫赣:对此,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就是片断性。这个设计的起点就是我不再关注以往的整体性,而关注每个局部的片断性。
我在做每一个片段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用砖,也没有设想它具体将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这次想要的一个新起点,跟过去不一样的起点。至于说由于用砖获得了一种整体性,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我是拿砖做事,我不是拿砖来做砖。我只是把砖当作一个工具,但糟糕的是,大家后来都把工具当成目的了。这就像苏州园林中,大量的白墙赋予了园林某种整体性。但园林一定有其他的东西,它的精华一定不只是白墙。我的房子也是这样,我真正想表达不是砖。
问:您觉得苏州园林有什么样的内在整体性?或者它的精华是什么? 董豫赣: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超出了我的实践。我对苏州园林的理解肯定要比我对盖房子的理解要大、要深。恰恰因为这个,我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做与园林相关的建筑。如果我做建筑超出了我对园林的理解的话,我就会觉得黔驴技穷了。
问:您研究中国园林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董豫赣:我从园林研究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看到了我自己建筑设计标准的可能转向。西方的建筑学是以建筑实体为核心的;而在中国园林中,建筑单体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时,建筑、自然和人等要素间的关系成为了关注的重点。
以前我会对建筑本身极其敏感,可现在我会对关系更加敏感。过去一贯训诫我的关于建筑整体性、建筑比例等的问题,我现在都可以漠视了。我漠视是因为我有了新的标准转向——它有能力寻找设计新的起点。
比如在清水会馆中,有些墙砌得不太符合我的要求。一开始我挺失望,可是现在我不那么在乎了。因为我觉得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在某一堵墙上了,而在一个大的关系上。我把握住了这个大关系,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问:在清水会馆中,您是从一个实体的片段开始设计。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您又通过园林研究开始转向室外虚的院落经营。这种转变实际上也导致了冲突和矛盾。比如后来您做院子的时候,会不断地修正片断性的实体。在这里想问一下,您从关注片断性实体到关注院落虚体的转变过程中,哪些元素是冲突最激烈的? 董豫赣:我觉得这里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关注实体本身;而后者是在经营一种关系。
这可以从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认为最成功的是入口有槐树的院子,它很容易出效果。
入口处的龙爪槐突然把你压低,它对你的行为构成影响,这是第一点。龙爪槐它还产生一个明暗。这不是说光线扫在墙上,随着时间变化的明暗,而是中间整个空间的暗。这样中间低矮的暗空间就和旁边高的亮空间构成了对比关系。
这是我以前领会不到的东西——树木开始跟周边的建筑实体等同。 还有那个“合欢”院子。当野草长起来的时候,并且长得非常高的时候,这会让人觉得旁边的院子在往前靠,这样就会改变了远近关系。
尽管我在写论文时早就知道了这点,说画论里面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远近法。但这次我是在自己设计的房子中感受到了这一点。可能我以前在其他地方也见过,但是我注意不到这一点,没法自觉地利用。
也就是说,我下回有可能先做这一块。 还有一个体现我转变的例子。我这个房子真正的总图设计的起点是游泳池。我做游泳池的时候,希望水被充分表现。在斯卡帕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表现水。他的方式就是把水流引到一个桌面大小的一块板上,形成一个迷宫形,让水尽量在这儿绕几圈,让水停顿。
然后你就注意到水了。而在中国画论里面,你一定要看到水的各种欲望,众多不同欲望的表达就是要和不同的东西发生关系。比如,水跟石头撞上就成了瀑布;水流进一个深潭就变成了镜子。而正是对不同欲望的表达让我发生了转变,让我开始更多地经营关系。就像白居易说他修竹是为了迎风,清池是为了见月,他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使内外发生关系。
问:那你是不是觉得:实体和虚体、自然元素和人工元素应该放到同等地位上去推敲? 董豫赣:我的理想是同等的。但我处在转变过程中,所以会有意识地矫枉过正。在短时间内,我甚至会放弃一面,而专攻另一面。园林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且是一个你可以永远不断吸取的东西,因为它在历史上积淀的东西太多了,有我个人不可能抵抗的东西。
问:说到欲望,这让我想起了密斯早期玻璃摩天楼的方案。其中有一个是曲线形的平面。密斯说他就是要从各个角度来展现玻璃的欲望——透射和反射。由于是一整面的玻璃幕墙,你可以看得见柱子在后面是悬挑的,同时你还能看见顶棚的水平面,这在古典建筑中是看不见的。
同时,玻璃又会产生反射,这让玻璃建筑又具有了实体性,具有了古典建筑的体量感。最为关键的是,连续的弧面让这两种性能统一在一起了。所以密斯在一个建筑中体现了玻璃的各种欲望。
董豫赣:就像阿尔瓦·阿尔托所说的(大意),现在最好的状况就是理解一个事物的细微差异,而不是引入更多的东西。比如清水会馆中会有雨水口和柯布西耶的落水口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柯布要表达的是那个建筑物体本身,是为了证明形自身;而我是要让水和石头结合起来,要让水砸在石头上,是追求一种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细微的理解,你最后只能看到一个形。当然这个形十分关键,但建筑不只是形。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只关注形本身。
问:我来清水会馆参观有好几次了。前几次是两三个人,而今天则有十几个人。前面您说到自然的元素会对空间关系有一个主动的改变,我想人也挺自然的,所以人也会对庭院空间有影响。就像一个院子里种一棵树和四、五棵树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十几个人在会馆中和以前两三个人在会馆中是感觉不一样的。这就牵涉到清水会馆本身功能的问题。它是否就真是一个住宅还是一个会馆?因为使用者数量的不同会对建筑以及庭院有所改变。 董豫赣:对。这点看似不重要,其实很重要。
我相信有些房子适合一个人呆着;而有些房子适合一群人呆着。这也是一个不同的起点。有的人爱静,有的人爱闹。这两个房子呢?小房子(注:小房子指祝宅,董老师设计的清水会馆旁边的另外一个住宅)的主人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他的房子需要有各种朋友聚会的地方。
而大房子(清水会馆)的主人的性格和前者不太一样。他跟我描述他的理想,说他将来退休以后住在这。会馆不再是业务上的使用,应该是很悠闲的生活状况。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是有很多人在里面,甚至有一堆不认识的人在里头生活,能够营造出《韩熙载夜宴图》里面的那种感觉。
问:您当时设计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清楚有多少使用者的? 董豫赣:我对一张朗香教堂的照片记忆深刻。照片中,满山有一大堆朝圣者,估计大部分是建筑系学生,在往教堂走。这时我就在想朗香教堂到底适合一群人祈祷,还是适合几个人祈祷?我相信任何功能的讨论都不可能绝对精确,但建筑师自己心里必须有底,有个模糊的概念。在这个房子中,通过和业主的交流,我觉得最理想的情况是有一堆目的不同的人,在各自使用不同的空间。
设计起点·砖房·园林 问:甲方和许多参观者认为清水会馆在总体空间感受上是一个北方大院。然而,您学习的园林却是江南的。这就带来南北气候差异的矛盾。您追求李渔的终极理想,渴望一个没有门窗的联通空间。这一点在南方很好实现,李渔一个人抱着暖炉坐在那里看窗外就行了。
但在北方的气候却要求建筑有一定的封闭性。这就导致了建筑处理中的一些矛盾。例如,各种镂空的花格墙是会馆中表现的重点,但很多时候却不得不被窗框破坏效果。
而您选择黑窗框并在一些地方进行隐藏窗框的处理就是想弱化这种矛盾。 董豫赣:李渔当时的情况是:冬天外面有一束梅,他关上窗就闻不到香,打开窗他又冷。所以他当时也还有遗憾。我觉得南、北方的区别现在反而被大家漠视。
这个漠视就是大家只关心形式。大家认为南方就应该开放,北方就应该封闭。可是现在我们的抗寒能力和抗热能力都很弱。所以南方,我们现在也要封闭,我们也要借助空调和暖气。所以南、北方的差异反而减弱了。现代生活在变,你不可能要求别人不使用空调。
如何将现代生活带入设计是需要不断考虑的问题,而并非只在形式层面。 现在我们的生活完全变得很脆弱了,完全依赖机械。所以很多传统的东西已经沦为表面了。所以我在苏州做房子时,我也不会全部用大玻璃。
我觉得不能把建筑讨论都建立在形式之上。房子肯定在变,但你应该弄明白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比如说我在北方做院子,我觉得长度要长一点,光线就可以打到里边。这个时候你有选择,你可以晒太阳也可以处在阴影里面。
而在南方,院子的尺度关系不大会变。 面对现代生活,每个建筑师都有自己的工作起点,每个人都能做出非常杰出的工作。比如2002年得普利茨克奖的澳大利亚建筑师(指格伦•默屈特),他给那么多有钱人盖房子,他就强制别人不用空调。但是他把建筑通风做得非常好,让人觉得没必要用空调。这是我非常佩服的建筑师,他是在解决真正的建筑问题,而非简单的形式。
问:下面想问一个元素和元素间关系的问题。中国的古建筑是一种复杂的元素。从外轮廓上看,它有优美的屋顶,丰富的檐下,有柱廊,有座椅还有基座。因此,它是一种丰富而多义的元素。同时,自然的树木也是丰富而多义的元素。
因此在园林中,建筑和自然物的关系也是多义的,是具有丰富层次的。然而在清水会馆里面,所有的建筑实体都是抽象几何形的。几何形要求精确,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最好是精确的几何关系。所以我想问:你采用几何性的元素(建筑实体)和园林中丰富多义的元素关系,这两者间会不会有一些内在矛盾? 董豫赣:我觉得问题的焦点不在几何形上。
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也有非常强的几何性,例如它的轴线对称等。因为四合院里头,生活是被礼仪化、制度化的。
尽管房子本身有优美的曲线,可能会修正几何性,但总体来说它的几何性是不亚于西方建筑的。 可是我觉得园林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介于自然和人工之间的“第三者”。童讨论江南园林时认为太湖石或者说人造的假山就是“第三者”。
它们既不是全人工的,也不是全自然的。江南园林中的房子也都是几何的。但有了一个中间层次的“第三者”,这个中间的层次让人工和自然不那么对立,让两个完全独立的片段可以通过它们发生联系而不觉得突兀,这就是第三者。
在园林中,由于“第三者”的量足够大,所以就会产生独特的效果。 比如说光照到园林中的格扇窗上,窗户投下的影子有时让你觉得特别像斑驳的树影,一样的细碎。而这种很细碎的东西可能会淡化那些几何的东西。
无论窗格投影还是树影,这种细碎的斑驳光影甚至会混淆一些东西。刚才我说过,中国人总在试图混淆一个界限,而“第三者”就是起的这种作用。 在做清水会馆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清楚,不可能有大量的石头在这个房子里头。
这既有资金上的原因,也有工艺上的原因,所以我的重点不在这儿,于是我在尝试在秩序感很强的空间中加入生活。因为当代生活的秩序感不可能那么强,你必须使房子更有趣。所以我希望有一堆人在使用这个房子。
我做了那么多路线,希望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间中发生故事,有种偶然性。我希望它有点像古时的曲水流觞。因为曲水流觞非常的大,还有许多拐弯,可这些弯共同构成一个大的趋势,而不是一条单线的迷宫。就像卡尔维诺所说的另外一种迷宫,就是不确定性的迷宫。当然,在清水会馆中我还是用几何形的手段来达到。但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不是我的建筑究竟达到多高水准,毕竟这只是我盖的第二个房子。
问:是否说假山是古人沟通自然和人工的一种中介,一种方式。现代建筑材料也变了,具体问题也变了,您在挖掘一种当代的沟通方式? 董豫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过去的原则你是否知道。如果你知道了过去的原则,你就有可能知道新的沟通方式。因为你知道了标准,知道标准背后的目的,你就会发现许多新的“第三者”,而不一定非要是具体的太湖石。
设计起点·中国建筑 问:好像您最早的研究是从“家具建筑”开始? 董豫赣:我学建筑学是从美术史开始的。因为当时我所知道的建筑学标准多半是从美术领域里借鉴过来的。当时我在清华开始读美术史方面的书,读完之后我又开始去读建筑史的书。
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都有自己的切入点。有些人的切入点非常宏大——借助一些城市问题;而另一些人的则比较具体——比如借助家具问题。 对我来说,我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建筑切入点,这就是所谓的“家具建筑”(注:家具建筑指董豫赣早年将家具和建筑构件结合的研究)。
我发现密斯和赖特也做过同样的研究,他们都曾试图把家具和建筑构件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安心,因为我相信建筑里面会需要一些“设备”,一些跟人直接发生关系的设备。
后来我研究建筑总会想:结构的高度能不能供一个人坐着或躺着?接着我就想建筑中各种各样的高度,就爱干这个事情。我觉得当时自己思考那些问题对我影响深远,对我现在转向中国园林研究帮助非常大——它老是将我拉回建筑与人的一种直接关系。
我写得最痛快的一篇文章,叫《旁敲侧击》。在其中,我觉得我把以前的研究和园林研究特别通畅地串到一块了。这就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建筑的自明性?自明性的推动力在哪?比如说埃森曼认为建筑中的几何学是先在而自明的,但它们以什么区别几何而成为建筑图表?它们借助结构体系的几何操作可以动。
可是谁让它们动?这就是牛顿第一推动力的问题。建筑应该有它的自明性——这是学科分工的被迫,但它应该有和人有关系的外在起点。早年我在“家具建筑”中体会到建筑发生的内部起点,现在我在中国园林中感受到中国人的智慧,它可以旁敲侧击,里应外合。
问: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中,王明贤策划了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性作品展览。作为当时的参展人,您怎样理解当代中国建筑界的“实验”或“先锋”现象? 董豫赣: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实验。最早的时候,第一我没有房子盖,第二我喜欢建筑这一行,所以我做了一些东西,做了一些至今让我受益匪浅的研究。
后来在王明贤的邀请下,我参加了那个展览。我觉得当时参展的建筑师也没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展览结果也是多元的。
对我而言,实验意味着什么呢?我现在觉得实验既不是生产也不是研究,是一种中间阶段。就是说你急于想生产,要先做个实验,以便后来有机会的时候实现。那个时候,我做了一系列的画家住宅——估计与我那阵子的美术史起点有关,自己建模,甚至把螺丝钉都建出来了。
问:清水会馆的甲方是一个有钱人,国内许多实验建筑的甲方都是有钱人。然而,决定当代中国城市面貌的是国有大型设计院。众多的大院设计师设计了城市中的大量建筑,尤其是普通住宅。而在西方早期现代建筑运动中,众多大师都试图将新建筑的艺术性同社会属性结合起来。
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是否像清水会馆这样的“实验建筑”只是建筑师自我陶醉的作品,是面对现代性的一种消极态度? 董豫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后现代时期。我不认为后现代建筑特别有意思,可是后现代主义本身却是现实的。
我们已经身处消费时代——这是我们可以具体讨论的现代性表现之一,而柯布西耶当年的时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生产时代。当时的许多大师都做过社会住宅,我知道路易•康就做过多年的福利住宅研究。
然而那些廉价住宅项目都是政府项目,政府不为了赚钱,建筑师也不为了赚钱,这样好的作品才可能出现。 当代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了,而且很多问题不是建筑师能够解决的。现在政府把住宅开发全部推向市场,房地产商好不容易弄起来一个项目,他首先想的就是赚钱,怎么可能不盈利让你去实验。
从设计方来看,研究社会住宅也不那么容易。大量的社会住宅由设计院把持是因为:早些年还不存在个人事务所(解放前是有的),而设计院的设计师又没有署名权。
没有个人署名权的时候,恰恰是没有个人表现力的时候,廉价住宅只不过是一个任务而已,设计师怎么可能不断去研究。 讨论到建筑师“个人化”的作品,你不能把社会问题和建筑问题混淆起来。
他们的工作是在建筑学层面上进行探索,对他们的评价也应该从建筑学本身出发,而不该转换标准——并不存在研究社会住宅就一定优于研究其他项目的起点判断——这将意味着社会住宅可以胡乱研究也没关系,因此重要的是研究的专业水平与深度。
另外,我们也应该超越简单的建筑功能属性来评价作品的社会性。比如张永和的作品对许多建筑系学生和设计院建筑师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他的社会性是蛮大的。在当代,你不可能指望谁来搞一个所谓的“建筑新文化运动”。
问:您觉得研究中国当代建筑问题有什么比较好的切入点? 董豫赣:我一直对建筑史很感兴趣。当代离你太近了,它运动的速度过快,让人很难判断它。 还有一点,我仍然觉得最重要的是自觉性。我们说梁思成在一个中国建筑发展的转折阶段,是因为我们回顾他,发现他确实是。
可是你需要一个自觉,你要自觉地意识到你自己也处在一个大转折之中。如果你没有这个自觉,也就意味着你总在等。因为总在等,所以你很难“见到”当代。当你“等到”将来,意识到现在也是一个转折点,就是等到“现在”这个转折点呈现清楚以后,它又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格。
所以只要我意识到有可能我就立刻去做。我觉得起点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时间。给你一年,和给你十年肯定不一样。每个人的方向都不太一样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坚持做下去,方向会越来越清晰的。日本现代建筑的发展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