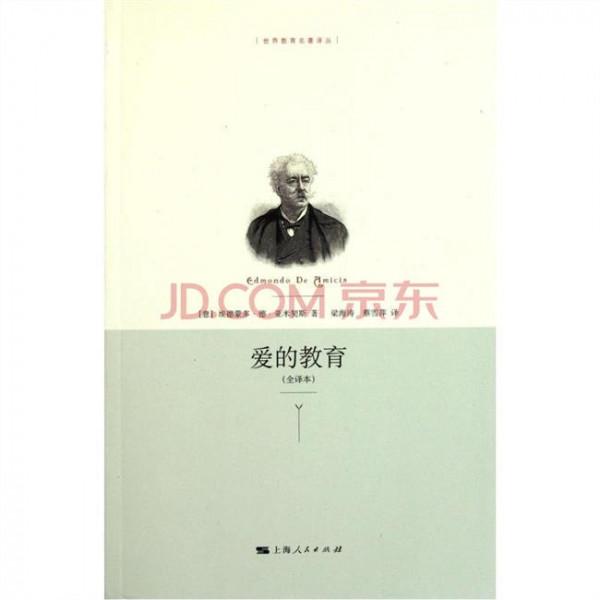邵飘萍的对话 邵飘萍与林白水的新闻观比照
邵飘萍与林白水是同处“五四”时期的著名报刊活动家,他们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和贡献。二人新闻生涯的起点都在杭州,辉煌期都在北京;二人都是我国早期新闻事业职业化的重要推动者:二人都以新闻救国为理想,体现了我国职业报人救国救民、胸怀天下的气魄:二人都以采写独家新闻而著称,采访报道技巧至今仍为新闻业界学习和效仿;二人同为社会启蒙思想家,引导和鼓励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二人同样都因新闻报道而贾祸,为军阀所不容而被杀害,但都为后世新闻记者树立了职业精神的标杆。
如今在有关邵飘萍与林白水的论著中。基本上都是以总结分析二人的新闻业务为主。事实上,从他们二人卓越的新闻业务中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出他们独特的新闻观念,而且二人由于在个人经历、价值观念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得二人的新闻观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邵飘萍与林白水新闻观的一致性
都视新闻事业为社会公共机关。邵飘萍与林白水所办报纸,与之前国人办报有很大不同,不再依附于某一政党或利益集团,而是社会公共机构,他们二人也都为专职报人。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指出:“新闻纸即为社会公共机关,同时也为国民舆论之代表。
”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实现报刊国民舆论代表的途径:一方面,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公共机关,与任何国家机关一样,具有平等、独立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可加以压制,否则,就是不承认言论机关的独立平等地位。
1926年4月25日深夜,北京东郊刑场。随着一声枪响,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轰然倒下。此后不到百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又于8月惨遭屠戮。两位著名报人相继丧命,让人悲叹“萍水相逢百日间”。原来,这是当时的军阀不满于报界的揭露和讽刺,对舆论界人士下的重手。
由于邵飘萍同情革命军,反对张作霖的“讨赤”主张,斥责张的亲日行径,张作霖决心除掉邵飘萍。1926年4月22日,张派人查禁了《京报》馆,逮捕了邵飘萍。三天后,张不顾新闻界的联名上书求情,将邵飘萍枪杀。
革命烈士林白水
张宗昌入京后,压制舆论,对新闻界更是打压有加。对此,林白水毫无惧色。1926年8月,林白水发表文章《官僚之运气》,讽刺财政部长潘复“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引起潘复不满。潘遂在张宗昌面前煽动,使张产生了杀林的决心。8月6日凌晨,林白水被骗至宪兵营,迅即被“判”为死刑并处死。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于军阀黑暗统治之下。法制和民主无立身之地。当一些有良知的中国人开始觉醒,就遭到了军阀惨无人道的杀害。所幸的是,面对反动军阀血淋淋的屠刀,还是有人敢于仗义执言。这种不怕牺牲的壮举,为中国人寻求民主和法制指明了方向。
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
“七八个宪兵从一辆人力车上拽下一个穿白布大褂的白发老人。老人被宪兵簇拥着推上垃圾堆坡上,身子尚未立稳,枪就响了。”
1926年8月6日清晨四时许,北京天桥春茗园茶馆老板目睹了一个老人的被杀经过。这个老人就是民国时代著名报人林白水,他因讽刺时任国务总理潘复为军阀张宗昌之肾囊而遭此毒手——从逮捕到行刑,前后不过三个小时,可见北京当局对之斩立决的迫切心态。
林白水自1901年开始投身新闻事业,前后自办过七八份报纸,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政论家之一。这样一个一生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的老人,临刑前的遗言却是: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林的遗言其来有自,除了自身遭际之外,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沉痛认知。
就在此前,4月26日凌晨一时许,另一位报界名人邵飘萍因得罪军阀张作霖而在天桥刑场被枪杀。这是民国以来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的第一例,留下了恶劣的影响。此后陆续有报人被害,如:1932年初,《新大陆报》创办人王鳌溪因揭露蒋介石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而被捕,后被杀害;1933年1月,江苏《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因报道省府鸦片公卖丑闻而被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杀害;1933年,《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军方枪杀;1934年11月13日,《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因触怒蒋介石政权而遭暴徒枪击致死;1939年秋天,《大美晚报》主笔朱惺公因发表反对汪精卫媚敌的文章亦遭暴徒狙击而死……
那是一个皇帝虽已被推翻但专制阴魂不散的时代。不过,清末以来民智渐开、军阀各霸的局面使得人们享有前人所没有的较大社会活动空间,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学说都纷纷登场,各类社会团体也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作为报人来说,如《新民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还是基本可以实现的。民国时代有那么多的私营报纸杂志,自生自灭,循环不息,就是证明。
也许能说,他们本可以不死,因为他们曾经面临过另一种选择。张作霖曾给邵飘萍汇款三十万银元,远超当年袁世凯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梁婉拒,该文发表,对袁世凯称帝是一大打击),创下民国年间封口费之最;潘复曾责令林白水在报上更正并且谢罪;国民党法庭上的军法人员曾引诱王鳌溪改弦更张,按政府旨意办报……按常人的理解,人都有父母妻子,他们也本可以做一点妥协,哪怕虚与委蛇也好。
但是,邵飘萍悉数退回三十万,对家人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林白水的答复是:“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王鳌溪当庭拒绝,据理力辩。于是,厄运注定要降落在他们头上。
民国年间报纸林立,从业者良莠不齐,风花雪月者有之,鸡零狗碎者有之,封建卫道者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为什么邵飘萍、林白水们偏偏独立不羁,傲然面对专横野蛮的权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报人不为稻粱谋,不顾妻子计,他们是为谁而生?
没有邵飘萍,就没有《京报》;没有林白水,就没有《社会日报》。报纸是他们施展身手的阵地,他们为报纸而生,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转换为:报纸为谁而办?
“应即大声疾呼,方无愧此喉舌”
关于这点,马克思早在1849年就有过清晰的思考:“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一言以蔽之,报纸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自然是为人民而办。
令笔者惊讶的是,虽然晚于马克思数十年,但梁启超极可能是中国最早独立提出报纸喉舌论的人,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写:“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梁启超认为,报纸有为一人、一党或一公司之利益而办,也有为一国乃至为全人类之利益而办;他倾向于为国家办报,渐进于为人类利益而办世界报。
笔者发现,邵飘萍、林白水们实际上继承并发扬了梁启超的新闻理念。邵飘萍认为,新闻社是与任何国家机关平等的独立社会机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
王鳌溪在所撰《报业革命之商榷》中说:“号称民众喉舌者,对民众之所欲言、之所不能言、之所不敢言者,应即大声疾呼,方无愧此喉舌,若竟不为民众说话,而反为民众公敌散布其麻醉剂,宣扬其赞美诗,以欺骗民众,则其人格之卑污,较雉兔而尤甚,更何论乎社会导师。”
王鳌溪的好友、《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对王的观点极为推崇,常常对报社新人讲起王氏事迹,并背诵王氏一些诗句来勉励后辈,如“人民喉舌要尊重,我辈头颅要看轻”、“世无公道全凭我,舌不自由枉有头”等。陈本人曾在1936年应邀就中国的新闻事业作过一次精彩的讲演,他分析道:“中国的新闻事业不发达,大概以外在原因为最多,尤其受政治影响,使舆论界得不着十分的保障,大家兢兢业业,连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报纸原是民众的喉舌,喉舌受了钳制,他如何可以发扬光大呢?”
曾任《大公报》社长的吴鼎昌也说过:“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的这张报纸是毫无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平心而论,我们无法怀疑吴所说的话,指斥他作秀,他不计盈亏、独力筹措五万元恢复已经停刊的《大公报》;等他出任国民党实业部部长的时候,又主动辞去社长职务以保持报纸的政治独立性。我们更无法怀疑邵飘萍、王鳌溪等报人的理念,因为他们已经以生命做出了沉甸甸的回答。
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邵飘萍等这样一批充满道义感的报人,才使得《大公报》《京报》《新民报》等几大报纸至今仍在中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报人为谁而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报人们面临的一道生死选择题。笔者无法想象,今天的我们如果处在清末民国时代,会有怎样的表现。
“为人民服务”
放眼世界,“报人为谁而生?”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大同而小异。国际上素有将媒体列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第四种权力”便是以监督政府、开启民智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