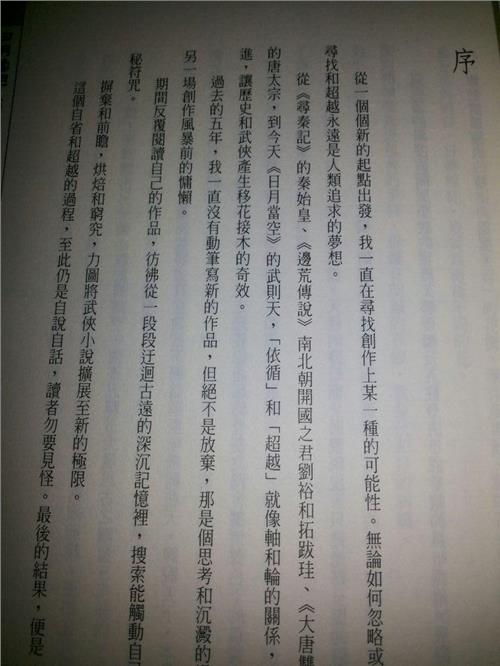金庸与古龙笔下的侠之比较
论及武侠小说,很难不从“侠”的观念入手。说到底,武侠小说是一种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类型。用梁羽生的话来说:“‘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手段。”①究竟什么是“侠”?“侠”的基本特征又有哪些?专家们的观点是纷纭复杂:刘若愚最早在《中国的侠》一书中列举了“侠”的八种特征;其后,侯建在《武侠小说论》中总结“侠”的十种特征,只有第一条“尚气任侠,及人之急”与刘若愚所讲相符;而田毓英在《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一书中列举“侠”的十一种特征,又都各有自己的说法。
②其实,仔细分辨,不难看出各家所赖以观察的角度不同,故其结论相去甚远。在现存的文字资料中,“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文中“游侠”、“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征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后世关于“侠”的观念在此已露端倪,但此说还语焉不详,且无具体例证。一直到《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因此,后世谈“侠”者大多本于此: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可与这段话照应的是《太史公自序》中关于《游侠列传》写作动机的说明:“游侠救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 ,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传中所记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之所作所为,大致不出此一范围。自司马迁以后,除班固沿袭之外,历代史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
从司马迁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侠”的特征是“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及“赴士之厄困”。再来看看现代人是如何给“侠”下定义的。《辞源》中解释“侠”说:“旧时指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人。
”《中华字海》中是这样解释“侠”的:“旧称有义气、能扶弱抑强、舍己助人的人。”《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对“侠”解释道:“旧时指有武艺、见义勇为、肯舍己助人的人。”基于上述这些古今给“侠”作的定义,并结合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侠”的特点,本文认为,所谓“侠”,就是指立身于“助人行善惩恶”、“重言诺”,并身负武功的处世者。
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古龙前期的作品是摹仿金庸创作的,还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故不在本文探讨研究的范围内。换言之,本文所要比较分析的,是金庸主要作品及古龙中后期主要作品中的“侠”形象。
对“侠”的形象,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入手来分析金、古二人创作上的不同,即:爱(爱情)、恨(仇恨及惩恶)、情(主要指友情)、义(侠义精神)。
一、侠之爱
爱情的描写,在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已普遍占有重要的位置,梁羽生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
”③金庸与古龙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
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是有深度的,就连以写情闻名、为情而生的女作家三毛对此都推崇备至,她写道:“我曾对金庸先生说:你岂只是写武侠小说的呢?你写的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也就是‘情’字。
”④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景观,在审美特征的角度上来分析,最突出也是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悲剧性。可以说,金庸笔下的爱情故事,大多属于一个悲情世界。《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与霍青桐、喀丝丽姐妹之间的爱情悲剧,《雪山飞狐》中胡斐与袁紫衣、程灵素之间的爱情悲剧,《连城诀》中狄云与戚芳的爱情悲剧,这些都是金庸笔下此方面的典型。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金庸笔下的爱情悲剧中,正是将侠的爱情——这一有价值的东西掷入毁灭的火焰中(这里所说的“毁灭”,是指所遭受到的挫折、失败和牺牲)。悲剧给人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即在审美愉悦中产生一种痛苦之感,并使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
在这里,则表现为金庸试图展现对爱情本质的思索。应该看到,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悲剧,不再是“不自由与不自主”的社会悲剧,其笔下的侠已经被赋予了超越历史现实的自由追求爱情的权利。
那么,在此基础上,为什么还会产生悲剧呢?陈家洛的爱情悲剧,应该说是其本身性格及其文化观念与价值的悲剧;胡斐的爱情悲剧,却是受命运的捉弄,即是命运悲剧;狄云的爱情悲剧更是直指千百年来的一个难解命题:究竟情为何物?在金庸笔下的爱情中,人们可以思考得更多。
此外,除了这种纯粹的悲剧,金庸还创作了“悲喜交加”的爱情故事,最突出表现这一点的就是《笑傲江湖》。令狐冲爱岳灵珊,但岳灵珊却爱上了林平之,这是他在爱情上的不幸;而岳灵珊身亡,令狐冲最终与深爱着他的任盈盈结合,这又使他在爱情上得到了补偿,并最终拥有圆满的结局。
然而,这种悲喜交加的爱情遭遇所形成的结局是极其微妙的,因为令狐冲自始至终爱的是岳灵珊,而他对任盈盈,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感动来得更确切些。金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避开了这种判断,避开了对令狐冲心理感受的描述,把体味、揣摩、判断和研究的谜团完整地交给了读者。
这些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更高一层的审美境界,这其中包含了更深刻的关于人性与爱情的思考。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笔下还出现过许多为爱情发疯发狂的“情魔”,如《碧血剑》中的何红药、《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等,这些人物形象也有很深刻的审美意味,但已不属于本文探讨的“侠”的范围,故不赘述。
再来看古龙笔下的“侠”的爱情,古龙的笔下鲜见悲剧意味的爱情,似乎只有李寻欢与林诗音的爱情勉强可以罗列其中。但是,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林诗音其实是不值得李寻欢去爱的,她被龙啸天迷惑在先,又纵子龙小云无理在后,李寻欢在她心中的分量显然是不够重的。
所以,即使是李寻欢这样的情痴,最终也脱去樊笼,和孙小红走入真正的幸福。
除此之外,古龙笔下的“侠”的爱情,大多是一种简单得甚至没有理由的样式,正所谓“爱了就爱了”。爱情在古龙的笔下来得太快,太突然,有时甚至是太泛滥,多情在古龙笔下衍化成滥情,楚留香、叶开、陆小凤等等这些“侠”的前头往往被冠以“风流”二字。
同一个人物身上发生了太多的爱情故事(有的甚至不能称之为爱情),也就不能一一挖掘审美层次上的意义,探索爱情背后的人性。所以古龙笔下的爱情景观尽管有时很绚烂,却缺乏深度,和金庸相比,就自然而然显得苍白无力。
其实,这也与古龙小说的文本结构有关。古龙有许多小说是形成系列的,即有关某一个主人公在不同故事中的遭遇,如《楚留香传奇》、《陆小凤传奇》等等,这些系列小说中不变的主人公往往只有男性,而女性形象是作为附属品出现的,不同的故事中会出现不同的女性形象,从而肯定会和男主人公展开不同的爱情故事,而这些爱情故事是不关联的,每一段爱情对男性主人公的影响只限于本个故事,在其他故事中,男性主人公又是一个全新的个体形象,故可以继续其他的爱情游戏。
此外,金古二人笔下“侠”之爱的不同还表现在性的吸引对“侠”的影响。试将二人笔下的杨过与叶开比较如下:与杨过相应的女性有小龙女、郭芙、郭襄、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但他始终对小龙女坚贞不二,而与其他女性严格划清界限,或姐或妹或友,绝不越雷池半步;与叶开相应的女性有丁灵琳、翠浓、马芳铃、沈三娘、上官小仙等,他除了与丁灵琳两情相悦之外,也与其他几位女性发生过或深或浅的性接触(包括愉悦心理)。
杨过与叶开同为不拘小节、视世俗理法为无物的“侠”,却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值得推崇的似乎应该是古龙。尽管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古龙笔下充斥了许多色情的性,但在根源上,他似乎比金庸更接近人的本质。
洒脱不羁如杨过者,尚不能对众多的性吸引心动(这里仅仅指心理上),更不用说那些“侠之大者”如郭靖、萧峰等人了。在此,古龙的观点是符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的,即符合一种非理性的深层人格,这种心理是理性所不能控制的。
人类(尤其是男性)对性吸引的反应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感性反应,即使是在理性(主要是道德观)的约束下,生理反应和心理愉悦也是在所难免的,金庸却避开了这种描述,将将自己笔下的侠推到了一个纯理性的高度,在此,或许会使侠显得更冠冕一些,但同时也背离了人性的要求。
但这儿有一个特例,那就是韦小宝,只是性在其中的取舍已脱离了爱,或者说超越了爱,并且和封建婚姻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发生这种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跟二人所接受的教育是有关的。金庸出身书香世家,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性观念上自然就相对保守;古龙则恰恰相反,他接受的大多是西方教育,其小说又大量借鉴吸收了西方侦探小说的情节特色和西方散文的语言风格,故在性观念上也就相对地开放,呈现出一种反传统的态势。
二、侠之恨
这里所要说的侠之恨,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侠客复仇,一是指侠客惩恶。
前者为侠客的私人之恨,后者则为侠客为打抱不平的侠义之恨。
先来说侠客复仇。在武侠小说的发展史上,复仇主题是源远流长的,尤其是在近代武侠小说兴起以来(即20世纪初开始),复仇一度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要情节支柱之一,这一点在金、古二位的作品中也不例外,金庸的《碧血剑》、《雪山飞狐》、《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及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风云第一刀》等,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复仇的情节。
但在二人的作品中,复仇之侠最终往往放弃了复仇的使命,“盈盈一笑,尽把恩仇了”。这样一种选择显示了金、古二人最终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然而决定二人这样选择的原因却又是不尽相同的。
金庸笔下如张无忌、狄云等人,自身拥有佛家思想中的一种人格特征——宽恕,因此张无忌才能抛开父母惨死的仇恨,于光明顶上极力化解正邪两派决战在先,于六合塔下冒死救助六大门派人士脱困在后,要知道,这其中六大门派的许多高手都是当年被张无忌认作是杀父杀母的元凶,他也曾发誓杀尽这些仇人。
然而,他最终以佛家和平止杀,也终结了复仇。狄云对万圭父子更是如此,他身怀绝世武功之后并不挟技报复,反而还给当年诬陷迫害自己的仇人送药治病,仇恨在他心中早以被佛家思想消解得无影无踪。除此之外,金庸笔下复仇之侠终止复仇使命,还有一部分是出于儒家思想,如杨过和萧峰。
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和私怨”,后来更是在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下飞身下城,不顾危险地救回郭靖。萧峰更是以死这个特殊的方式,来泯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怨。
面对个人仇恨与国家民族大义,儒家思想选择了后者。
反观古龙,他笔下如李寻欢、叶开师徒,放弃了自身的仇恨、父母的仇恨,是出于本身所具备的伟大人格——博爱,这很明显地也沾染上佛家思想的痕迹。而儒家思想在古龙的笔下似乎难见痕迹,这一点就像是第一部分中分析过的一样,古龙很少接受甚至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就不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将会在第四部分展开论述。
这里有个独特的地方需要提出,那就是古龙的作品中不仅终止了复仇,还用反讽的手法来消解复仇的意义,这具体体现在《风云第一刀》一书中。书中有两个复仇者:叶开与傅红雪,值得把玩的是,真正的复仇者叶开愿意放弃仇恨,而作为复仇者替代品的傅红雪,却为了一个虚假的复仇使命痛苦了二十年,这不能不说是对复仇的一种讽刺。
讽刺一种表面肃穆实际荒诞的东西,其意义本身大于终止它。在这一点上,古龙又超越了一步。
再来说侠客惩恶。
侠客惩恶时往往会杀人,金、古二人对此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金庸选择了淡化,他在笔下往往避开侠客杀人的场面,避不开的也尽量少用笔墨。而古龙的态度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选择消解,他笔下的楚留香、陆小凤都是双手不沾血腥的“侠”,或者像傅红雪一样,杀完人之后感到恶心,甚至要痛苦一场;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噬血的暴力倾向,常常将杀人视为一种艺术,杀人后的快感更是不甚美哉,这种快感没有比西门吹雪的这段话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的了:
这世上永远都有杀不尽的背信无义之人,当你一剑刺入他们的咽喉,眼看着血花在你剑下绽开,你若能看得见那一瞬间的灿烂辉煌,就会知道,那种美是绝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的。(古龙《陆小凤》“远山传歌声”)
将杀人当作“神圣而美丽的事”,能于杀人中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即使杀的是恶人,也无法掩饰其隐藏的噬血欲望。正如艾弗洛姆(Erich fromm)所指出的:“这种人通过回到人以前的生存状态,通过成为一个动物,从而摆脱理性的负担来寻求生活的答案。
对于这种人来说,血就是生活的本质;流血则是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强者,从而凌驾于一切人之上。”⑤这里,恐怕和古龙创作的商业化以及其自身因遭遇坎坷而产生的阴暗心理不无关系,而此亦是古龙作品的弊端之一。
三、侠之情
这里要说的情,不是爱情,而是友情。在此一点上,金、古二人的笔下之侠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金庸笔下的“侠”们,虽或有师门兄弟,或有帮派团体,看起来同道甚多,热闹非凡,但却没有或缺乏真正的朋友,在人群之中,他们是孤独者。
就算是《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虚竹、段誉三人结为异姓兄弟,但却从未见到他们有真正的内心的精神交流,萧峰之死就完全出乎虚竹与段誉的意料。因而这一死也是真正的孤独之死。在此,金庸笔下的“侠”秉承了武侠小说史上的“漫游”者的精神特征:孤独。
这样的“孤独之侠”,作为一个逃亡者,一个边缘人,一个不被理解不被承认的时代弃儿,内心的痛苦是必然的。金庸笔下的“侠”在寂寞和空虚中重新参悟人生,在孤独中和绝望中挣扎抗争过后,成为真正的“侠”。
古龙虽然在作品中也表现“侠”的孤独与寂寞,就像李寻欢,“他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寂寞,但他却偏偏时常与寂寞为伍”(《多情剑客无情剑》第1章);然而,“侠”也总有一两个能真正知心的朋友,如楚留香与胡铁花、陆小凤与花满楼、李寻欢与阿飞、叶开与傅红雪 …… 举不胜举。
这些“侠”和“侠”的知己们,有的自小一起张大,故知己知彼(如楚留香与胡铁花);更多的是表面上相交甚少,认识的时间也很短,但都一见如故,本身所具备的相同气质特征让他们能够在精神上达到惊人的默契。
古龙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来表现友情是如何地真挚,而是将这种情融入字里行间,朋友之间不用多说什么,自然就能心有灵犀。这种笔法符合了庄子的理论:
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⑥
为什么金、古二人在对友情的取舍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呢?其实原因很简单,金庸笔下的“侠”,大多是位高名重的“大侠”,高处不胜寒,他们在自己的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精神上也处在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度,所以他们孤独,他们寂寞。
古龙笔下的“侠”大都是浪子型的,游戏人间的他们虽然也时常寂寞,但孤独者不只他一人。其实,古龙笔下的朋友,往往是两个同样孤独的人(如李寻欢与阿飞),精神境界一致,共鸣也就在所难免了。另外,古龙还很擅长写正邪双方敌对者之间的惜情,无论是西门吹雪与叶孤城,或是楚留香与无花,还是阿飞与荆无命,他们都在敌对中惺惺相惜,产生一种超越友情的奇妙感情。
李寻欢就曾经感叹:“一个最可怕的对手,往往也会是你最知心的朋友。
”(《多情剑客无情剑》32章)。如此“敌友不分”,固然有愤世嫉俗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强调“理解”——只有最可怕的对手才拼命试图准确了解你。因此,古龙才说:“有资格做你对手的人,才有资格做你的知己。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了解你。
”
四、侠之义
唐代李德裕在《豪侠论》中云:“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在武侠小说中,“下”与“义”是密不可分的,侠之义乃是“侠”之所以为“侠”的精神支柱。那么,究竟什么是“义”呢?简言之,所谓“义”,是指“正义”、“合理”、“应该”。
而“侠”对“义”的理解,应主要着眼于“助该助之人”。对“该助之人”的界定,金、古二人的侧重点是大不相同的。
金庸在“义”上主要立足于民族大义,他把“该助之人”界定在处于民族斗争中的老百姓范畴内。
陈家洛、郭靖、萧峰乃至韦小宝,他们都在民族斗争中绽现光芒,他们身上最突出、最伟大的品质就是民族大义、民族气节。陈家洛毕生的志愿就是推翻满清的统治;郭靖夫妇为抵抗蒙古入侵,双双战死襄阳城;萧峰以死来化解宋辽的民族恩怨……在金庸的作品中(主要是前期作品),民族大义往往高于一切,为此,可以放弃爱情,也可以放弃仇恨。
陈家洛为了争取乾隆的支持,不惜出让自己的爱人,杨过有感于郭靖的民族大义,终于打消了为父报仇的念头(其实是场误会),他们都在民族气节(主要是汉民族)的过滤下日趋走向自我的熏陶,从而最终能成为“侠之大者”。《神雕侠侣》第二十回,金庸借郭靖的口表达了自己的这种观点:
郭靖又道:“我辈练功习武,所为何时?行侠仗义 、济人厄困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驻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各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金庸将“侠”与建功立业(这是“为国为民”背后的思想根源)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对明清公案小说中侠客为朝廷效力的一个继承发展,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金庸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的体现,这就是民族本体论的思想,这是70年代左右香港作家的一个共同点,即一种朴素的爱国(有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爱汉民族)情结,此一点与香港多年和祖国大陆分离是有关的。
古龙的作品却几乎全然看不到跟民族斗争有关的情节。其作品有意地淡化甚至消解故事的背景,这就使得它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来表现“侠”在民族斗争中的大义。
古龙更多地表现了“侠”的江湖道义,“侠”们常常是为了与自己不相关的人或事去出生入死,或寻出杀人凶手(如《陆小凤传奇》之“绣花大盗”),或瓦解某个邪恶团体(如《楚留香传奇》之“蝙蝠传奇”)。
他们的理由非常单纯,正所谓“江湖救急”,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助人”。此外,这也与古龙笔下“侠”本身所具备的冒险精神是分不开的,好奇心往往会牵引着“侠”的行动。这一方面,古龙表现得更为人性化的一点,在于其笔下的“侠”有时也不想多管闲事,他们也有着常人明哲保身的观念,只是受一人所托甚至与人打赌而为之,其实本身已然在多次冒险后厌倦了这种生活。
这种厌倦,只要看看楚留香每次冒险后的心态就能一目了然了。
在“侠”之“义”上,面对金庸和古龙,本文更倾向于后者。尽管金庸作品中的“义”是汉民族文化积淀后的厚重表现,但是,将此“义”与“侠”相联,却有些失却武侠小说的根本。
说到底,侠不过是江湖中的个体,是以其侠骨豪情而不是丰功伟绩来吸引读者,这也正是侠不同于民族英雄之处。其实金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可以得见于其作品中“侠”在民族斗争中只能以失败的悲剧终结,韦小宝的故事更是反讽了这种观念,然而矛盾的是,金庸依然无法放下这种浓重的英雄情结,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了。
古龙笔下的“侠”只在江湖中显示其“义”,这一种“义”可能不如金庸笔下的那么凝重,那么厚实,然而却接近了最根本的“侠义精神”。“侠”也只有在江湖中才能凸现出其自身的个体魅力和独特的气质特征,而并非是在民族斗争中。金庸与古龙都强调武侠小说要写“人性”,从侠之义上来看,古龙做得更彻底一些。
以上通过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展示了金、古二人笔下“侠”形象的异同之处,那么,自然而然会有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二人谁更胜一筹呢?这不能用简单的“AB”的公式来回答。首先,二人笔下的人物是各有千秋的,金庸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文化底蕴与历史厚度上要远胜于古龙,而古龙则在人物个性特征及商业角度的读者接受层面要更高一筹。
其次,这里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金庸在人物塑造上是有一个变化发展甚至是升华的过程。众所周知,能否揭示人性是塑造人物形象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金庸与古龙都曾对此深表赞同:“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⑦ “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⑧这里所说的“人性”,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个性化特征,一是对人类某些问题的系统化探索。
先来说个性化特征。什么是“个性”?何其芳在《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中这样解释道:“它的个性也恐怕只能说都浸透了阶级性但并不完全等于阶级性的具体表现了。”⑨焦菊隐也说道:“首先抓住这一阶级里各阶层人物所共有的大性格,然后你才能把这大性格提炼,和你的创造中的人物的小性格结合起来而完成一个典型的人物。
”⑩金庸的早期作品中就存在着缺乏或弱化人物的小性格的弊端,陈家洛、郭靖等大英雄尽管也有各自的性格特征,但被大家所记住的却是他们的大性格,即爱国爱民的民族大义。
在此,人物的小性格已经在大性格的映照下黯然无光了。但古龙笔下的人物则不然,他们在行侠仗义的同时,身上的小性格也凸现得淋漓尽致,楚留香的潇洒,李寻欢的忧郁,陆小凤的机智,西门吹雪的孤傲 ……这些都牢牢地被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金庸中后期的作品中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变化发展,萧峰、杨过、令狐冲,尤其是韦小宝,这些人物的身上,小性格已脱离出大性格的束缚,个性化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本文认为,令狐冲这一形象是金、古二人在塑造人物时的重叠之处,他几乎完全接近了古龙笔下的“侠”们,在具备冒险精神及助人于困厄的品质的同时,也拥有贪杯、不拘小节、痴情等难以掩盖的小性格。
再到韦小宝时,金庸实际已超越了古龙。
再说对人类某些问题的系统化探索,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的人性化思考。
在这一点上,金庸侧重的是民族问题、爱情本质问题等一系列厚重的主题,而古龙侧重的是对人类本身非理性化人格的开掘(如性欲等),在古龙作品中不时充斥着色情与暴力的同时,也时常触到了人类本身的灵魂深处。
或许是金庸对武侠小说(也是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了,所以在其作品中,承载太多深度思考的同时,也丢掉了武侠小说的本身。但是,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韦小宝这一形象却是金庸推翻以前的自己的武器,他与其他任何武侠小说中的“侠”相比,人性化色彩(或说人性中的缺陷)都是空前绝后的。
韦小宝与金庸笔下以前的任何一个“侠”相比,似乎太缺乏厚度与深度。其实,这是金庸借韦小宝来质疑消解“侠”的意义。其师傅陈近南是一代大侠,却落了个悲剧的下场;韦小宝本人却凭着油腔滑调、溜须拍马四处逢源,他的平步青云是对行侠仗义以及建功立业的最大讽刺;但他本身又具备“侠”的最本质、最单纯的特征,即“讲义气”,没有过多考虑,只是最简单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不愿背叛师傅,也不愿出卖朋友。
最后,他仍然走不出失败的结局,只能选择退隐,这一结局又一次否定“侠”在宫廷中的命运。在消解“侠”的同时,金庸似乎又为“侠”指明了真正的出路。于此,金庸再一次超越了古龙,倘若古龙不是英年早逝的话,相信一定会有更精彩的作品出现。
注释:①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香港伟青书店1980 年版
②参见刘若愚《The Chinese Dnight—Errant》(Chicago,1967)第一章;侯健《中国小说比较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83)中《武侠小说论》一文;田毓英《西班牙七十与中国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八章;崔奉源《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第一章
③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转引自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78页)
④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转引自陈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景观》,《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5页)
⑤艾弗洛姆:《人心》中译本第21——22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1版
⑥《庄子渔父》,《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版第208页
⑦金庸:《笑傲江湖后记》
⑧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
⑨何其芳:《文学艺术的春天序》(1964年),作家出版社 1964年版第6页
⑩焦菊隐:《导演的艺术创造》(1951年),《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转引自《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8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