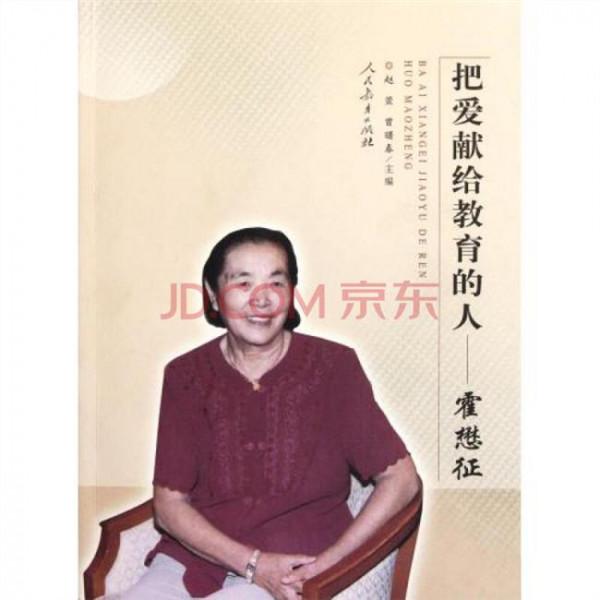柳云龙:我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
和柳云龙对话,你会发觉,这是一个不会妥协的人,他绝对不会顺着记者的“问”去“答”,结果是你“问的初衷”和他“答的结果”完全不在预料之内。
这和他“内心有种叛逆,喜欢主动出击,有控制欲,爱‘叫板’”的个性有关。不被设定,是柳云龙内心很难觉察到的一种叛逆。所以会有《暗算》中,主人公安在天和黄依依不能相伴一生的结局。
“原著中安在天是娶了黄依依,但我一想,我不能正中观众下怀。我一定要让观众揪心,难过。我一定要让他们念念不忘。”柳云龙是个追求完美的人,王子和公主最终不能幸福生活在一起,“这种有缺憾的结局,就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完美”。
《暗算》是今年电视屏幕上的一匹黑马,谁也料不到,一个五六十年代关乎“革命”和“英雄”的故事会引起收视狂潮,甚至,“暗算”这个词也成了今年的时尚语录。主人公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戏中虽有情感因素存在,却是非典型性的爱情,激烈与血腥的打斗场面更是不见踪影。它缺少现在电视剧中的“娱乐元素”,不能供人“消遣”,甚至,看完这部电视剧,你还要反思。
“是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情结”,柳云龙补充道,他不甘心让“革命”和“英雄”这两个词与我们产生年代感,他要让它们生动起来。“就电视剧本身的故事而言,我认为是陌生带给了观众求知的欲望,因为侦听,破译,深入敌人虎穴迎风而战,都是一种全新或久违的视听语言。它牵动了人们对信仰的回归。”
“理想、英雄、使命、责任”之类的词经常会从柳云龙嘴里冒出来,总觉得他三十多岁的年轻面孔和这些话语之间缺少关联性,而且,这是个充满娱乐的时代,这些词的频繁出现显得有些突兀,有些格格不入。柳云龙不否认自己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
“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英雄情结,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结,我其实也是一个没有机会在现实中表达英雄情结的人,更多的还是运用自己的职业,来表达我对英雄的尊敬,和对英雄的一种演绎方式吧。”
“我是个愿意说真话的人,我可以保持沉默,但一旦与记者面对面,我不会粉饰太平,涂脂抹粉,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这样的结果,是记者们觉得我太死板,不圆通,说话太冲,得罪人,他们也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由头,没‘点’,不会‘炒’,总不能老写我怎么刻苦创作吧,那没什么读者愿意看。我就是这么一个无趣的人,没有新闻,更没有秘闻。” 这个山东汉子看着有点倔。
柳云龙说自己一直很怕和媒体打交道,“因为《暗算》是成立影视公司后拍的第一部戏,作为投资人、策划人、导演以及主演,我不光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董事会与职工负责,为其他出品方负责,所以我接受采访多了起来,记者们也夸赞我比以前愿说了,能说了。”
《暗算》之前,很多人对柳云龙没有印象,虽然他在电影《玉观音》、电视剧《公安局长》、《七夜》中都有过分量不轻的表演,但人们对他的印象还是有些模糊。“之所以不被观众和媒体关注,是因为那几年我就没怎么做让他们关注的事。
《暗算》之前的一些戏,因为职业的缘故,我演了,但仅仅是演了而已,还没有遇到过自己首先被打动得一塌糊涂的角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我自己首先还没付出那么多,而我相信付出和获得是成正比的。”
柳云龙1993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那时候话剧舞台留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我又不习惯拿着自己的简历到处找戏拍的尴尬,就辞职了。这可能是我的个性使然,我希望自己能够选择生活,而不是让生活来选择我。”
柳云龙说自己从没怀疑过自己做演员这一职业的正确性与潜能,但那个时候也许是年轻气盛,“站在了屋檐下,还是不想低头,所以就南下广州了” 。柳云龙的声音云淡风清,但言语间却充满霸气。
没多久,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在广东,他做过广告公司,也出过音乐专辑,前者是生存,后者却有些玩票的性质。“做这些的时候,我只是在做,没有不再做演员的想法。打个比方说,我无论如何总是要回家的,不过看时间还早,路上风景也不错,所以就串了串门,绕了一个弯,只是想让自己看一看而已。
但家是早晚要回的。果不其然,两年以后我就又回到了北京。”总感觉他的回归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味道,《暗算》也许只是他抛出的一块“砖”。“从我做导演来讲,《暗算》只是从幼儿园进入小学,之后还会有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所以,路还很长。”
在现场,他一会一个想法地跟执行导演交换意见。“什么叫创作,可以平等沟通才叫创作。”柳云龙搓着手、跺着脚地感叹。
“他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有时像个孩子,特别简单,做事极其认真,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是个劳碌命。”他公司的员工说。
在房间里采访一个多小时后,和柳云龙握别时,感觉他的手很瘦弱,没有他的人看着有力,而且,依旧冰凉。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暗算》里的男主人公太完美了吗……
柳云龙: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我们的社会需要完美,现如今的社会太需要完美了,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碰不到完美,我们也希望我们创作的人物、故事也是残缺的。不对的,不对的,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急迫地需要这种主流的、完美的东西。
《暗算》里的这两代人,安在天,钱之江,这两个男人,完成了我对中国男人的想象,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男人所承载责任的想象。所以在《暗算》的播出过程当中,有很多记者像你一样,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说这是我有意而为之的事儿。
柳云龙:对,我需要,我希望出现这样跟现在社会价值观不同的两个人物。
柳云龙:我不知道成功还是不成功。对我来讲,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我还会给大家惊喜,我有这个自信。当然,文艺作品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但对于我一个创作者来讲,我需要有自信,我必须要自信,我不能游离。
柳云龙:会。但我的这种霸气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
人物周刊:很多人说你有阳刚气,有魅力,你觉得你的魅力在哪?
柳云龙:(笑)以前我以自己的腹肌为荣,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只能靠眼睛了。我觉得现在社会中性的人越来越多,半男不女的人越来越多。其实《暗算》这两个人把我对现在社会的无奈、失落、彷徨的东西,全部都展示出来了。
人物周刊:你无奈?无奈什么呢?
柳云龙:我无奈,我很无奈。我无奈于我们的社会大多的群体、大多的人很茫然地活着,除了金钱,什么都不想。当然,物质的东西是基础,没有物质什么都不要谈,但是难道仅仅有物质就行了吗?除了物质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吗?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柳云龙: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是一个有非常强的使命感的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通过我的职业,把我所想的东西展现出来。从初中时起就愿看类似于王成啊,董存瑞啊这些英雄电影,我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被他们感动得流泪,我说:“将来我要能变成他那多好啊!”
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我情有独钟的年代。在我的概念里,那些年代都是“火红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我的父辈经历过,耳濡目染,看到他们神往的表情,听他们唱苏联歌曲,我感染到了那种激昂、纯洁、向上,以及生机盎然,我坚信曾经有这么些人靠着信仰在坚定地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大众。他们可能生活上贫困,但他们的精神却极为贵族。他们都是海燕,在高傲地飞翔,而不是在陆地行走,我对他们充满敬意与向往。
人物周刊:在演艺界,大家常用的两个词,一个是“出名要趁早”,再一个是“大器晚成”。你呢,是大器晚成吗?你觉得现在“成”了吗?晚吗?
柳云龙:我知道是张爱玲说的这句话(出名要趁早),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她的运气。在我看来,成名是水到渠成,没有先来后到之分,“早”有早的好处,但容易昙花一现;“晚”有晚的气势,却也难免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
我绝对不是大器晚成,第一我还不老,第二我目前也不能就算是“出了名”。我离自己“成”的标准,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走到现在,什么时候是你走得最艰难的时候?
柳云龙:未来。因为人们最恐惧的,是未知的东西。已经走过的人生,既然过来了,那一定不是最难。
人物周刊:你有过消极的时候吗?
柳云龙:我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人为什么要消极呢?那是跟自己过不去。与其消极地在痛苦中挣扎,不如积极地一跳,让自己飞扬起来。
人物周刊:你做人的原则是什么?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在拍戏时,因为很多效果做不到那个年代的感觉,你会经常着急发火,你的脾气性格如何,可以自我评价一下吗?
柳云龙:我认为,人最好自己不要给自己的脾气性格下结论,因为无法下结论,即使是在镜子里,你看到自己的形象也有偏差,何况是看自己心中的自己呢?
拍戏时,我最见不得的就是对工作的不认真,对艺术的不尊重,敷衍了事,得过且过,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发火发急。拍《隐姓埋名》时,一次演员在这边声泪俱下,工作人员却在那边聊天,大笑,还是同期录音,我气得抄起了一块砖头,破口大骂,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事后我戏称自己是“泼妇式战斗机”(美国在二战时的军用飞机)。
人物周刊:你个性和这圈子有冲突?
人物周刊: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柳云龙:我喜欢。我喜欢的不是这个圈子,我喜欢的是这个职业。因为它能完成我对人生,对世界的这种想象。我喜欢这个职业,但是我同时又是一个跟这个圈子离得很远的人。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你不太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生活中你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吗?你现在和刚进入这个圈子相比有变化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柳云龙:我是个话不投机连半句都不愿说的人。生活之中,决定我善不善于表达的因素,是对方而不是我自己,我也有过“千杯少”的时候。
我现在和刚进这个圈子时相比,应该没有太大变化,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样子,不同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脾气收敛了一些,懂得克制了。
最近有人说我耍“大牌儿”,我笑了,因为以前我的“牌儿”更大。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因为一部电影中导演对我的不公,失踪了一个星期;刚毕业,也因为有部戏里伙食实在太差了,我就领着大家维权。比较起来,我此时很“乖”,至少能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