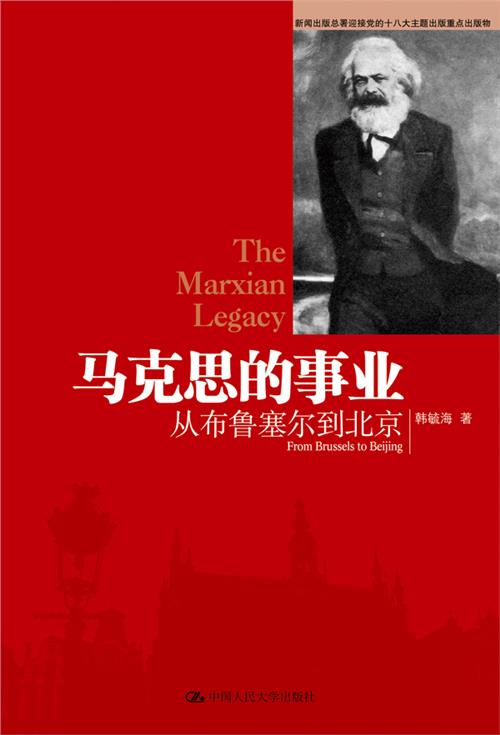汪晖承认什么何种政治 汪晖:承认什么 何种政治?(五)
大约16年前,新年的钟声在天空回荡,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迎接新世纪的降临。他首先想到的是人口流动对21世纪的巨大影响,于是以《文化共生的世纪?》为题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他归纳出人口流动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即国内和国际的商业和休闲旅行;自愿和被迫的移民;由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自“20世纪晚期以来的全新现象”,即其生存不与任何固定地方或国家相联系的跨国人员。
[1]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激发起人们关于“一个文化混同共存的多种多样的世界”的乐观想象:“今天的移民生活在三个世界中:他们自己的世界、移居国的世界,另外还有全球的世界,因为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消费及媒体社会使全球世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
”[2]然而,乐观的调子尚在回荡,巴黎、慕尼黑的枪声一再击破欧洲的宁静。面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及随后的难民危机、伊斯兰国的崛起、土耳其的政变及随之可能到来的政治-宗教变化、多民族国家内由新的动因触发的民族/宗教冲突,人们不禁自问:在一个高度流动的时代,我们是否真的生活在一个文化共生的世纪?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文化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各民族区域形成的基本条件。当代世界的不同之处既不是文化多样性,也不是区域间的流动性,而是两者之间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紧密联系。变迁和流动的速度、密度和规模前所未有。
除了人口的流动之外,金融化、互联网技术等等促成了前所未有的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现象。如今,人口、土地、货币等维持社会稳定的要素全部以空前的态势处于流动状态。大规模社会流动不但可以改变民众的伦理文化取向,也会改变其在审美和其他领域的价值判断,因此,移民以及跨越区域的互联网文化最终可能影响一个社会在伦理、政治、审美等各个方面的自我理解。
在高度流动的关系中,认同政治以不同方式追问自身文化完整性的保存这一问题,以致民族或宗教身份压倒了其他多重身份。
如果“文化多元主义”首先意味着“对所有自称为文化团体的集团都予以公开承认。这样的团体只注重自己关心的事情”,[3]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政治共同体的法律对于移民的要求有没有限制,以便保持其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完整性?在完全自律的整个国家制度都打上伦理烙印的前提下,自决权是否包括一个民族坚持自我认同的权利,更何况是在面对有可能改变其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移民潮的情况下?”[4]
早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围绕新一波移民浪潮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 rgen Habermas)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现代社会能否在某些情况下把保障集体性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二,现代社会是“程序的共和国”,还是应当考虑实质性的观点?[5 ]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按照传统观点,保证平等对待公民所享有的各种尊重与保护公民不会由于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等因素而遭致不平等对待是完全一致的,但当代“承认的政治”提出的是一种新的诉求,即一些民族或社群要求保存其特性的愿望与要求享有某种自治的自主性形式直接关联,按照这一诉求,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对同一社会内其他公民的行为和权利构成约束和限制。
因此,认同政治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的流动关系中,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权利理论是否需要重新修订?[6]我们可以将这一问题更为明确地概括为:究竟应该通过扩展个人权利的多元内涵来解决当代社会的平等问题,还是应该考虑集体性权利——即通过承认的政治,形成多元社会体制?究竟怎样的政治原则和制度安排可以缓解全球化时代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紧张?
实际上,泰勒的问题源自他对魁北克问题的思考,其核心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如何对待在特定区域占据多数的少数民族群体的领土性自治诉求?与此不同,哈贝马斯面对的是冷战结束后的大规模移民潮。因此,前者的“承认的政治”与后者开放移民但同时维持法律程序主义的主张各有侧重,论辩双方的立场源自不同的语境。
就泰勒的“承认的政治”而言,“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即便不是思考的唯一前提,也是基本前提之一;但对哈贝马斯所讨论的欧洲移民问题而言,大规模移民潮对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价值、法律和安全构成了挑战,从而“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才是问题的根本。
哈贝马斯的选择是双重的,即一方面要求国家向移民进一步开放,另一方面要求移民遵循既定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拒绝在同一的公民权利之外承认独特的集体性权利。
在中国,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新疆“7.5”事件,以及在云南、北京和新疆不同地区发生的暴力冲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也在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添加了新的疑虑。由于冲突的爆发点主要集中在民族区域,故而这一问题引发的是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是否需要调整的法律和政策争议。
但是,如果我们不只是将问题集中于族群或宗教,而将移民问题视为一个普遍问题,那么,十多年前即已爆发的有关收容制度和居住制度的大讨论不是已经触及社会流动与身份问题吗?由于内地区域间移民的规模远大于国际移民和少数民族移民,从而有关保持文化习俗等等的讨论居于十分边缘的地位。
但关注少数民族移民的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彝族、藏族、回族、朝鲜族、维吾尔族甚至汉族等各族经营者和打工者的困境其实十分相似,从新疆移居各地的公民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新的矛盾和冲突并不仅仅限于国内,而且也与遍及世界的、新的、形态各异的宗教运动有着复杂的联系。
在很大程度上,内部矛盾的激化是输入性因素刺激的结果。但也正由于此,在国内发生的矛盾常常被全球媒体的报道蒙上一层文明冲突的标记。因此,民族宗教问题涉及区域性、全国性和全球性等三个方面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