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建花鸟画 朱新建用笔墨画"国画"到底 怎么画怎么开心
从个人的角度说,在几十年的生命过程中,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是很少的。 当初喜欢画画,一开始碰到的“老师”(有的只是比自己稍大一些的孩子)大多是“国画”的,于是自己也就“国画”了。时至今日,“改行”是不太可能了,大概就要这么“国画”到底了。
所幸,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几十年泡在里面的“国画”是非常迷人的世界。 传统的文人画本质上说是一个“业余”画种。玩这个游戏的在当时大多是一些文豪、财主、大官,甚至皇帝什么的,一般都生活在社会矛盾、变革的漩涡中心,往往比其他人更多身不由己地随命运的大起大落,所以内心就更加向往安宁、朴素。
他们在笔墨里追求天趣,往往反社会、反财富、反文化。他们往往孤傲、清高、独立特行……但是创造了一个美妙、真诚、朴素、生动的精神世界。
“技术”在这个世界里只是一种面值很小的货币,我希望自己的画是反技术、反文化的。我所希望的只是内心更加的真诚、朴素、生动。祖先创造的那个美妙的精神世界就像今天地球上热带雨林一样已经大大地萎缩了。
我们仍在继续孜孜不倦地用潮流、创新、现代、科学等等各种大功率的“电锯”扫荡她所剩无几的残余。个人太渺小了,无力对抗这样的大扫荡,某个某几个人或者可以做几只苍蝇,或者在身上可以带一些花粉、孢子什么的,或者可以坚持,勉强飞过今天这样的“瓶颈”,为明天肥沃的土地保留一些活体的物种。
假如这样,躺在明天实验室的尸体解剖台上,他们应该骄傲。 “笔”记 我画画一直用的是一枝小号的“古法胎毫”,已经二十来年了,画惯了,反正我画画是“先射箭后画鸟”的那一派,画到哪儿算哪儿,也并在乎还有没有锋,就像一个“剑客”,大概看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那把破剑是跟性命差不多的。
中国人讲笔,第一笔杆要直,所谓“笔直的”,小时候老师教我们挑毛笔的时候,要把笔放在玻璃柜台上滚,咕噜噜很顺地能滚起来的就说明笔杆直。
可我那枝胎毫买的时候就没好意思使劲儿挑,日长月久,水浸烟熏的,它自然弯腰驼背得就更加厉害了,再加上那笔杆用的也不是什么好竹子,还在煤油灯上七死八活地烤过(为了冒充斑竹),所以笔杆会裂,笔毛还会掉下来(古法讲究笔毛是用松香烧化了滴在上面和笔杆粘起来的。
那时候的读书人多文雅,脸白白的,个个长得都跟孙老师那样,可我不是那种型号的,我是吃起猪头肉来没够的那种,粗鲁啊,不好意思)。
为了不让它彻底地骨肉分离(说到骨肉分离,想起来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下放的那个镇上,有一个江湖郎中在街上摆个摊子替人拔牙,来一马大哈,问他,拔得疼不疼。
他说,有药,一点都不疼。就拿膝盖把马大哈的脑袋顶在墙角上,往他嘴里滴了两滴花露水,就使拔鞋钉的那种老虎钳就拔。马大哈疼得如杀猪一样地叫,就不干了:你他妈不说不疼吗?那江湖郎中说话很有道理:放你妈屁,不疼?骨肉分离啊,能不疼吗?此为即时插入公益广告,下面继续)……为了不让它骨肉分离,我就拿中秋节捆月饼盒子的那种小绳子给它捆了个结结实实,再用地摊上买来的一种最新高科技产品,什么几零几的胶水,把笔毛死死地粘起来,估计叫那江湖郎中用拔鞋钉的考虎钳也很难拔下来了。
有一次,我在夫子庙,一条还没来得及拆迁的旧巷里,拿这枝古法胎毫写生。就来几位美女,手里还拎着明晃晃的龙泉宝剑什么的,应是刚刚搞完晨练,在我后面兴趣盎然地看了半天,就开始言论,你看人家老师傅,连枝新毛笔,也就两三块钱吧,都不舍得买,还这么刻苦、用功。
现在画的是不太好,不过人家这么刻苦,以后说不定还能上个老年大学呢。
“墨”记 作为材料讲,我的墨很简单,倒半瓶“一得阁”,放在一个瓷盘里,让它慢慢地变干、变浓,画的时候再用小勺舀一点滚水调一调,否则刚倒出来的新墨太稀,画起来就单薄。以前人也有砚台不洗的,叫宿墨。
黄宾虹、关良等人就爱用宿墨画画。“早年”我不敢用墨,画画大多是单而极细的线,心很想放纵一下,手却老是使不上力,就开始多写字。我迷老颜的《麻姑》和《家庙》,整天写,上了瘾,什么事都不愿意再做,连吃饭睡觉的心思都不太有。
那时候我正单身呢,一个人在北京飘,没人有权力来“硬劲”照顾我。我扛了三麻袋花生,两大箱可乐放在家里,锁了门,拔了电话,拼命地跟《麻姑》、《家庙》、《魏碑选》这些字帖,八大、青藤、齐白石的画册叫板。
饿了,就剥一把花生;渴了,就灌半瓶可乐;困了,就找一盘最无聊的三级片,看不了两分钟,马上就睡死;醒了,就爬起来,也不洗脸、刷牙,连表都懒得看,接着再过瘾……几个月以后,笔底下的力量就见长,笔道开始变粗……就在这段时间,阿城从美国回来,被我拖来玩过一次,我把塞满了床肚底下的一大堆黑漆麻乌、乱七八糟的画和字都翻出来给他看。
这家伙憋半天给了一句评语:“就连古人一块儿算,使这么大劲儿的好像也没有。
”被这个大哥级的朋友表扬了一下,我那份欢喜当然是非同小可,连忙讨好他说:“你挑一张吧。”他翻了一会儿,大概是拿不定主意该拿哪张,就骂起来:“他妈的,不带这么折磨朋友的。”我赶紧给他挑了一张乱七八糟写了好多字的,他挺喜欢,我当然也很高兴。
可我还是不很敢用墨,还是有点怕,怕什么呢?好像是怕水。水少了,墨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意思,像个公鸭嗓子被人掐着脖子唱歌;水多了,又会瘫在纸上,古人管这种瘫在纸上没有力量的墨叫“墨猪”。
咳,“墨猪”!我真想刻一个图章,就用这两个字,跟自己调侃一把。恰恰在这段时间,刘晓纯先生等来组“第三届中国油画联展”的稿,我就又开始疯狂地玩油画,昏天黑地地又画了两个月,把这个展览混过去之后又来画水墨,突然发现不一样了,画“油画”的时候,笔搅在调色油和颜料里,总觉得自己在跟铺马路的沥青打交道。
突然回到宣纸上,就舒服多了,心里想,老子马路油都不怕了,还怕水吗?也许这是所谓第七个烧饼,我开始怎么画怎么开心,墨猪也好,公鸭嗓子也好,都跟我没关系了。
喜得我不停地打电话给各路朋友,告诉他们我现在不怕水了,人家以为我参加了游泳队。跟打麻将的人胡了大牌一样,我更不舍得睡觉了,每天疯过瘾,一天大概也就睡两小时左右。
又过了个把月,突然小便蜡黄、恶心、浑身无力,朋友把我弄到医院一查,我得了很严重的肝炎,我这才知道,过瘾是要付代价的。还好,我竟然又没死,现在又他妈的能胡画画、乱写“诗”了,真他妈的过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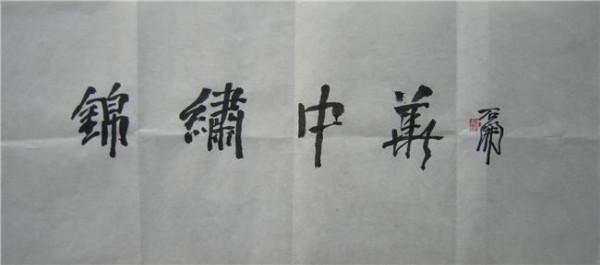




![[邱兴隆简历 朱迅]【朱迅癌症最新近况】朱迅癌症入院手术丈夫放](https://pic.bilezu.com/upload/7/18/7181253deec1bf29beac4537fb49a4f7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