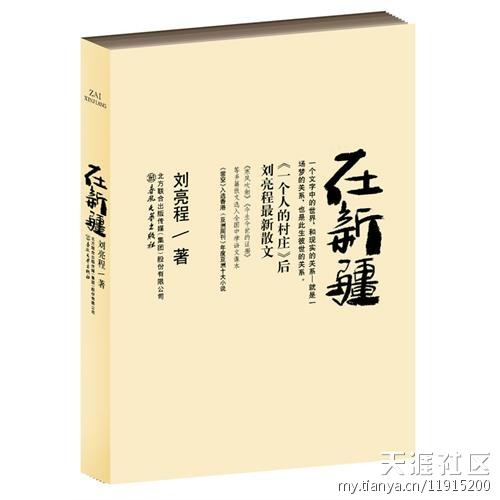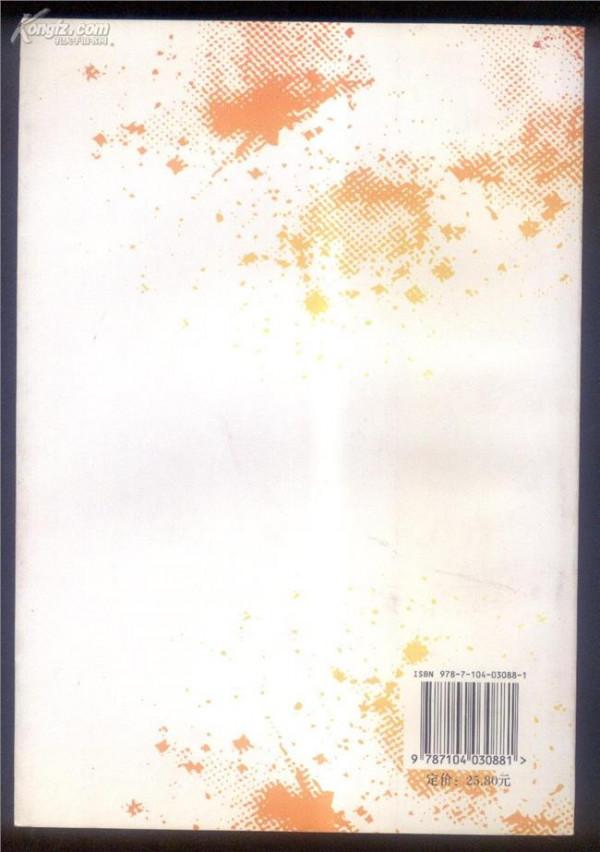我的树刘亮程 刘亮程:我的文字充满了新疆的气息
刘亮程最新的散文集《在新疆》(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依然沿袭了《一个人的村庄》的风格,这位种过地、放过羊的土生土长的新疆作家,笔下的故乡感动着每个读过他文字的人,其多篇散文选入全国中学及大学语文课本。去年,他的小说《凿空》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10年十大小说。从诗歌到散文再到小说,新疆始终在刘亮程的关注和讲述中,他所有的文字都与他所生存过的土地有关。
刘亮程说自己的长相“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和蒙古人”,自己的目光是“一种新疆人的目光,中亚人的目光,也是汉史中时常描述的‘窥中原’的目光”。作为新疆作协副主席的刘亮程,如今正在从事有关新疆文化整理发掘的工作,在与他的对话中,可以感觉到,新疆那片土地的文化、历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液。
记者:您的最新散文结集叫《在新疆》,可以说,新疆对内地的读者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这里有不同的民族和民族文化,新疆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刘亮程:《在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后的散文结集。我以前很少谈新疆。新疆是我的家乡,对我而言,她就像空气一样、像阳光和雨水一样,你怎么去谈它?那种对家乡的情感,远非一个爱可以表达,它更丰富更复杂,百感交集,悲欣交集。
《一个人的村庄》写的是我家乡的小村庄,从文学意义上说,这个小村庄也许更大。从自己童年的小村庄,写到整个新疆,家乡随着年龄在变大、扩张。但再不会大过新疆。当我书写家乡新疆时,我知道她也是其他人的家乡,是许多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共同家乡。当我用汉语书写自己对新疆的情感时,我知道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诸多民族的语言也在表达对同一块土地的感受。这正是新疆的丰富与博大。
记者:很多人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但可能反而忽视了自己生活的家乡,也不关心它的文化存在,为什么您对新疆有这么深厚的感情,这么关注新疆的文化意象?
刘亮程:我在新疆出生长大。写《一个人的村庄》时我没有提及新疆,我认为文学是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但写《在新疆》时,我有了一个新疆人的感觉,新疆给我的东西太多:长相、口音、眼光、走路架势和语言方式,等等。
我在区文联工作那会儿,经常有人推开办公室门,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向我打听某个人或某件事,我大概能听明白,但只能用汉语回答,他们听我说汉语,就笑了,他们把我当成本民族的人了。的确,我长得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人和蒙古人,还有点像回族人。我不知道自己为啥长成这样了,是风吹的,还是太阳晒的,或者是这里的饮食、空气、气味让我变成了这样?这个地方在不知不觉中让我的文字和生命都充满了她的气息。
新疆还给了我一个看中国的视角。是站在西北角上看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我看到的中国,或许比一个内地人眼中的更大更丰富。因为我知道除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有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在泰山庐山之外,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
除了《诗经》、唐宋诗词,我们还有英雄史诗《江格尔》《玛纳斯》、十二木卡姆诗歌等等。这些伟大河山,千古文字,一样在养育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人们常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这不仅仅是到新疆看到了地域上的中国之大,更重要的是这片广袤地域的厚重文化丰富和壮大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觉得非常重要。我理解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该是由中华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共同参与、塑造的“精神家园”,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汇聚成大新疆文化。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不能没有边疆文化精神。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事实上我们对边疆的文化重视还不够。
比如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一直没有收入三大史诗的章节,也没有收入木卡姆诗歌,这是一个缺憾。这几年我们工作室在做江格尔文化,有幸深入了解了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我和团队的同仁,都被这部伟大史诗深深吸引和感动,她就产生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多少年来我们忙着阅读和追捧来自遥远地方的世界文学,却忽视了身边的这部伟大著作。
我们正在改编出版少儿版《江格尔故事》,十万行的《江格尔》史诗中,有数不尽的适合孩子阅读的美妙故事,她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记者:您的书中专门有一章描写古龟兹地区,非常有趣,您当初是因为什么对这个地区感兴趣的?
刘亮程:《在新疆》的第二辑“半路上的库车”和第四辑“月光”都在写龟兹-库车这个地方。我的长篇小说《凿空》也是以龟兹为背景展开的。我从2001年开始关注龟兹-库车地区。起初是受一家出版社委托,写一部有关新疆老城的书,我选择了库车。当时库车人口40万,有4万头毛驴。库车大巴扎在龟兹河床上,河水从一旁的渠道引走,整个宽阔的大河滩成了天然的大巴扎。每当巴扎日,有上万辆驴车聚集在那个大河滩上,非常壮观。
当时我对库车老城的兴趣,就是这里的4万头毛驴,和家家都有的驴车,它们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产业。因为驴需要钉驴掌,驴车上有铁件,所以铁匠铺一年到头铁活不断。驴车需要皮具,养活了一些做驴拥子做套具的皮匠。还有打制驴车的木匠,等等。这个手工业链条就靠这几万头毛驴在维系。
驴和驴车在内地早就不见了,在北疆农村也少见了。其实毛驴早在两千年前的鸠摩罗什时代,就是遍布龟兹的代步工具。驴车也是那个时代就有了。驴车是我们老祖先坐的车,历经几千年依然鲜活地存在着,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知道好多游客去库车,可能是奔着苏巴什故城去的,奔着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佛窟去的。但是,他们一到老城,看到满街的驴车和手工业作坊,都会停下脚步,仿佛一下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都想坐坐驴车,这是我们花多少钱都做不出来的景观,却要费很大劲把它破坏掉。
这太可惜了。两千多年都过去了,我们仅仅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让很多古老的事物从我们身边消失掉,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吧。我们都在讲保护文化,保护文物,驴和驴车就是一种活态文化和文物。驴车文化完全可以申遗。不要等到一种文化成死文化了,进博物馆了,我们才去保护它。我们应该保护活态文化,已经被我们祖先延续了几千年,作为一种生活形态传承下来的文化,更有价值。
记者:您的书里写村庄、旧城、沙漠、佛窟、月亮,写树、牛、马、驴、狗、老鼠,更写了铁匠、放牧人、画师、商人、居民等各式各样的人,甚至有一章专门写了不同的小偷,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是什么触动了您的写作?
刘亮程:我喜欢气息这个词,作家写羊,文字中就要有羊的气息。写草木,就要有草木气息。我写的是在新疆,文字必然弥漫新疆气息。有气息的文字是活的。我崇尚万物有灵。作家得自己有灵,方能跟万物的灵交流。这便是灵气。
我喜欢那些不会改变的旧事物。就像“锄禾日当午”,过去千年了,这首诗歌里的锄头、禾苗、太阳、正午、汗滴、土、辛苦、盘中餐等等,一件都没有消失,原样地保留在诗歌中的大地上。我喜欢慢事物。所谓慢,是我们对待事物或事物对待我们的一种态度:彼此珍惜与挽留。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慢的,仔细的,是停下来细观慢察的。我喜欢那些停下来不动的句子,事物被文字捕捉到。
记者:从诗歌到散文到小说,您创作中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刘亮程:写小说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诗人。诗意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无论散文或小说,我呈现的世界诗意弥漫。那是我愿意写的。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两本您最近喜爱读的书?
刘亮程:我正在读有关古代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所有书籍,从出土文书、史料,到相关书籍。我一直盯着公元1000年那个点在看,那是于阗佛国灭亡的时间,是西域宗教改变的转折点。我不研究历史,是在浩瀚文史中寻找人们曾经生活的细节。
细节就像细胞,可以复活那些过去的生命,可以听到那时候人们的心跳。给死亡的生活一缕气息和温度,这是文学能够做到的。年前重读了《突厥语大词典》,这部书让我看懂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域新疆。还读了《巴布尔回忆录》,这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缔造者巴布尔记录的历史,一个人的活历史,近百万字可以让人津津有味读下去。现在是过去生活的另一种延续。理解历史,也是在理解今天。
记者:可以看出,您对新疆的地方文化研究很深,您怎么看待新疆的大文化格局?
刘亮程:新疆的地理分布是三山夹两盆,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夹塔里木盆地和准葛尔盆地。其大文化格局亦如此,可以概括为三山文化和两盆文化。由南往北,依次为昆仑山文化、天山文化、阿尔泰山文化,以及塔里木盆地文化、准葛尔盆地文化。
昆仑文化是最早的融合型文化,它对今天新疆的多民族文化发展仍有启示意义。阿尔泰山是养育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祖山。两千多年来,内地中央政权一直在跟阿尔泰的游牧民族交往,经过漫长的战争与和平,阿尔泰山及阿尔泰语系的诸多民族都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
阿尔泰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山之一。目前阿勒泰地区的主要民族有哈萨克族、汉族、蒙古族图瓦人等。在新疆的三山文化中,天山文化尤为特殊,现代考古证明,早在丝绸之路之前,就有一条从西亚通往内地的天山道。
也就是天山走廊,它直接连接着河西走廊。这条道路也是后来丝绸之路北部支线的最早雏形。几千年来,天山南北坡承载过很多闻名于世的佛窟佛寺、道观、清真寺。
新疆的两盆文化中,多年来我们对塔里木盆地文化宣传得比较充分,一直把南疆塔里木文化作为新疆的文化代表。那些沉淀在各绿洲板块的古代文化和传承到现在的民俗文化,都使塔里木绿洲文化成为新疆最有特色的文化之一。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等。
天山北坡的准葛尔盆地,是中华农耕文化落地生根发育成熟的地区,这个狭长的绿洲带,起自哈密,从奇台、吉木萨尔、玛纳斯,到沙湾乌苏。目前这一地区主要居住着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农业人口。自汉唐以来,中华农耕文化源源不断进入这一地区,留下大量的农耕遗迹。
在玛纳斯河下游,上世纪50年代曾发现被当地人称为唐朝渠的灌溉遗迹,清代的渠道遗迹就更多了,许多村庄的名字都跟渠道有关,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叫太平渠村,村边的清代渠道太平渠遗迹至今还在,还有皇渠村、惠民渠村,都是农耕历史的见证。
以“三山两盆”划分新疆的文化板块,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现在新疆各地都在发展自己的地方特色文化。但对新疆文化的总体内涵把握,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混合的地区。让各民族的文化、各种形态的文化都有一个公平的、公正的展示自己的平台。在发展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如何体现,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记者:正如您谈到的,新疆地域辽阔,各种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您怎么看待新疆的文化交融状态?
刘亮程:新疆是东西方古代文明的交汇地,这些文明或文化曾经对古代新疆产生过什么影响,给现在新疆留下了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较早到达西域新疆的。自张骞出使西域,随着汉代对西域的统治,中华儒文化进入西域,对西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自汉代唐代,一直到清代新疆建省,以及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源远流长。我们从维吾尔族经典著作《福乐智慧》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印度佛教文化大概在魏晋时期或更早进入西域,克孜尔千佛洞的早期壁画,都是魏晋时期的。佛教文化前后影响新疆一千多年。自10世纪以后,佛教文化逐渐被另一种更加强势的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其间还有萨满教、道教、景教、天教等,都对新疆产生过影响。
中原儒文化是以一种世俗文化进入新疆的。新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隶属中央政权的管辖和受儒文化的影响。儒文化讲和谐、中庸。儒文化一直在西域的各种文化中起着积极的调和作用。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地区,只有儒文化可以充分调和多民族关系。我们今天的边疆文化建设,仍需要从儒文化中汲取智慧。
现在新疆的社会生活,仍然是这些古代文明影响的一个结局。那些古老的文化,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
记者:您一直在从事挖掘、整理新疆地方文化的工作,这是一种什么模式?
刘亮程:我们成立的文化工作室做地方文化的大概模式是,先组织作家学者,把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等整体性挖掘、梳理,也就是做成一本文化书,把一个地方真实的历史文化,还原给当地,让民众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
然后,在挖掘呈现过程中,提炼出有独特价值的文化品牌和理念,做文化塑造。其实这些工作在内地大部分地区早就完成了。新疆好多地方的历史文化及民间故事,基本上还是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民间,没有完整地记录整理过。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对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文化的保护如何实现?
刘亮程:我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发现和命名了一条古老宏大的游牧大道:塔玛牧道。
这是我们在给托里县做地方文化时,由我们工作室作家方如果发现和命名的。塔玛牧道,是指从塔城的塔尔巴哈台山到托里玛依勒山间长达300多公里的游牧转场道路。塔尔巴哈台山是天然的夏牧场,那里冬天雪厚风大,不适合牛羊过冬。所以一到冬天,塔尔巴哈台山的牛羊就要向托里的玛依勒山去转场,玛依勒山区冬天雪小风小,是有名的冬窝子。这样自然的地理状况,成就了一条几千年不变的转场牧道。
我们知道在西方,游牧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早在100年前就进博物馆了。即使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也看不到大规模的转场了。在新疆因为县、乡、村的划分,好多原有的牧场被分割,牧道自然隔绝了。但是在塔城盆地,还存有一条完整的被四个县市共用的转场牧道。
通过牧道所经地岩画和古墓葬推断,塔玛牧道的固定转场历史有3500年之久。塔玛牧道有可能是世界游牧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每到春秋转场季节,可以看到连绵不绝牛羊群,走在这条千年大牧道上,一条挨一条的深深羊道,绵延300多公里,每个转场季节有150万头牲畜走过这条牧道。这是游牧文明最后的奇观了。这种景观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了。
农耕民族是居国,筑城修墙。长城是农耕文明最大的文物遗存。长城的作用就是一个国家的院墙,用以护卫城邦家园。那么,作为和农耕文明历史一样悠久的游牧文明,它的文化遗存是什么?游牧民族是行国,在大地上游牧,不筑城,毡房驮在马背上,四季转场,随水草而居。游牧文明的文化遗存便是牧道。游牧是其生产生活方式,牧道是其最重要的文化遗存。
塔玛牧道就是这样一条保存完整的游牧大道,那些羊肠小道,有些地方有半米多深,有些地方甚至有一米深。一条挨一条,密密麻麻,每一条羊道都有3500多年的历史。这么巨大的一个文物,扔在草原上、荒山中,我们多少年对它视而不见,不把它当文物。我们对塔玛牧道的挖掘和命名,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第一次把羊道当文物对待。
随着各地牧民定居政策的实施,游牧作为牧民的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迟早会从大地上消失。但是,游牧作为一种文化,需要我们去保护。尤其像塔玛牧道这样一条承载着数千年游牧文化,现在依然在使用的古老牧道,我们没理由让它消失。塔玛牧道的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记者:这本散文集以后,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
刘亮程:我正在写一个有关新疆公元10世纪前后历史题材的故事,那是新疆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宗教转换时期。我们只有理解历史,才能理解今天。
文学艺术是心灵沟通术。优秀的文学不会站在某个民族立场上言说,而是站在人的立场说话。文学能让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们,在一滴水、一棵草、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在对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在无需翻译的花香鸟语中,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这是我所有的文字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