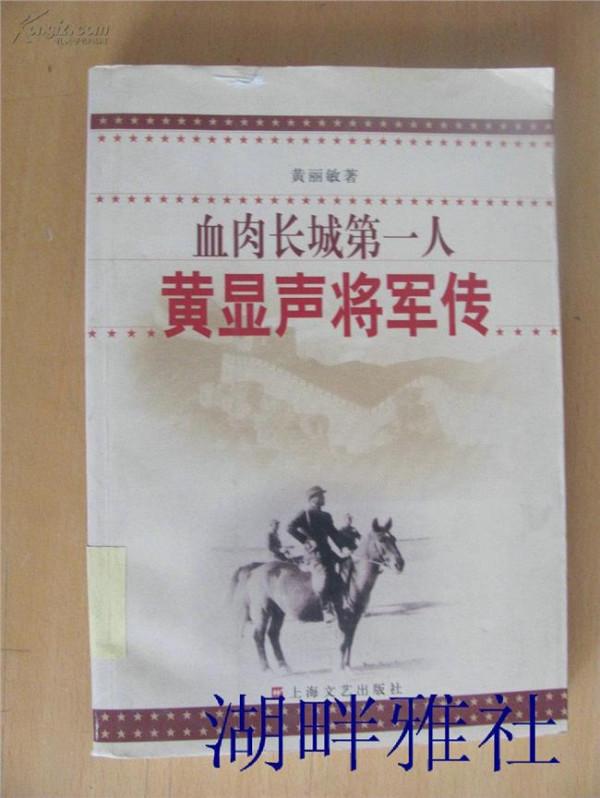血肉长城第一人(黄显声将军传)
引言 2001年的4月下旬,我从丁弘先生那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人性的诗魂—拜会黄彤光老人》。这篇文章介绍黄彤光老人“是当年白公馆、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并提到黄彤光老人和黄显声将军——张学良将军的挚友和副官、国民党第53军副军长,也是一位中共特别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这一特定条件下建立的恋爱关系等情况。
丁弘先生告诉我,黄彤光现年八十六岁,身体仍很健康,他说:“彤光老人是你的邻居呀,她还经常到你家门口的富贵园菜场来买菜呢。
”一句话,使我感到应该去看看这位老人。 六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学生。《红岩》这本书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凡在“白公馆”“渣滓洞”“息烽集中营”这些魔窟里关押过的人或与之有关联的人,即使不在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折磨、杀害而死,一些能活着的,只因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复杂,也难免在“文革”中再遭磨难;即使逃过了“文革”这一关,所剩无几的幸存者,也因大自然的法则在衰老中渐渐离去。
一位经历了如此大难还健在的老人,简直就是一种奇迹,何况还有“邻居”这一种缘,于是,我对丁弘先生提出,要见这位老人。
很快地,丁弘先生告诉我:“黄彤光很欢迎你去,去前给她通个电话。”几天后,我安排时间去拜访黄彤光,老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响亮而有力,中气很足,她说:“我们这里的门牌乱,你不好找,我到门口来接你。
”语气挺硬,不容我推辞。 她下楼来接我,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立刻就在心中肯定说,这就是她,我不由自主地唤了一声:“你是黄彤光妈妈吧?”其实我才发出第一个音节,她便回过头来,立即答应着:“是啊,是啊。
”一脸诚恳地拉了拉我的手,引我向她家走去。 她住的这幢楼,处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心地区的十字街口,是南通城里最早盖起来的住宅楼之一,没有厨房,仅有一个抽水马桶。
南北两个房间,已显陈旧、简陋的家具,布置得有些紧紧巴巴,却给人一种实在、简洁和明了的感觉。 从年龄和经历看,我们是隔代人,却一见如故,没有什么客套之词,谈得无拘无束。
谈她的经历,谈“文革”,谈我们共同认识的丁弘先生,谈小萝卜头。我知道,世界上确有这样一种交流和沟通,不因相识的时间长短,也不因年龄的差距、男女性别的局限,更不因所拥有的财产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甚至是“死去”和“活着”的制约,那是一种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超越了人世间一切物质条件的限制,成为人类最独特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是极力想要享受它的人之一,但愿这不是一种非分之想。
分别的时候,黄彤光老人借给我一本小萝卜头的书。 为了黄彤光老人的盛情,我决定重新再翻一翻早已熟悉的小萝卜头的故事。出乎意料的是,相隔三十多年以后重看这本书,我泪流不止。我在“文革”中挨整被“分配”到远离亲人的青海高原一个生命禁区时,并没有流过泪,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几次面对过痛苦的磨难、死亡的威胁,对于人生的痛苦和残酷,早有思想准备的我,却在看一本写小孩子的书时,如此动感情,难道是人生到了过半的年纪,反而变得脆弱不堪了吗? 我向黄彤光老人还书时,黄彤光老人将另一本有宋振镛先生印章的小萝卜头的书送给我,交谈中,黄彤光老人谈到了张露萍,她是老人在息烽集中营的难友,1945年7月 14日被国民党 反动派杀害,牺牲得很壮烈。
老人着重谈到了她的英勇、她的不畏强暴、她的多才多艺、她的热情和美丽以及她壮烈牺牲以后却一直背着叛徒的黑锅,使她的亲人也遭到连累……老人说:这个张露萍应该有人写一写,她的事迹和品德毫不逊色于《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同志呢。
当时我没有接过老人的这一话题。临别时,老人又借给我一本关于张露萍身世的书,我不好推却,想用一天的时间来读一下也好,看看这个能与江姐原型相比的女性是什么样子。
书中多是张露萍烈士的亲人与朋友们回忆她的短文,也有一些有关单位关于她的身世之谜的调查报告。文章只记述了事实,没有创作和虚构的成分。这本书,我看了整整一天,晚上,我的先生走进家门时,见到我红肿的双眼有核桃大,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弄清原因后说:“退休了,要清心养性才好。看本书就哭成这样,是何苦呢。” 谁知自讨苦吃的事还在后头呢。与黄彤光老人第三次接触时,老人就郑重地提出:我有个心愿,就是想把那一段的经历写一写,但年岁不饶人,我是力不从心了。
我看了你写的书,觉得你能理解那些事。我想请你写一写息烽集中营,写一写张露萍、黄显声他们……不知你接受不接受?在这之前,我已经获悉,这十多年里,曾有不少人来采访黄彤光老人,有的对黄彤光与黄显声将军那段狱中恋情特感兴趣;有的认为黄显声将军曾在抗日、国共合作、西安事变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应该让人民记得他;有人试着搞一个有关黄显声的电视剧本、文学传记,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搞成,其中,有的是黄彤光老人不愿意接受采访。
她说:“有的人,一交谈,没劲,就不想再谈了。”我敢不敢接受呢?未及细想,我点了点头,说:“我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