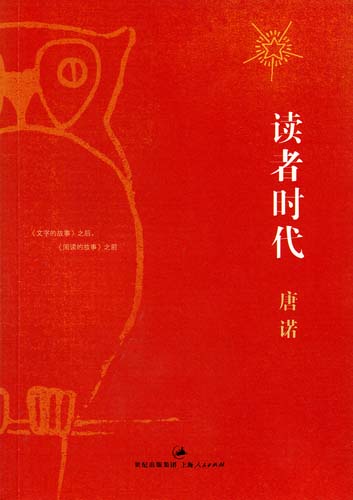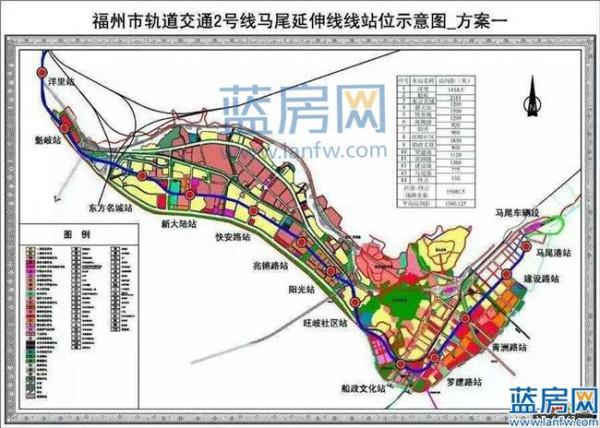朱天心文轩 朱天心&唐诺专访:文学早已不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
晚饭时,朱天心指指手中吃掉一半的甜品,轻唤一声:“谢材俊,杨枝甘露。”对方摆摆手:“我不用,还没到吃甜食的时间,抱歉抱歉。”
小小的场景几近典型地展露出夫妇两人的特点与习惯。漫于纸面的豪情之外,现实是一襟柔情晚照。
“小说书写者”朱天心——他们惯常拣选这个字眼,恐称“小说家”太过狂妄——生活里永远这般语气温婉,低眉慈目。52岁的她看起来仍像中学生,有时带着与其在台湾文学界的声名不相符的怯生生,让人难以想象她作品里面的执拗和火气究竟何来。
“专业读者”唐诺(原名谢材俊,笔名源自美国“梅森探案系列”小说男主角“赖唐诺”)则总习惯以“抱歉”作为一段话的句点。在近期京沪四场讲座里,常有读者向他提出“伪”问题,他细细剖析开来,告诉你为什么问题为伪,为什么事情不是非A即B那么简单。然后,“我很清楚我并没有解决你的困惑。抱歉抱歉。”
他们在上海的第一场讲座定于4月21日,赶上全国哀悼日。读者们从早到晚打了无数电话来,担心讲座会因当天娱乐文化活动全被叫停而取消——毕竟,歌手光良仅仅是在这天给爱犬洗了个澡,就遭到爱国又暴怒的网友们声讨——唐诺宽慰大家道:“放心,我们举行的是哀伤的文化活动。”
说哀伤,倒也不全是玩笑。次日复旦的讲座中,唐诺提及他日复一日写作的咖啡馆里,总有一个妈妈在批评孩子学习为什么那么差,总有一群骗子在讨论股票和楼市,但再也听不到人们讨论文学。“你越来越清楚,文学早已不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
“今天在台湾,如果你谈文学,很难超过25个人到现场,即使来的是非常好的文学作者。但是只要挂一个头衔,比如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某公司的副总来谈投资理财,一定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话到这里,唐诺一笑,“可我不是在哀号,我只是陈述事实。”
在大部分人那里,文学和生活已毫不相干。但对唐诺朱天心而言,很难分出二者的界限。
他们身边全是书写者: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是军中作家,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来台;母亲刘慕沙是台湾著名日语文学翻译家;姐姐朱天文是著名小说家,电影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妹妹朱天衣亦曾写作。朱天心自己十六岁便在报纸上连载小说《长干行》,十八岁创作长篇自传《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至今重版十多次。
“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他们的老友、作家阿城曾为朱天心的作品《古都》作序说。
唐诺天心是高中时期认识的。彼时唐诺编校刊,常去约作家朱西宁的稿子,慢慢与同龄的天心熟识。十年后,应读者的强烈要求,两人结了婚。
“人们总在想象我跟这么一个十几岁就名满天下的人——那时候所谓天下就是指台湾——结婚该怎么办,觉得我一定是在酗酒,然后回家捶桌子:‘我都没有自我!’”唐诺笑笑,“你们真的想太多了。”
日常生活里,他们每周七天无休,在同一家或者分别两家咖啡馆里写作,从上午九、十点钟到下午两点。这些年里,单他们眼睁睁看着死亡的咖啡馆便达五家之多。
唐诺总是天心作品的第一读者,二十多年来,他负责誊写天心的作品手稿。他又向来要求严厉,偶尔评论天心作品时,好友、小说家骆以军都会忍不住出来打圆场:“没到那样啦。”
“我们很少谈小说真正处理的题材,我不会进入她的工作坊。不是因为朱天心不相信我,而是我担心她有时候会相信我,那会弄乱掉。我希望她保持自己的思维,书写永远是孤独的。”
与姐姐天文的迥异书写,某种程度上可以给这份孤独做个注脚。她们从小到大从未分离超过一个月,成长于同样的环境,认识同样的朋友,甚至读的书都是差不多的。两人文学风格却截然相反。朱天文淡泊超然,仿佛世界喧嚣都无法进入自己的沁凉世界。朱天心用阿城的评价则是:“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一种强悍的敏感。敏感并非是阴柔的,所以朱天心的强悍类似玉石。”
从八十年代《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开始,朱天心由青春小说转向对弱势族群的深切关注,此后一直关切公众事务,因为“政府的好坏是一时的,建设公民社会才是长久的。”
朱天心专访——纯文学的恐龙在这里
我关注的东西越多,可以写的越少
问:你会参加社民党,参与倒扁活动,关注现实议题,这种与现实很紧密的状态会不会与写作需要的状态冲突?
朱天心:在早期我比较感觉不到,甚至觉得这是互为表里的。你看到现实问题严峻,很想做点实际的行动。但写作是一个很缓慢的事情,有它自己的时间表,有时候需要二三十年的沉淀。真是急死人了。所以你会找寻一些写作之外的社会实践,不管最后结果是否尽如人意,多少你有做事。这也是为了保护我的写作,我好怕我心急之下会把自己唯一会的事情变成工具,比如明天要游行了,我今天赶快写一个工运小说……
可是最近参与社会事务有了新的感受。以前我会觉得要向强者——不管是社会主流,还是拥有权力的人——说不,是很困难的事,需要很多勇气、对策。这三五年,我觉得向弱者说不是更难的事情。但只有你两者都能做到,在文学上才有全然的自由。
这种触动来自我的实践体会,也有我看到的文学经验。比如陈映真,很左翼的作家,像大陆三十年代的作家。他对笔下人物充满同情,他们已经这么弱势了,会忍不住把他们都……
问:美化?
朱天心:甚至神化。也许你把这看做社会工作,替他们发声,可是在文学上,任何神化都会伤害到你的文学性。我在社会实践中会感觉到,有些弱者,可怜之处必有可恨之处,你要完全地写出一个生动的人的时候,无法只选择他可怜的或者好的部分写,必然也会写出他人性里的缺点,甚至卑劣之处。可是又怎么忍心呢?你要替他说话都来不及,怎么会在说话的同时又捅他一刀?所以这三五年我给自己一个功课,要学会向弱者说不。
去年我们有个陈映真创作50周年研讨会,大家都在歌颂,只有我一个人的题目是“逃离陈映真”,别人都很错愕。作为一个文学书写者,我对他的敬仰就不必说了,但是站在文学本位的话,我会觉得要是陈映真有一天也敢对他的弱者说不,他的文学成就一定会更高。
当然我这个说法得不到响应,大家说陈映真哪里是要文学成就,他是不得已。他是想做列宁、想做毛泽东不成,所以只好写小说,他才没有对自己的小说这么在意。可我自己还是把文学放在最高位,其他次之,我的价值序列是这个样子。
问:这三五年里发生了什么让你有如此感触?
朱天心:我的好多朋友在台湾做的都是边缘又边缘、弱势又弱势的社会实践。比如台湾有大量外籍劳工。他们在法律、社会福利方面都很欠缺。因为他们不是台湾籍,没有选票。台湾是很现实的社会,虽然知道他们的处境,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愿意帮他们说任何话,他没有投票权嘛。
外籍配偶的状况也是一塌糊涂。我看着他们已经做到底了,能动用的所有资源都动用了,自己也很急迫想出一份力。我可能是里头少数能写的人,也想帮他们写,因为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你去帮忙游行也就是多一个人头,媒体能登都还罢了,大部分都不登。
你的力量是你的笔,不是多一个人。但是一下笔,你又发现没法继续。我接触的人越多,会使得我可以写的东西越少。我在文学上已经快要到一个致命的危机,可以写的变得好少好少啊。
问:那还会那么投身这些政治议题吗?会不会因此要站远一点?
朱天心:我很羡慕那种方式,可以一了百了。但我知道自己心很热,无法真正隔离。我现在其实光是做动物保护就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对于外籍劳工之类的活动只能做到互相声援支持,有重要的事情要开记者会,或者要上街头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
现在这个结越打越死,好像你在小说里面越不能帮忙什么,就只好在实践里头多做一点什么帮助他们。可是做得越多,能写的越少,这个结我也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
素朴的爱国是蛮可爱的,可是这样子好吗?
问:你曾经提到“现实跑得比你设想的还快,眼前的荒谬比你想的还要恶意,很难处理这层时间的差距。”
朱天心:我一直有一个还没开始的长篇题材,想用列传的形式把台湾的一代人写出来。我心里有二三十个名单,绝大部分是政治领域,比如陈水扁。这么多人崇拜他,没道理,你本来很想把他们从神坛上拉下来,想写原来他们过往是怎样的人。可是你还没准备开笔,他已经是全国的过街老鼠,不用你讲,有人比你还讨厌,比你还恨。你的动力本来是告诉人家他不是那么好,但现在好像倒过来你在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这个荒谬感就在这里。
台湾这么更迭的政治状况,还不待你把真相还原出来,他们自己都已经说明了。我曾经很敬重的一位民进党人士张俊宏,在牢里写东西的人,他今年初在台湾一个县选立法委,只有两千票,都是亲友票。人家都已经自动弃绝他了。那又何需你去讲他?这些都是我面临准备了这么久的大题材的一个困境。
后来唐诺有提醒我说,你要描写一个时代面貌,也可以不要这么政治。倒不是说安全之类的考虑,而是这些政治人太经不起了,他们本身可能就没有多了不起的思想和学问做支持,是纸片一样的人,寄托不了很多。不如把这些人物改成你更熟悉的文化界的人,很多人在台湾、在大陆两岸都在神坛上,你不觉得把他们揪下来更有趣吗?尽管开一个大车要转向不是那么容易,可是这个提醒确实对我有帮助。
问:你为什么选政治人物作为反映时代面貌的切入点?
朱天心:我们这些1949年跟父亲到台湾“外省人”,从小受的是忠党爱国的教育,可是到了二三十岁,碰到大的政治变动,当场变成一场笑话,甚至是污点。在前十年,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刚开始主政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外省人,会时时被问到说:万一有一天两岸打仗,你会选哪一边?他不用等你回答,就认为你一定会倒向对方,一定会通敌的。
你的忠诚度会因为你父母的出生地而被彻底质疑,所以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理解和关心政治的问题,它会来理你的。它伸手向你的时候,你会有你的困惑、不平、愤怒,所以很难免想要把政治当成一个重心。
另外,很多人对我而言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年轻时长期有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从没有占过任何的身份的便宜,却被本省人那么痛恨?而且当时还打着民主的旗号,民主怎么会是这样激烈残暴的方式,民主不是应该更宽容、更多元吗,怎么会是“外省人滚回去”这样的排他?为了解决这个困惑,我找了很多党外杂志、禁书去看。
看的时候知道,原来台湾人也有很多伤心事,他们的生命史、家族史充满各种各样的苦痛,以前被日本人、后来被外省人压制和剥夺。
好比规定说国语的时候,很多说了一辈子台语或者日语的人就像失语一样,六七十岁的人也没办法重新学国语,开电视也看不懂,听广播也听不懂,他对国民党怎么会感激呢?痛恨大概是最正常的。虽然我不一定能接受,但我可以理解他们了。在大量阅读的时候,我补修了很多台湾学分。那个时代勇敢地写这些文章的人,对我都有这样解惑的意义在。
问:你小时候在眷村的经历,对当时被误解的愤怒,是不是最初的写作动力之一?
朱天心:当初也许没这么自觉,可是现在看回去,确实如此。
外省人有很多种,眷村基本是外省人的底层,是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才会有的。国民党一再在喊反攻大陆,直到韩战起来,国际格局变化,知道肯定回不去了。这时候要为这200万大军找个容身之处,才盖了大量眷村。眷村在城市的市郊边缘,是台湾人都不要住的地方、不要种的田,非常孤立,而且可能在这里住一辈子。
你要是运气好认识本省的朋友,或者运气更好结婚的对象是本省人,可以知道本省人的生活和想法。可是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眷村,社会的变动他永远没法了解,一直活在假想的中国大陆里头。
这些人生活状况很悲惨。比如最初是不准许军队的人在当地结婚的,因为随时准备回去,结婚就会有牵扯。韩战之后允许结婚,老兵们年纪都大了,那一点点微薄的薪水只能娶到穷人、残疾或者山里的原住民、东南亚新娘。穷人跟穷人结合的结果通常是永世不得翻身,甚至小孩都有可能是残障的。你可能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外省老兵样子,在眷村含饴弄孙,好有福的样子,其实才是带他的儿子。
可是这些人在台湾剧烈变动的时候被卷入,被看做是国民党的帮凶,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被认定是国民党的铁票,每年不管任何选举国民党推再烂的人出来,在台湾社会的理解里,眷村一定会选你的票,你的票箱就不用开了,一村三百人,打开之后三百票肯定都是国民党的。但我看到的情形不是这样子,他们这么悲惨,哪里获得利益?我会为他们不平,我觉得自己还有笔,被误解还有说话的余地,可他们就没办法,所以我会写《想我眷村的兄弟》。
问:这时开始你的风格变了。此前还是青春欢笑题材的,比如《击壌歌》,现在拿出来再版,大家重新看到当时高中女生对国民党领袖的崇拜,会觉得政治不正确吗?
朱天心:去年我在香港书展,马家辉直接点名问,你怎么看待你过往对国家民族的这种用感情的方式?我丝毫不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觉得这是个可耻的过去。“外省人第二代”是跟着父辈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你的命运与他绑在一起。
你们想象的敌人、对历史的记忆、使用的语言都是相仿的,将来能不能回大陆去也是看蒋介石,很自然对他是对待亲人、父兄一样。这对民主来讲当然是很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能对一个权力拥有者用感情呢?你用感情和信赖不是等于交一张空白支票给他吗?予取予求,随便任他打任他关?可是这确实是在历史情境下曾经真实的一个阶段。
所以到后来会很感慨,在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的时候,你会看到,唉,悲剧又重演了。你会看到大部分的台湾人会只因为这两位跟他们说同样的方言,一样的历史记忆,一样的价值观,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人。以前说外省人跟蒋介石如何,毕竟是在一个没有人懂什么是民主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大家都认为是民主的时代,结果你还是重蹈覆辙,你还是一样用信赖对待一个权力者。
外省人眼睁睁看到悲剧发生又无能为力,因为他在这十年是失去话语权的状态,你要是说你们要想想我们以前走过的路,对方就会说,哎,你们的人当统治者的时候就什么都对,换我们了你们就不高兴啊。
或者,外省人已经爽了五十年,我们本省人爽个两年有什么关系?你对民主的这番体会和启蒙变得没意义。《击壌歌》也许这时是一个负面教材,固然素朴的爱国是蛮可爱的,可是这样子好吗?
现在眷村像是被打死的蟑螂,可以做做标本了
问:外省人失语的状态,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
朱天心:文学界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有研究生念城市大学——成大一直本土色彩很强,第一个有台文所的——硕士论文本来要研究我,但是指导教师直接告诉她:“这种外省作家你去研究她干什么啦?研究了也不会过。”所以在那十年,很多中文系里,任何教授退休或者有意外情况有空缺,都是宁缺不补的,但是台文系,只要申请就能开设。
现在这部分在马英九上台之后很自然地衰败了。不是说马英九的作为怎么样,他不会在省籍问题上以暴制暴,而是说陈水扁的神话结束,大家也甘心了。
外省人也做过,本省人也做过,就是这样子啊,有一点都扯平了,好像大家又回到起跑点,比较心平气和。在现实中,本来台文所本来就没那么多东西可研究,所以很自然悄悄转了方向。
问:外省人的地位变化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朱天心:我觉得这二三十年来,成绩比较好的是外省作家。理由一点都不奇怪,以省籍看,本省人如此政治正确,处在一个这么舒服的位置,作为个人可能很幸福,可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没有任何动能了。外省人的处境比较艰难,讲的话因为不容易被人听到,就更得琢磨,要不就把声音放得很大,要不就把技巧变得高超,本事被迫锻炼得比较好。
我比较推崇的,现在还在写的作家里面,天文,内举不避亲,骆以军、张大春,这几个都是外省作家。舞鹤是本省人,何以东西这么好,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从来不占身份的便宜。他出身政治正确得不得了,是台湾最有历史的台南在地人,但他从来不用这些,在有机会发言声援的时候,是完全跨越省籍的。可能也是这个关系吧,他的作品可以跨过刚才说的宿命。
问:对于眷村的历史,你觉得在文学表现上有很好的把这段描摹出来吗?影视方面,近期如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话剧《宝岛一村》,在两岸都火得很。
朱天心:眷村题材曾经很贫瘠,这有它的历史背景。眷村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台湾人或者民进党妖魔化,以至于很多人会装作自己不是外省人。家长会跟孩子讲,在学校老师问你是不是外省人千万不要说。我觉得当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讲家族故事的时候,这个族裔已经形同为绝种。
陈水扁下台,大家又重新回到起跑点的时候,眷村影响没那么大了。这时好像蟑螂苍蝇已经被打死,不会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来研究一下,把它做做标本。我不晓得这个态度会不会太轻佻,但确实感觉如此。在表现方式上,永远是比较次文化的东西容易传播,所以影视很快出来。
有些严肃的眷村人对这个比较反感,觉得他们太消费了,太强调眷村有趣的那一面,好像这十年里艰难的、被羞辱的、严肃那一面都不存在。可我自己觉得还好,原来是一个荒漠,总要先有各种生机出现,最后了不起的东西才会出来。
问: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也是追溯外省人的个人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是否会有文学意义以外的反响?
朱天心:这倒没有。唐诺说我和大春对于外省的记忆是采取不同的政策。大春是索性颠覆它,讪笑它,甚至是,我干它。台湾在地人打造国族历史或神话时,大春的策略是玉石俱焚,要拆穿你,我先自我拆穿。唐诺认为我是,“我记得,我看到,我记下。
”当然我这样会惹来非议,因为讨厌嘛,大家都在欢呼,台湾民主化了,多元包容了,你每次都出来扮演乌鸦呱呱呱,很扫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台湾社会或是文学领域就是扮演这个嚷着皇帝没穿新衣的小孩,老是要拆穿别人好事。大春的策略不是这样,所以不会变成这么清楚的标靶。
问:你的选择真的要自己足够坚定才可以。
朱天心:不然会觉得好像会退无失所。像我家那些猫一样,三脚的、两脚的、身体病歪歪的,你都不要它们谁还会要它们?我会觉得,我不说就不会有人说,所以我只好说。
求仁得仁吧,你要选择另外一条路,做一个普通市民,也许会好过很多。但作为创作者,那样就把自己的爪牙拔掉了。这选择也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你要了这个,你就得承担你可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很不习惯去叫苦或者抱怨,因为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去逼你,那有什么好抱怨的?抱怨自己吧。
飞到无何有之乡的风筝,与地上的人有什么关系?
问:作为小说书写者,你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是怎样的?
朱天心:每个阶段大概不同。二三十岁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擦得亮亮的,一点都不折射,不是哈哈镜,不是凹凸镜,真实客观把现实反映出来,就是无限大一个功德了。
再到某个阶段,会觉得你不要装了,你毕竟不是一个镜子,你是一个生命,有感情有想法有个性,有自己对现实的关心。有的人可能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但是我不行。现实对你不断干扰,你也不能不理它。所以我在四十左右,觉得就算自己是一个哈哈镜凹凸镜,那也称职地表现它吧。只是差别在于,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执拗和偏见发声出来,而且可以说服别人。
等到五十的年纪,我给自己的要求是,除了能说服别人,这个过程还应该是赏心悦目的,是好的文学作品,有好的艺术形式。不晓得到了六十七十之后,会不会我连装都不想装了,就想做个传教士。觉得生命有限,秒针在嗒嗒响,有很多想说的话,但是怕时间不多了。
有些了不起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前面的小说成就已经这样大,可是到最后——尽管他已经很长寿——还是觉得时间不多,赶快要把自己最后相信的东西说出来,不假装不虚构。我也不晓得自己有一天会不会这样。
问:你觉得纯文学要承担一定的功用吗?比如对现实问题的反映甚至改变。
朱天心:我从来不把所处的现实看成一个责任,不是说你有义务回应你的现实,而是它是优势和特权。我们的父祖辈也许好想知道到我的孙女那一辈在想什么,我们未来几代的人也许会奇怪台湾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整个岛感染了瘟疫或者热病,怎么会所有的人好像没有脑子的做同样一件事。
我们真的好幸运,正好处在此时此刻。这应该是一个优势,你放着这个别人想破头想知道的此情此际不看,自己生造一个世界出来,我觉得好可惜。飞得再高的风筝不打一个钉在地上,不晓得有什么意义。幻想要与现实要有一个张力,不然它飞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跟我们地上的人有什么关联呢?
当然我也可以了解其他作家的不同想法和要求。好比天文,她对现实的热度就跟我不同,她是习惯在旁边冷眼看的人,所以她比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像我这样的心急之人,恨不得说的话可以对现实有一丁点的波动。其实就像台湾一句俚语“狗吠火车”,狗对着火车大叫,但火车还是轰轰然驶过,这是非常徒劳的。可是我就永远不信因为你的写作不会有一点的影响,这也是支撑我在写的一个动力。
问:抱有这样的期望,会不会很多时候都很失望呢?
朱天心:会。可是你会退守到最后。我每次爱举纳粹时期那个神甫的话做例子:“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我最后给自己的一个最底线,我最起码发声了。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万一台湾真的走到万劫不复的时候,我最起码可以对自己交待。我不要有一丝丝懊悔,那时候要是我说了什么,可能现在不至于……
问:有没有人评论你像鲁迅?
朱天心:我好希望哦!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很多小说,包括去年我在香港书展的讲座题目就用了他的“呐喊”。很多内地来的媒体觉得很诧异……我一直不晓得鲁迅在大陆是一个什么状况,台湾到现在还是只有文学系的人会读个一两篇,完全没有人谈。我自己是喜欢的,包括他的铁屋子的譬喻,现在对我还是一个时时的提醒,或是说明自己的很好的例子。王德威有一次写东西说我很像鲁迅,他讲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说怎么能这么讲,其实偷偷好高兴。
这几年台湾好像做了一个梦
问:唐诺在讲座里说,“在这几年台湾好像做了一个梦。不知道你做的事情对谁有意义,好像没有人对你感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说,大陆对于我们来说变得非常重要,原来你做什么还是有人在乎的。”你认为是如此吗?
朱天心:是这样。我也不晓得这是不是全球的现象。本来大家觉得文学的主力读者,起码在台湾长期以来,是高中和大学生,他们刚进社会,阅读习惯还在。可现在这群人是不看东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关系,这代人更在意横向的讯息,同侪、朋友、社群之间关心的话题,你即使不感兴趣也要感兴趣,不然你就插不上嘴。
比如大家都在网上讲陈冠希,你就得多少知道一点,不然无从理解你的同代。所以你后来一步一步变得都很相仿,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里想同样的事消费同样的东西。
他们好像觉得上代人跟我没关系。我们以前喜欢一个人的文学,不会在意这个作者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还是已经死了半世纪。可现在年轻一代很在意这个,我22岁,那23岁的作家都嫌老,要看就看22岁以下的人写的,之前的人没有必要去了解。这好像一个核爆的场面,唰地一下方圆几百公里全部夷为同样一种东西。我觉得台湾这个特质非常非常明显。
在大陆好像还不是这样。大陆现在很像三十年前的台湾,读者不是光看热闹,他会带着问题来。你会觉得你对人家是有意义的。几次比较之后,我们都觉得,台湾完蛋了,台湾过往某些走在前面的优势已经吃老本吃光了。
问:但大家总感到还是台湾的文化氛围比较好,大陆是让人失望的状况。
朱天心:台湾也许在生产创作那一面目前还ok,可是读者这一侧萎缩很厉害。也会有人找你签名,可是那个签名旁边怎么会是林志玲或者蔡康永?那就很尴尬。
台湾有一个九歌出版社年度文学选,每年选一篇小说做年度奖。去年我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获了奖,有个公视记者访问我——公视是公立电视台,不用商业竞逐,一般比其他商业电视台素质好很多——问的第一句话是:“像你这样一个新人,第一本书就得奖,你会不会很兴奋?有什么感受?”我当时连生气或者质问的心情都没有。天哪,我们公视跑艺文的记者是这样的素质,真的再次被震惊。
问:意识到这种状况,会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会因此觉得写作没有意义,或者因为这样,需要去关注年轻人关注的东西?
朱天心:你说的这几种情形都有作者去这么做。我自己是觉得,所以更得 “在着”。纯文学这个族裔已经快要绝种了,如果有一天读者们说,那个恐龙快要绝种了,哪里还有一个让我们去看看?喏,恐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