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申府访谈录》:探寻一个多面人
《张申府访谈录》 舒衡哲著 李少明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年出版
世纪之交,一批跨世纪的老人陆续仙逝。特别是经历了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的离世,催生出许多回忆录和悼文,成为了当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同代人的回忆,还是后人的叙说,抑或是口述实录,却有不少只是盲人摸象,或者是过年话甚至谀词。我对于这样传记式的回忆录一直持有警惕,因为心理学家早就说过:“无论什么样的自传,都不会不包含着自我辩护。”
最近读美国学者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李少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一本前些年出的旧书,虽然写法是访谈式、断片式的,仍然属于口述实录的传记类的书。不过,写法和我们有些特别是那些有闻必录必信且倚马可待的报告文学和传记作家大不相同,舒衡哲的这本书,前后写了十年,对于受访者,是放在历史的语境和材料文本中比较,而后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判断乃至质疑。
因为舒衡哲发现,她在和张申府交谈中所涌现的史实,“有时是配合的,有时是扭曲的,有时是质疑的”。她希望她的书能够“是一条锚索,使回忆不致从复杂的真实经验中漂流得太远”。
这是每一位传记作者都需要警醒的,特别是面对张申府这样横跨几个朝代又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在中国现代史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复杂多面性,不是黑白判断那样简单明了的。在某种程度上,回忆有时是不可靠的,回忆面临着被重新唤醒,或法国哲学家《论集体记忆》一书作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恢复”。所以,舒衡哲把自己的这本书命名为“一部关于记忆与失忆的寓言”。这不仅是对受访者的一种负责的态度,也是作者应该秉持的良知。
因此,她既写了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的光辉历史,写了他对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哲学的贡献,他最早介绍罗素、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维根斯坦,扩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视野的学术成就,以及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等人的思想熔为一炉的狂想;她也写了他在历史风云跌宕之中的沉浮,包括1923年被清除少共,1925年退党,1948年为3000元写作《呼吁和平》而罹难,被新中国定为“人民的敌人”和“卖国贼”,以致被他自己始创的民盟开除;以及1957年右派之冤和文化大革命之累。
同时也写了他对处于危难之际的周作人、梁漱溟、章伯钧等人出自性情的关心。
但是,她也以相当的篇幅,直言不讳地写了张申府种种弱点毛病,甚至在我们平常人看来并不光彩的一面。
比如,她写了他“自我吹嘘和历史考证的混淆”。“修改历史纪录以突出他自己和他经手组织的巴黎中共小组的重要性”。
比如,她写他只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五四运动若即若离,“当其他的政治行动派为革命舍身的时候,这些怀疑使张三心二意,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比如,她写他的“自夸”,说他的学术成就过于博杂,杂而不纯,“没有一部正式的著作……甚至生命的尽头,他和1918年的自己可称无甚差别,依然故我,仍是杂志的作者和读者”。
比如,她写了他批判胡风,“像1948-1949年张的爱人和朋友公开表示要‘严惩叛徒张申府’,现在张又被迫用同样的字眼给诗人胡风套上罪名”。他曾经也被体无完肤地抨击过,当然懂得这个罪名的滋味,“但现在却要用同样的标签抹黑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再比如,她不止一处批评他的风流,并以整整一章(全书共六章)的篇幅,写他在罗素性解放的影响下和几个女人的关系。这一章的题目叫做“浪子和解放主义者”,明显的批判色彩,在写了他和两任妻子的关系之后,她着重写了他和刘清扬、董桂生和孙荪荃三个女人的爱恨情仇。
张申府标榜自己“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他认为女朋友这概念来自西方,五四之前没有,五四给了他自由去找女朋友,“可以说我是五四时期才成为了男人。”而她则一针见血地批评他说:对爱情特别对孙荪荃的言行不一背叛,“外表上尊重女权的人,内里原来抱残守缺”。
很难在我们的传记类的作品中看到这样不留情面的书写。我们更愿意为贤者讳,愿意表扬和自我表扬,愿意在个人恩怨之间相互指责攻讦,愿意在人造泳池中去扬帆破浪,便当然和真相拉开了距离,有意无意之间把书写的对象特别是如张申府这样的大人物,书写成哈哈镜里的镜像,或戏台上披戴装扮过的角色。
舒衡哲认为信史的书写是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和受访者一起解谜的过程。她说:“作为一个历史过来人,在公开和私下的回忆里,张戴上不同而且经常互不协调的面具,这就越发使得他的谜解不开。
”她还说:“一个幸存者,基于需要,必定是一个双面人(甚或是多面人)。”舒衡哲的这些经验之谈,对于我们今天颇热的各类传记类的写作和阅读,是一个有益的路标。
想起放翁有诗云:史书弄笔后来事,绣鞍宝带聊儿戏。是因为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舒衡哲说过这样话:面对张申府,作为历史学家的她不能视为儿戏,那些真实的事情,像河里的尖石块一样,每一次走进就会刺她一下。在我们这里,却常常把它们当成儿戏,而且是要把它们“绣鞍宝带”装扮一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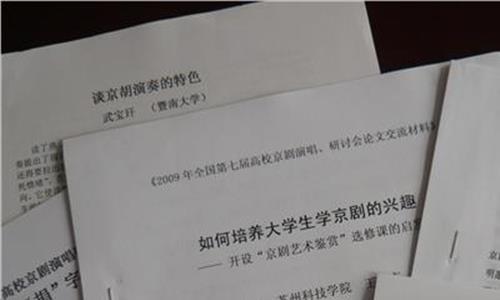





![>“面人王”捏出嫦娥奔月“捏面人很快乐”[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e/9c/e9c301f00bc6956c904e317ed44ae089_thumb.jpg)

![>朱德为什么不要陈玉珍 [转载] 周恩来为什么要下令处决朱德第四任妻子](https://pic.bilezu.com/upload/b/22/b22837920d398a09ab4d6b1bdff0f9ca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