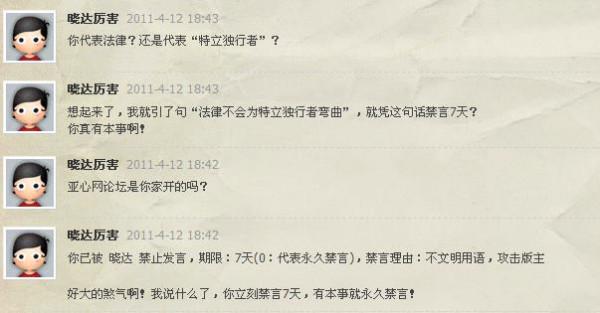人物访谈:访诗人艾青之子著名油画家艾轩
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差异。它的差异在于一种是娱乐人的眼睛,而另一种却是感受人的心怀。中国写实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北京画院油画室主任,国家一级画师,著名油画家艾轩(著名诗人艾青之子)的画,给人的感觉便是一种心灵的震憾。
他的作品,其中心就是一个人,以孤独的图像出现在漫涌天际的枯草荒原上,于是在这宁静的画面之中,有多少情绪在交织?又有多少情愫在激荡?那每一笔,都似在低声向我们倾诉着,诉说着属于艾轩灵魂深处独有的秘密,而这秘密如同遥远的天际突然传来的轰雷声,重重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这成为了我执意要与画家对话的原因。
中电文化:读您的画,总感觉到有一种矛盾纠葛在其中,因为画面的背景总是那么苍凉而空茫,像是没有被污染过的远古,它透着一种生命自然的本真,然而,画面人物却又总是年轻如花初绽的生命,您似乎试图要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来反映什么?
艾轩(以下简称艾):反映宿命,这宿命它来自于一种无可奈何。我是到了西藏那个地方以后才感觉到宿命的存在。因为那里很荒凉,除了有一种画面感外,我更多地感受到的不是壮丽和辽阔,而是作为人的渺小和脆弱。因为,它的环境很残酷,那里大自然环境给人的感觉,跟北京周围大自然环境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高原,海拨非常的高,它的气候变化非常的恶劣,它会突然间暴晒,而后随时来的一片云就可能是冰雹,夏天的时候还会有暴风雪来,人在这里总是处在自然的蹂躏之中。
自然老在蹂躏着人,那种感觉完全不像在北京,随时都可以躲避蹂躏和侵袭,而在那里,人却是无法躲避的,只有忍着,只有无可奈何地任其蹂躏。自然总是这么揉搓着人的脸,几年前还是很好看的小孩子的脸,几年下来就会显得很苍老、很憔悴,让你感觉时间的跨度很大。
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小孩子很小很好看的,可是过几年再去找她,完全辨认不出来了。因为她每天都要放牧,要去拴牛、拴羊,还要把牛粪往墙上贴,好晒干当柴火烧。
城里人到那里后,他们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很神奇,却并不知道自然在这里无情地蹂躏着这些面孔,所以我就感觉到人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是特别的渺小,特别的脆弱和无奈,特别临时,美似乎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所以我的画里面都是一些人类临时的感应过程。
中电文化:这就是你所说的宿命、轮回?
艾轩:是的,宿命。轮回是西藏人的说法,我只是从中感觉到一种无可奈何。人在自然面前是这样的脆弱和渺小,所以对自然的蹂躏,只有面对,只有承受,只是在承受之时会显示出一种刚毅。人处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没有办法不刚毅,因为无可奈何,你只有刚毅,所以在那里生存的人,都把希望都放在转世里。
中电文化:把今生的希望都放在来世里?
艾轩:是的,他们把今生的希望都放在转世上。像他们转经啊等等,都是在祈求来世的幸福,而对当世却并没有太多的奢望。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这种生物体完全不同于我们这个城市周围的生活状态,他们就像是生存在大荒园里的一道雪线,说得残忍一点,这雪线就等同于回收生命的死亡线,就是无休止地回收生命,然后再创造出新的生命,再回收生命。
我经常画那种漫无边际的雪坡,实际上就是带有这种寓意的。雪坡其实就是代表一种严酷、严峻,不可超越,也不可抗拒。我是想表达这种东西,至于为什么,我是说不清的,艺术就是这样,你真正想表达一种什么,有时连自己都很难说清。
中电文化:这或许就是艺术的魅力。
艾轩:是的,说不清楚。你可以说这是对命运的一种判断,也可以说是对自身的辨认,也可以说是对某些事情的悔恨,或是对未来的不可知,总之有很多种感觉在里面,而不是特别的、明确的、表达单一的感情状态。
中电文化:有时候是这样的。
艾轩:自己说不清楚,表现在作品里便也说不清楚,因此别人看我的画后会说,看了你的画之后,让人心里有一种咯噔一下的感觉,但为什么会咯噔一下却不知道。很多人看我画之后的感觉都是这样,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感情的传递吧!
中电文化:我也有过这种感觉,那是您作品人物的眼睛所致。它含满了忧郁,而忧郁之中,却又透出一种渴盼和希冀,感觉您是在借人物的眼睛作为心灵的通道,来表达您自己内心的某种渴望?
艾轩:怎么说呢?绘画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它自然不自然地会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倾向,这种情感倾向,有可能是特别外在的,特别张扬的,也有可能是比较含蓄的,比较蕴藏的一种东西,而我可能比较复杂。实际上看见一些人做为个体在这荒原上,这种状态,你自然就会联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一种什么位置。
你在辨别自己,每一个看画的人都会这样来辨别自己,你为什么被这种东西冲击了?你为什么会有感触?我想这足已说明绘画者已经达到了目的,因为他的作品引起了共鸣,这种共鸣也许只是一种感觉,或者是想哭,或者是心酸。
很多人这样来跟我讲他们看过我作品之后的感觉,这样讲的人不是一个地区,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这时我就想,这可能就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我是说某个面,因为人类的情感是由多面构成,而不是某个面来代替全部,至少它能撞击出某些人情感中的某一面,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成功了。
中电文化:但是,当代有许多美术作品,即使是被炒作很高的作品,却充满了媚俗形态、虚浮概念和浅薄的趣味。做为当代一个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您怎么看当下的这种艺术形态?
艾轩:绘画的冲击力,表现在当下的一些作品,比如波普、装置、或者行为,我觉得它们只属于当代艺术中的某一个分枝,它不能囊括于当代艺术的全部。当代艺术的全部,是当下所有重事艺术的门类,都算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比较清楚。其实在中国最好的艺术形态,是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
中电文化:有许多人管那一阶段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艾轩:我觉得那阶段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为那时候绘画跟政治几乎脱离了关系。比如我原来在部队的时候,绘画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到了八十年代初,便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到了九十年代后,绘画又变味了,商品进入了,西方的资本进入了,还有国外的意识形态进入了,比如说政治。
这时的政治跟原来的政治又不一样,由原来麻木地吹捧一切“红、光、亮”,到开始找你的毛病。有许多画家,比如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些画家,就是靠政治起家的。
他专门挑中国人的毛病,把中国人画得很难看,外国人看了很高兴,以为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这样是不是好,这只能做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但是这个现象确实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兴起。2005——2006年,这些画家开始靠资本运做,在西方炒作,炒得很高,其实这是另外一种东西,和绘画本身没有关系。
而我们所画的这些画,是属于当代的写实绘画。写实绘画在中国的状态目前还是属于高技术含量状态,它在中国经过一百年的传承,加之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不断走出去,去国外学习,这才纠正了原来很多人把油画带给我们的所固定的一些东西,创造了一些新的原素,而且画的技术含量也比从前高了许多,所以才有能力去刻画人物的情感。
因为刻画人物的情感是要靠细节、靠情感、靠深入。
中电文化:写实就是靠细节、靠情感来打动读者。
艾轩:绘画者只有很高的能力和技术,才能表达出来。
中电文化:这其实跟写小说很相像。
艾轩:是的,不只要有故事,还要有很好的技术。你可能经历很多,一肚子的故事,却因为没有很好的技术,便可能都烂在肚子里,死了。你只有通过有才能的表述方式,天份,再加上后期很好的训练,才能创作出好的小说作品。音乐也是一样,若是没有好的音乐演奏,或是没有高技术,你就只是瞎哼几嗓子,听众也不会知道你在唱什么,所以也就不会被感动。你得有很好的技术,所以,我们现在强调技术含量。
中电文化:也就是说没有技术含量,也就不可能表达出很充沛的情感。
艾轩: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艺术,它可能会打动人的眼睛,但却打动不了人的心灵。我觉得能冲击人的心灵的这样的艺术作品才是好作品,哪怕你绘画的手法比较拙,但最终能撞击人的心,撞击人的灵魂,这说明这作品到了一定的高层次。有很多画只是让人感到悦目,但不会在心里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共鸣。
中电文化:是这样的。有很多作品虽然好看,可只是好看,你却无法感受到它里面所包含着情感和思想。而您的画不同,虽然画面给人一种寒冷、凛冽,充满了一种伤感、无奈、心酸,可是看过之后还想再看。
艾轩:我自己也是这样,有时想这画是怎么回事,去看几眼,过一段时间,还想再看,还是那个味道,这才避开了,因为我不能总在那种味道里面停留。
中电文化:最初看您的作品,打动我的是《静静的冻土带》,画面上女孩儿的那双眼睛非常地打动我,可是后来,我发现那幅《歌声离我远去》更让我感到震憾。虽然画面的人物并没有像《静静的冻土带》画面人物那样,一双大眼睛直视着你,她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瘦弱娇小的侧影。
艾轩:而且眼睛黯淡无光,面部也比较模糊。
中电文化:对,面部比较模糊,但她瘦弱的侧影,透出的那种无奈与无助感,却让人的心灵为之感到一颤。这也是纠结在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您的作品,有一部份,像《静静的冻土带》,画面人物是直视读者的,而一部份却是侧身面对远方的,例如《歌声离我远去》,还有一部份完全是背影,你几乎无法看到人物的表情,这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是三个不同的创作阶段,还是你在三种不同的心态、或是情感支配下完成的?
艾轩:我觉得重要的不在表达的姿势,而在于某种姿势下能够表达出的一种情感。比如背影,或是趴在栅栏上的,或是趴在桌子上的,阳光照在他们的背上,例如《也许天还是那么蓝》,其实这背影都是很苍凉的,而它们传达出的信息却很深很深。
就像我正在创作的这幅画,我原来画她睁着眼睛,可我觉得睁着眼睛浅薄了一点,我觉得睡着了以后更有味道,所以就把她画成趴在那里睡着了。但这似乎不符合市场的要求,我画的许多女孩子都是挺大的眼睛,它符合市场的要求,满足了一部分喜欢这种状态的收藏者。还有另外一部分收藏者,他喜欢比如像《歌声离我远去》这种,他觉得这种东西更有味道,这不能说哪种绝对好,只能说感觉不一样。
中电文化:视觉冲击给人的感觉很直观,有一种优美感。
艾轩:但是不是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画画跟做音乐一样,只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的一种感觉,只要把这种感觉表达到一种极致便可。
中电文化:您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可您的灵魂似乎并没融在这里,您总是超然于度外,这从您画作选取的背景便可体会到。您选取的画作的背景,总是空旷、寥远的荒原,使得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苍凉孤寂的情绪,静默而又神秘,而如此苍茫的荒野,衬托的人物却又都是独立的个体。
当人做为生命的载体独立出现在这样旷远的背景下,生命便显得孤独而脆弱,这样刻意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时常会感到您的内心就是这样的孤独苍凉,无人能解呢?
艾轩:至少我的画是这样,我在画中刻意寻找这种苍凉。我不是融入不了大都市,我知道大都市很好,很热闹,很繁华,有许多你需要的东西,灯红酒绿的,但是人有多层面,他在大都市里却时常会感受到大都市的荒凉,他到那个荒野里去,把心灵放置在荒野里,在荒野中寻找美,他会感觉到在这里他能够完全地展示自己。
从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我每年都会去西藏。我经常在暴风雪里翻车,或是车撞山崖上了,或是赶上塌方。像这次汶川地震,前前后后我就去了几十次,走的都是同一条道。从汶川进去到阿坝,我画的都是阿坝,这里人的状态和原生态感觉都要好很多,人就是这样,在大都市里生存得也很好,可是——
中电文化:虽然生活得很好,可是在你的内心深处,总感觉灵魂无处安放,找不到归属?
艾轩:正是这样。我总是想要到荒野里去,到那里呆着,四处都看不见人,只是坐在那里呆着,一个人看着地平线,草刷刷地响,听着风呜呜地响,云一回儿来一回儿走,这种感觉很好,怎么好自己也说不清,莫名其妙的。有人说我是受虐狂,喜欢受迫害,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随时都要面对塌方、泥石流、高山反应、流鼻血、头疼,折腾得好几天都会睡不着觉,可每年我还是会去。
我内心总感觉那里画不完,总想画那里,你知道,画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画不下去。
比如能力啊,画面色彩的感觉啊,超控整个画面构成的能力越来越差,所以,我现在就得抓紧时间,我估计还能画几年,我总感觉到还没表现够,还有很多很多的情感没有发掘出来,所以我还想再画,但是到了一定阶段,我一定会画不动的,就跟“地平线”在那里等着我一样,那是毫无经疑问的。
那地平线很严峻,很不饶人,我必须得面对,这就得赶时间,多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特别能够震憾我自己的。震憾自己了,也就震憾别人了
中电文化:也就是说,其实你内心有很多东西始终没有被人读懂,只有靠绘画来挥发出来。
艾轩:是这样吧?(笑)
中电文化:您的许多画作都是那么的清冷而诗意,而您为画作起的名字都如诗一般优美,将意境喧染得愈加深远,而这些如诗一般的画名中,我发现您常采用“歌声”如《歌声离我远去》、《极远的歌声》、《那歌不是唱给我的》,单读这些画名,让人感到有一种剌痛,一种怅惘,这“歌声”两个字,是不是隐含着一个人或者一段往事?
艾轩:(你自己猜?笑)这歌声通常是一个暗语,其实它体现的只是一个很远的声音,也许这声音离我越来越近,正在向我走来,也许它曾经属于我,但却离我远去,而且是越来越远,不再属于我了,这完全依靠个人的想像,你可以把歌声量化成一个人,一个景致,一段往事,一个故事,都可以。
我感觉给画起题目,其实也是心灵的一种碰撞,不只是为了说明这张画,倘若只是为了说明一张画,还不如给画起名叫几号作品呢,画名和画其实是一种对应,是一种震憾,震憾加震憾,然后就会引人注目。
有些人说我起的画名是受遗传基因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画名与画体现的都是一种宿命,跟人类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心灵中的苍凉感,都非常吻合。比如那个孩子趴在那个桌子上,《也许天还是那么蓝》,就感觉活着的无奈,后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只是心灵上有那么一小回儿的慰籍,而后面无数的急风暴雨可能随之就来了。还有《她走了,没说什么》。
中电文化:这个题目听来让人心里有一种痛感。
艾轩:这不是刻意起的,而是自我流露出来的,因为当时市场并没有这样要求,就完全是靠自我感觉。一个人坐在那儿发愣,连脸都没画,只有头发飘动着,还有一个拴牛的桩子,周围都是草,忽然就想叫这个名字,而且觉得很有味道。比如还有一个男的坐在那里,叫《风把歌声吹散了吧》,至于为什么风把歌声吹散,那是他自己无法言说的伤痛,别人不会知道的。
中电文化:在艺术品市场里,出现了仿您的假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艾轩:很多,十几年了,北京潘家园那里有的是。仿了十几年这说明这个市场很大,而且大江南北都在仿,从拉萨到福建到各个酒店、旅游景点,布达拉宫脚下,成都的街上,把我的画画成素描,拿着绳子挂在那里。后来我想,他们仿了十几年了,这说明我的画到现在还很有市场。
有人在仿制我的作品,这就是说有很多人很喜欢我的作品,不然不会仿制。仿制的画中,有许多画是不签名的,他觉得可能是签名不好,只要画出来很快就会被旅游者拿走。还有一些人属于高仿,这些人仔仔细细地仿,认认真真地画,画好后,拿到拍卖行去当真画卖,卖的价很高,这不好。倘若你只卖给旅游者,很少的钱,为了生活可以理解,但若是当真画卖就不好了,因为那是欺骗(笑)。
后记:采访结束时,已是夜里九点多钟。走出艾轩的家,刚下过雨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潮湿的青草的味道。嗅着青草的芳香,不经意地回头去,只见艾轩站在门灯下,不知为什么,那身影又使我想起了那幅《歌声离我远去》,这似乎再次认证了我的感觉,与其说画家是在画西藏风情,不如说画家是在抒写他的内心独白,抒写他内心中那种孤独而又苍凉的感情和记忆。这或许就是画家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