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国遗稿谈林彪家选妃选婿
王维国 (1919年9-1993年)河北元氏万年人,1938年6月入党。1938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68年1月兼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临时常委、书记。1969年3月任空4军第1政委。
1970年3月兼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兼上海市委常委,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85年刑满释放。中共9届中央候补委员。1993年去世。)
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章回忆说,空4军的确抽调了几个干部组成小组,专门为林立果找对象,后来也为他办一些其它事情,总之是为林立果的生活服务。成员有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组织处处长袭着显、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管理处处长过全、保卫处副处长唐剑鸣、秘书处副处长郭永诚,干部处副处长张兆玺,还有空军455医院的护士小卢;因为是八个人,所以也称“八人小组”,严格地讲是个“概念组”。
我既没有听过我父亲用“小组”称呼那些部下,也没听他提过什么“入组须知”。找对象的事情应该是叶群托付给了江腾蛟,江腾蛟跟我父亲打了招呼的,这八个人基本上都是当年江腾蛟任空4军政委时的得力下属,林立果来上海,要办的事情就由他们去办。
王大章还说:我父亲王维国虽然不了解为什么以这种形式给林立果找对象,但肯定要支持。江腾蛟具体是怎么过问的我不太清楚。负责找人的基本上在外面跑,有什么需求要依靠军里时,再来找我父亲,但他不管“找人”的具体事。我记得有一次,蒋、袭二人看上一个女孩子就跟到了她家里,动员她当兵。女孩子的家人从军装上认出他们是空军,结果直接告状到了张春桥那里。
王大章讲的这段经过,《王维国遗稿》中也提到了:
【1971 年2月我向“找人小组”讲了一次话,中心内容讲的是要他们在找人时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出乱子,不要惹祸,不要帮倒忙,影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威信。当时我也提到,我们和王洪文、张春桥的斗争已经明朗化了,要他们在“找对象”中注意策略,照顾大局。
由于“找人小组”当时在上海柴油机厂找“对象”时出了问题,对方告状告到了市革会,张春桥在告状信上批示“请维国同志调查处理”,搞得我很被动。所以我的讲话内容主要是关于找人的方式,叮嘱他们前提是注意和 “上海帮”的斗争,不要乱搞。】
1970年初李伟信到了林立果身边,林有事直接通过李跟蒋、袭联系,后来小组成员和林立果也熟悉起来,渐渐牛了,不太把王维国放在眼里了。
据林彪女婿张清林讲,叶群为儿女找对象一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全会是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林彪那时一直在大连休养。在开会之前,毛泽东要林彪回京参会,林彪无意参政,托病不回。
后来,江青就给叶群打电话,李讷也给林立果打过电话,邀请他回北京参加运动。叶群告诉林彪,江青在电话里要求林彪回北京参加全会,要求豆豆(林立衡)和老虎(林立果)都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青在电话里还讲了,大意是两家的孩子都不小了,想把女儿介绍给老虎(李讷比林立果大好几岁),把毛远新介绍给豆豆。林彪听了以后说:“搞什么封建联姻?!要拉人整人了,别理她!”这些叶群都有电话记录。
在中国,利用生活作风问题把人搞臭是一大制胜法宝,“9.13事件”后也一样,“选美”、“选妃”令人们津津乐道。人们只道是林副统帅的野心膨胀,才如此张扬,不料底牌却是叶群与毛家刻意保持距离的韬晦之计。
但并不高明,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由于当时“找人”的人不少,找的人也不少,借此向林彪表忠心,一时间吹喇叭、抬轿子,越来越热闹,局面逐渐失控。
1965年吴法宪带领空军党办几个秘书(包括刘沛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陪同叶群到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那时空4军政委是江腾蛟,王维国是政治部主任。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叶群曾经把还是大学生的林立果托付给江腾蛟照料,因此后来叶群托“江叔叔”在上海给林立果找对象。时值九大党章总纲写进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人们心中毛林一体,江腾蛟衔命而来,虽无“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但其中的深意谁都懂得。
林彪、林立果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当时紧跟他们就代表着“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1970年7月底,吴法宪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公开讲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王维国还把政治上跟随林立果比喻为坐上“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其忠心耿耿可见一斑。
王大章讲,我父亲是二野的人,跟林彪没有历史渊源,只因他在上海市革委会和公检法主政深感艰难,林彪主管军队,认为有林彪做靠山,就不怕上海帮了,所以把对毛的崇拜,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很具体地“落实”在了林彪、林立果身上。
记得那是在1971年,有一次林立果来上海仍然住在巨鹿路招待所,我父亲每天都去陪他吃饭。林立果曾经有几天觉得肝区不适,八人小组有人跟他透露:王政委得过肝炎,别是王政委把你传染了!
结果他再去的时候林立果就把饭菜分成了两份。一开始他没觉得怎样,还让医生来给林立果检查化验,后来他听说有人讲可能是自己传染的林立果,很生气。
他的肝不好是因为1958年被诊断为“阿米巴痢疾”,服药过多导致了“中毒性肝炎”,早已痊愈。这样我父亲也不去吃饭了。
林立果化验一切正常,他也知道我父亲不去吃饭是有人说了“传染”的事,为了消除误会,就提出来要到我们家里来“看看王政委的孩子”。
我们家那时候住着一栋日式的旧房子,墙壁又薄,外面下雨,屋里墙壁上洇得一大块、一大块的,像地图一样,破破烂烂的,怎么好来?结果还是我们都去了巨鹿路招待所,受了林立果一次接见。
林送了我们几个很时髦的人造革拉链提包,送了我一个军用指北针。 这是与我们一家仅有的一次“私交”。
上海是林立果与上海帮的必争之地,王维国想靠,林立果想拉,这就是王维国在《遗稿》里一再强调、没有明说的“特定”历史条件。
对自己和“两谋”的关系,《遗稿》强调“我不知道他们在搞反革命政变……更不是为了他们搞反革命政变服务”;“我不知道、也没有和他们一起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事实上……是碰上了他们可能想搞政变;他们在欺骗我,利用我”。
法庭认定王维国参与了对这个“小组”的领导。对王维国的辩解,法庭的逻辑是:“被告是空4军的领导,'小组’成员都是被告的部属,当然是他们的领导”(《审判顾同舟、胡萍、王维国材料汇编》1982年4月,112页,下称《材料汇编》)。
其实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法庭,都有意模糊“领导”的概念,把王维国和“找人小组”的行政关系与林立果对“找人小组”的“指挥”混为一谈,这样就把林立果与王维国连在一起,林立果让“找人小组”干了什么,等于王维国也干了。
林立果搞了“两谋”,于是受他“指挥、控制”的小组最后被戴上了“为武装政变直接服务”的帽子,其成员幸免刑罚,但对“两谋”不知情的王维国,却因是小组的所谓“领导”,与“武装政变”搭上了界。
出现在于新野笔记本里的“上海小组”一词,更像是为与“北京”相区别,与“调研小组”相区别……无论叫什么,只要小组成员没有搞反革命的故意,没有参与政变的故意,都不是犯罪。
再说笔记本是个人的,只能证明于新野自己。
王维国对自己的问题是这样的认识:“我的问题的实质,是在'文革’动乱中,在上海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下,我把林彪一伙当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来看待,信任他们,依靠他们,受了他们的蒙蔽,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利用了。
也可以说,是被他们捉弄了的人。在我总共和林彪一伙接触的一年半中,我是犯有错误的,有的是严重的,但我绝不是和他们共同犯罪。”(《遗稿》)
组织专人给副统帅的儿子找对象,为他来上海大修居所,甚至是为此组建了一支警卫队伍,这些做法在如今听来都象征着特权,是权力腐败,是王维国为首的空4军领导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自觉为林立果在上海的生活以及保卫服务,并且上升到“路线”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去认识,以至于最后在党内路线斗争的洪流中沈浮、迷失。
但特权也好、腐败也罢,说到底和政变是两回事。王维国的要害问题是满心革命、忠心耿耿却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而卷入另一个漩涡,渐变到了空4军为林立果所用的境地,为其左右,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做了林立果想做的事。
这也怪不得谁,凡政治上一面倒的做法本身即具有高度风险,历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至图穷匕见,王维国方大梦初醒!
扪心自问,王维国不是不后悔,但他对照法律认错不认罪,即是他个人作风使然,耿直性格使然,几十年党性使然,对“文革”历史态度使然。对照法律自检,错是就错了,没有的就是没有,该认账的认账。但对罪与非罪,绝不乱认;谁想压服他,他绝不服软。
林立果开“三国四方会议”当晚出意外插曲
2,王维国成立军教导队的前因后果
王维国《遗稿》称:成立军教导队“早于”《“571工程”纪要》(下称《纪要》),“是当时和'上海帮’斗争的需要”。王维国此言大大悖于官方关于“两谋”说法的时间顺序:《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召开——成立教导队——政变,颠覆了原本听来顺理成章的案情。
空4军在巨鹿路有一个不错的招待所,里面有十几幢老洋房。首长们、包括林立果来上海一般都住在那里。后来林立果为什么不住了呢?据王大章所知:有一次林立果从上海回到北京,吴法宪问他在上海住哪里了?他说住巨鹿路招待所。
吴问住招待所哪里?林说招待所里面靠巨鹿路边上的一座小楼,是个新修的独立院落,可以单独进出,不需经过招待所大门。不久后吴法宪到上海来,他指名道姓也要住那里。张春桥知道吴来了上海,一定要登门拜访,所以张春桥也去过那幢小楼。既然张去过,林立果就认为那里暴露了,再也不愿意住了。
还能住哪里呢?王维国感到比较为难。岳阳路少年科技站是上海警卫处招待所,临时住一住可以,但总不是长远之计。于是他和军里领导商量,想启用新华一邨招待所,但需修建一下,另外警卫问题还是自己来解决。所以修建新华一邨和组建教导队,先在军里基本上有了一个统一的意见。因为修建工程还没有正式动工,1971年3月份林立果来上海便暂时还住在岳阳路。
王大章讲,“三国四方会议”当晚还出了一个意外插曲,大家都紧张坏了!——“林立果他们都在里面的时候,警备区有一支部队,搞不清是一个连还是一个排,突然就把少年科技站包围了!而担任科技站警卫的只有我父亲从警卫处调来的一个班,虽然有枪但都是手枪,短枪跟建制部队的武器比,在射程和威力上是不能比的,而且来人很多!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父亲和李伟信等人很紧张,不是为别的,林立果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怎么跟林家交代?!
当时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过了一会儿这支部队集合起来又撤了,这才分析他们是搞演习。通过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林立果今后不能再住这里了,要住我们自己的招待所,要搞一个我们自己的警卫部队,决定加快把新华一邨的招待所修一下,然后搞一个负责警卫的教导队,既培养干部,还可以给来上海的首长担任警卫工作。
”本来与“两谋”无关的教导队就由这件突发事情而正式启动了。因此王维国在法庭上理直气壮——“能够证明此事属实的,应该有空4军党委会上我的发言和大家的讨论、会议决定等记录为证。参与此事的一些人都还在,而且也不会忘掉,都可以证明我的话属实。”(《遗稿》)
王维国称:“1980年4月公安部和总政治部合审我的案子时,他们叫我看过一份证明材料,是我在1971年3、4月份指示空4军干部处副处长张兆玺,布置向部队下达关于选拔教导队干部和干部苗子的六个条件的文件照片,那是当时的原始记录,而且是当时实际实施过的,很能说明我们办教导队的意图和目的。
这个材料的内容是这样的:关于选调'教导队’人员的条件:1,政治思想好;2,无复杂社会关系;3,身体好;4,打过仗;5,和首长有感情;6,不要选本地人。
” 并且解释说“不要本地人就是不要上海人。因为教导队是在上海市新华一邨招待所担任警卫工作,上海是张春桥、王洪文的地盘,本地人社会关系多,容易泄密,为了接受教训,所以提出了第6条。”(《遗稿》)
王维国在法庭上认可的证人证言极少,我们注意到这份证言证明教导队组建的时间,先于林立果等人制定《纪要》的3月24~26号,也先于3月31号至4月1号的“三国四方会议”。这一点证明了(1982)刑二字第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下称“裁定书”)认定教导队是“按林立果等人根据武装政变的需要”组建的指控是不实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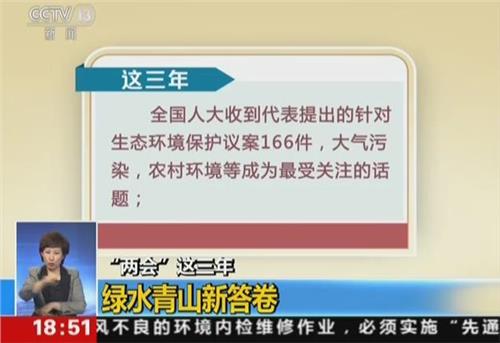

![【选妃记杨柳之死是哪集】选妃记[2001年陈好主演古装喜剧]](https://pic.bilezu.com/upload/0/0e/00e317c4a3695b7ae92a98475c2d03c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