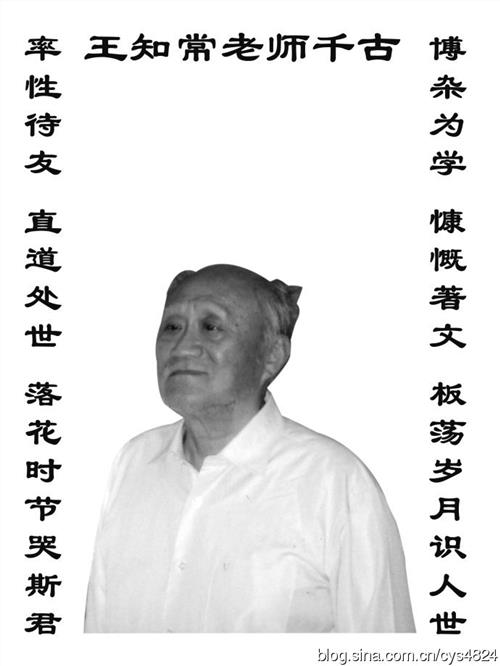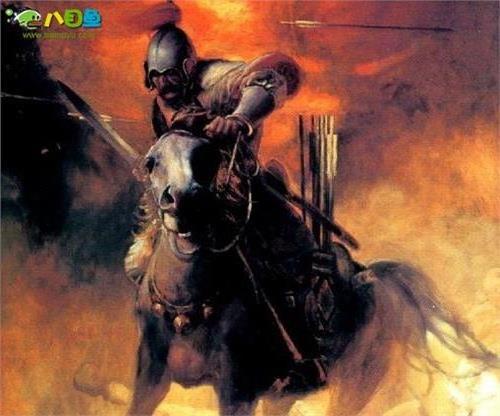王知常朱永嘉 朱永嘉:祭亡友王知常文
毛主席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为人民服务》)
王知常老师,于今年四月十一日去世,为此我们在四月二十六日举行了一次追思会,会议由高志仁同志主持,出席者三十人左右,有他的夫人、儿子和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寄托我们对王知常老师的哀思。会上朱永嘉念了祭文,肖木、吴瑞武、王绍玺写了挽联,他儿子王震作了题为《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的发言。此后肖木、王绍玺、余子道、郑宝恒、章智明都作了简短的发言。
祭亡友王知常文
朱永嘉
维公元二〇一四年,岁次甲午,农历三月十一日,午时,朱永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知常之灵。
呜呼知常,吾有数言,君其闻否!朋友凋落,永诀之情,从古所悲,不图此言,乃为君发。忆往昔,与君相处,数十年矣【1】。专题写作,尔今先去【2】。《红旗》组稿,朱王肖仨,一鼎三足,折足倾覆,公餗形渥【3】。思君平昔,不计名利,好强胜人。
博览群籍,学识渊远。作文深入浅出,衣着不修边幅。言语率性,谈笑风生,却又不留情面。替人改文,心甘情愿,为他人苦作嫁衣。上命差遣,奋不顾身,积劳成疾,从未怨天尤人。想当年,大难临头,不思畏缩,慷慨挺身艰难。
十二年,牢狱苦难【4】,相忍同为难友;相助相扶,苦心孤诣,教导后进青年。一生一世,忠心耿耿,不谋个人私念。忍辱负重,君皆饮恨吞声而痴心不改。此中甘苦,何足与他人道哉!况自古以来,君子遭际,莫不皆然。
意君所去,乃形质耳,魂气与精神所托,其灵恒常,千古之文章,自有后来。今日哭君,吾身孤寂,唇齿相依,含泪送君。白发白须,墓期非远,但问泉下有无相见。魂兮归来,听予哀词,君必知我所思所言,矢心不渝。
呜呼哀哉!尚飨。
注释
【1】与君相处,数十年矣 王知常,又名王乃天,语出《老子》第十六章。他1949年即参军了,那时他已高三,是一个学生兵。参军后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长期随军在扬州。
他是在部队入的党,以后是南京军区政治委员肖望东的文化教员,中尉军衔。1957年要求转业,升学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学生时代他便与同学合作出书了,毕业以后,留校为近代史教研组教师,任金冲及的助教。
1963年参加罗思鼎小组,那时学雷锋,向党表示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故谐音取罗思鼎为笔名。以后一起调至华东局内刊写作反修文章,后被留在内刊编辑部的历史组。那时金冲及是组长,组员有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
后金冲及随石西民去北京,王知常与我一直在市委写作班共事,那时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由上海市委领导和安排的。批判《海瑞罢官》时,我们奉命为姚文元提供明代的历史资料,因此而成为毛主席亲定的姚文元的写作班子。
直到1976年10月,我们一起受审查,一起服刑,刑满以后一起写作,前后相处五十余年。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组织上安排的,参加党,参加革命,就要服从组织安排,都有一腔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故大家为了党的事业心甘情愿、忍辱负重、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而无怨无悔。
【2】专题写作,尔今先去 指1967年3月,原写作班的人又集中起来成立专题写作组,共有八个人,有吴瑞武、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肖木、吴文虎、朱惠民,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纪树立,而纪树立因五七干校丁法章他们有意见,所以提前离开,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
我们为之不平,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专程去探望他。记得1967年的8、9月间,姚文元那篇《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章发表前,姚的秘书胡鼎君带了清样来,要我们提意见,我们不知所以的炮轰了一顿,说文章如散落地上的珍珠,没有中心线来贯穿。
后来胡鼎君说我们真傻,文章在毛那儿已经通过,而且受到表扬,是毛要姚来征求一下他的写作班的意见。其实我们应考订一下他的引文和事实。在原来八个人中,王知常第一个作古了,故云尔今先去。专题写作组解散是在1968年的8月间,大家分别到各个大学当工宣队员了,我去了华东师大,肖木去了复旦。
【3】红旗组稿,朱王肖仨,一鼎三足,折足倾覆,公餗形渥 红旗组稿,是1968年9月间,姚文元奉毛主席命,去《红旗》夺了陈伯达的权,主编《红旗》杂志,使停了很久的《红旗》杂志恢复出版。
这就需要有人为《红旗》组织稿件,经毛主席同意在上海成立《红旗》组稿小组,由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三人组成,故云“朱王肖仨”。在毛主席心目中,我们就是当初帮姚文元写作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写作班子,主席在与斯诺谈话中提到,他在江青《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亲笔加上姚文元的写作班子。
那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上海为北京《红旗》杂志组稿,我们从学校回康平路参加张春桥、姚文元召集的会议,肖木还戴着工宣队员造反派的袖章,姚文元看到说:“我们这儿没有派别,你戴什么袖章。
”肖木这才把袖章取下。事后他说那是上钢五厂的工宣队看到他手太白净,一付书生相,这样人家会怀疑你从哪儿来的,因此给他戴了袖章。
《易》鼎卦有象传,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有三足,折一足,鼎身就会倒下,鼎中之餗倾覆于地。餗,即汤菜稀粥,其形汪汪然。渥,汁液濡地之貌,这是凶兆。1971年上海市委写作组成立,便是由《红旗》组稿小组在组织文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写作组到1976年10月以后,经过清查才宣告结束,故其结局为“凶”字,我们三个人都入狱服刑了。
值得告慰的是,我们在写作组十余年,除了拼命工作以外,没有伸手要过官,更没有要过财物,清查时,我们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生活问题,两袖清风傲公卿。
又及:文学组姚汉荣同志在 2014年4月27日去世,丧报一个接着一个,无限感伤。我屈指算一下,写作组已经去世的同志很多了,除了徐景贤之外,历史组有陈旭麓、王守稼、许道勋、吴乾兑,经济组有顾澄海、曹溶,文学组有高义龙,活着的也难以相聚了,大家都已老态龙钟,行动不便,出行要有人扶携,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同志将不久于人世矣。
走的人,临走时都带有不少遗憾,我自己与他们告别时,总感到有无数话来不及诉说。写作组的同志,尽管历尽艰难,但大家对毛主席、对我们那个集体还是热爱的,对那时的集体生活,对故人仍有无限的依恋。社会在前进,但自己在情感上仍离不开那个时间段的真诚相待。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
【4】十二年,牢狱苦难 我们三个人都在1982年被判刑入狱,我是十四年,王知常是十二年,肖木是九年。六年隔离审查期,我们没有相遇的机会。大家一起进入提篮桥监狱服刑以后,我与王知常在八大队,肖木先在七大队,后来转到八大队。
我与王知常在八大队,从小监开出来任教师,肖木在《劳改报》当编辑。所以我们还有一起相聚的机会。肖木还在习美工作,搞美术创作,他的书法、绘画、泥塑的技巧,都在那儿发挥了作用。
办大专班是有一次王知常在我那儿提出来的,我同意了,一起向监狱领导同志提议得到批准,这样才在犯人中间招了四十多个学员,其中还有女监的学员。我们还成立了教研组,从犯人中物色了理科的大学生参加。
故最后四年我们是在监狱中搞教学。王知常后来还学英文,在监狱中搞翻译。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患难与共。我是1988年末保外就医,提前二年出狱。王知常是刑满出狱的,他与肖木刑满以后,还被强留在劳动钢管厂,那儿叫老三毛,都是刑满以后留厂劳动的。
他们继续在工厂劳动,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在那儿还是从事教学工作,一直到退休,所以他们工龄是从刑满以后算起。我保外以后,到刑满前是没有工资的,刑满后说是挂在复旦大学,开始有生活费了。
以后我们三个人又一起相聚,我先与萧木合作为台湾三民书局做《吕氏春秋》与《唐六典》的新注新译,以后与王知常合作搞《春秋繁露》的新注新译。与王知常合作到一半,他中途出车祸,几乎使他的眼睛瞎了,这是他最痛苦的地方,失明以后他失去工作能力了。
如果他刑满以后能回校安置可能要好得多,至少同学还是可以互相照应,还有图书资料比较方便。王知常跟我相处了一辈子,政治上的起起伏伏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我们写稿子,某种意义也是为生活所逼,劳保的退休金都是最低的,不够生活开支。虽然现实有很多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虽然我们历经个人命运的各种磨难,但我们三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辈子都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
一切苦难,都未能泯灭我们的那颗红心,而且我们的一切作为,始终审时度势,要说清楚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既不屈不挠,又以大局为重。同时我们这样的态度,从长远看,于国于民都是非常有益的。这也是一个共产党人为人应有的态度。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唯一值得告慰自己的地方。至于有一些人另眼看人,那就由他去吧,我深信历史会证明他们错了。
知常吾兄千古
博杂为学,慷慨著文,板荡岁月识人世。
率性待友,直道处世,落花时节哭斯君。
弟肖木挽
王君知常兄千古
求学就出书,毕业即上阵,复旦历届并不多见。痛故人今安在。
旧学根底深,行文似流水,沪上同辈能有几何。哭斯人昨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