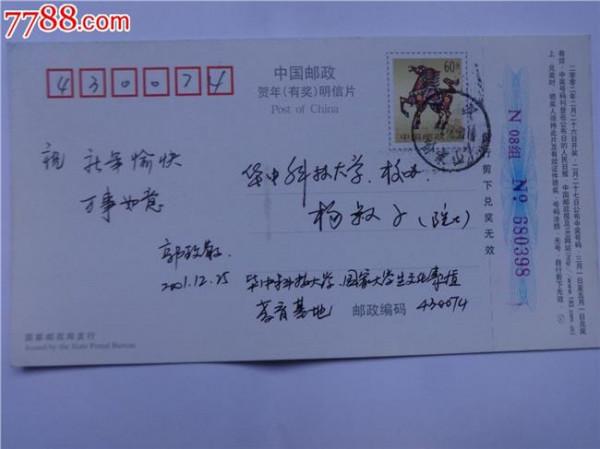朱永嘉老混蛋 三教九流过眼录|“文革遗老” 朱永嘉
在青少年时代,朱永嘉是一个让我仰望的名字。他原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兼总支书记,研究明史,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为人淡泊宽厚。按照他的气质,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大学者的。但他毕竟是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内心深处不甘寂寞。
1964年底,朱永嘉刚拜明史专家吴晗为师,并为之兴奋不已。几个月后,就被调到华东局写作组,成为“罗思鼎”的头领,毫不留情地协助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文革”时期,他还一度爬上市委常委和市革会常委的高位,掌管文教大权,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
当时爱读书的我最喜欢看上海市委写作班办的《学习与批判》和《朝霞》,这两本杂志都是朱永嘉管的,对这位上海第一大笔杆子相当崇拜。“四人帮”倒台时,他曾书生意气地提议发动武装政变,“再造一个巴黎公社”,以致锒铛入狱,被判刑14年。从此,朱永嘉这个名字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上世纪末,我在写有关上海知识分子的博士论文,朱永嘉是我的研究对象。1999年1月21日晚,朱维铮教授带我去登门访谈。复旦第一宿舍的老楼是上世纪40年代日本人盖的连排屋,坐东朝西的两层楼,一进门便是窄而陡的楼梯,每层楼两个房间,每个房间差不多也就六七平方米。
朱永嘉从当青年教师时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即使“文革”身居高位也没有搬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身材高大健硕,头发已经花白,操一口带浓厚吴语口音的普通话。
他把我们让到底楼的小书房坐下。小书房实在是小,一面开窗,另外三面墙,两个铁架床的上下铺堆满书报,勉强能挤下3个人。他在1988年提前保外就医,因为已过退休年龄,不再安排就业,由原单位复旦大学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交谈了两个小时。尽管此时的朱永嘉落迫失意,但也许因为有其老友朱维铮为我背书,和我说话还是比较坦率。他说,刚进监狱就给母亲带话,“在里面估计时间不会短,给我带一套二十四史吧。”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把二十四史反复读了几遍,悟出许多道理:“‘文革’中写作组的知识分子就像唐代的中书舍人、明清的翰林院学士,替皇帝起草各种诏令,总要揣摸上面的心思。
揣摸对了,是上面英明;揣摸错了,是自己倒霉。”“我本以为自己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家,实际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一场闹剧,也是悲剧。”言谈间流露出莫名的哀怨。
我俩再见已是过了近十年。2008年某日,友人带我去见朱永嘉。再次踏进朱永嘉的小书房,他说还记得我。他的外貌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多了些许白发,脸上写满悲伤。那天离他的夫人去世不久,屋里还摆满了花圈。见此情景,我没有停留太久就告辞了。
此后只要去上海都会抽空去看望朱永嘉。言谈间,感觉他和十年前大为不同,变得十分健谈。他和我谈毛泽东、谈“文革”、谈当前的时局和社会。他对毛泽东的崇拜程度比起“文革”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提醒我要把毛发动“文革”放到当年国际共运的背景下考察。他的本意是要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改革运动,但由于执行层面的偏差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了“文革”的失败。他痛恨眼下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认为这就证明了毛当年的担心并非多余。
但他没有牢骚,也没有激愤,更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这些年,朱永嘉开始将自己的经历和所思所想写成网络文字。我一次次鼓动他写书,后来替他出版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颇受好评。
因为谈及写书,才知道朱永嘉长期靠给台湾三民书局整理古籍维持生活,20元美金1000字。《唐六典》、《容斋随笔》、《春秋繁露》,一部接一部,几百万字下来,收入也算不错,但毕竟十分辛苦。2009年前后,我认识了上海金融投资界的一些精英。
他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但听说以往给他们讲课的大多是那些活跃在电视上的所谓明星学者,并没有领略过真正的学问。我想起朱永嘉,就推荐给他们每月讲一两次明史,讲课费不菲。讲完明史,又讲曹操,持续了两年多,朱永嘉的生活明显改善。他后来慢慢又红了起来,成了网络名人,各种出版社络绎不绝地登门,我也就不想再去凑热闹了。
朱永嘉有浓浓的“文革”情结,总想把“文革”合理化。在我看来,人到老了要否认自己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很难的。“文革”过去半个世纪了,他就算是个“文革遗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