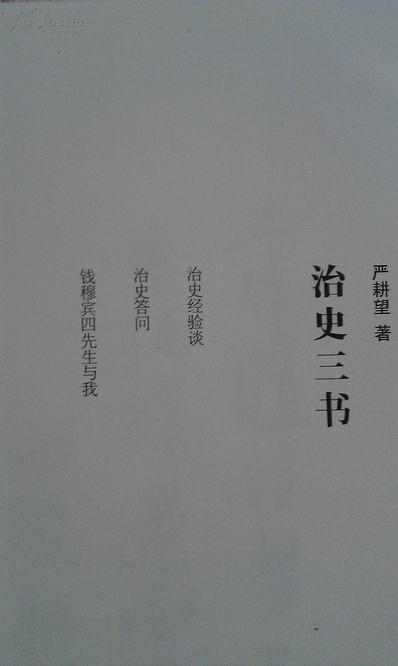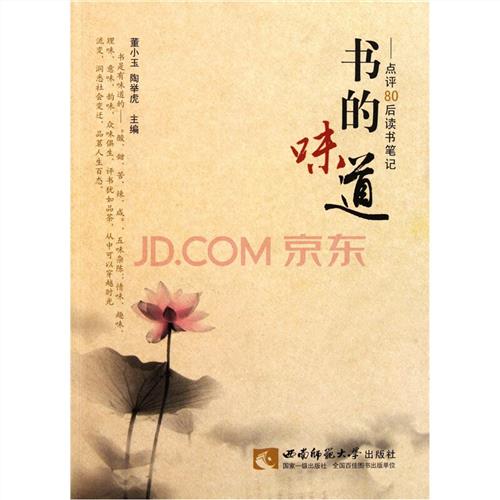严耕望光辉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充实而光辉
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里谈学术境界时说:“杨联陞兄是位学术批评家,好几年前曾称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成就,说‘充实而有光辉’;又曾转述胡适之先生称赞同一个人的成绩说‘精细而能见其大’。我想这两句话的内涵不完全相同,但意境实很相近。
这两句评语,某位史学工作者是否当之无愧,姑且不论;但我想借此两语作为史学论著的标准,却极为恰当。联陞兄的话本自《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语,原即寓有‘大’义。今就这两句话分析起来,‘见其大’可谓‘光辉’的一面,而‘精细’尤为‘充实’的最基本条件……”
又,严氏以后在一次访谈中也论及同一话题:“一九七一年一月杨莲生(按:即杨联陞)先生曾给我一封信,拿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一语作为衡量学术著作的标准。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本指德行修养而言,莲生先生转作评论学术论著的标准,非常恰当……”此处所言,正可与《治史经验谈》相参照。
按:假借“充实而有光辉”以形容学问,其实不自杨联陞始,明末清初名儒孙奇逢评说朱熹已谓:“文公(按:朱熹谥号)之学可称充实而有光辉矣,所谓集大成也。”
杨联陞以学术批评的严厉著称,在美国学界有“汉学警察”之号,他誉之为“充实而有光辉”者,真可谓登龙门。那么,这个同时被胡适、杨联陞推重备至的“某位史学工作者”,究竟为何方神圣?
实际上,被视为“充实而有光辉”的,正是严耕望本人。
胡适和杨联陞1950年代同寓美国,交往、通信都很多,1957年9月12日胡致杨函提及:“严耕望先生已到康桥(按:哈佛大学),来信说他‘既聋且哑,又兼半瞎’。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
望老兄特别指导他,使他的时间可以用在最有益处。”胡适函中所谓“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当然也就是杨联陞转告严氏的“精细而能见其大”;可证杨联陞“充实而有光辉”的评语,同样是对严耕望而发。
严氏对“充实而有光辉”作了相当透彻的疏解:“……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不过要达到‘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自非易事,最主要的做法仍是老生常谈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从小处着手,工作才能‘充实’;从大处着眼,成果才有‘光辉’。不从小处着手,势必大而化之,不切实际,漏洞必多,虽作出很动听、看来有光辉的结论,能吸引读者的注意;但终久未必能站得住脚,自不能算是真有光辉,更未必有长久价值可言。
不从大处着眼,就往往走上小路,钻牛角尖,不能脱困而出,结果成绩琐碎,不成大体系,自亦不能显现其光辉。不过此类论著仍较大而化之不切实际者为佳,因为这种论著是充实的,仍有其长久价值,不过境界不高耳。”作为朴实学风的楷模,严氏显然重“充实”
甚于重“光辉”,而以“充实”为根本。在“充实”的基础上,有“光辉”自然最好,即便达不到“光辉”之境,仍不失为“充实”;相反,假若没有“充实”作基础,则“光辉”亦不成其“光辉”,至多不过眩人眼目于一时耳。
今人论学,有所谓“学术”与“思想”的分野,正可借鉴严耕望关于“充实”与“光辉”的论说以作梳理:不能“充实”,则不足以言学术;没有思想,亦不可能有“光辉”。思想固然高明于学术———有思想的学术,要胜过无思想的学术;可是,学术必须优先于思想———学术虽小,思想虽大,但要先有学术,才进而谈得上思想;因为没有思想的学术仍是学术,而没有学术的思想,又哪里算得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