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岩松建筑不是造房子 马岩松:建筑不是造房子
设计师,1975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建筑学硕士。2004年回到中国,并成立了北京MAD建筑事务所。作品设计理念超前,代表作有《浮游之岛》、《胡同里的泡泡》等。
像所有刚刚步入“初老”的人一样,马岩松不介意,甚至是有点喜欢谈起他的老。他指指自己的头顶,那里仍是蓬然竖立之地,顶多夹杂了两三根白发。但他说,老了。他的眼神看起来也有点疲惫,不过他解释这和岁月无关—他把它归结为他刚刚结束的那趟迪拜之旅,在沙漠和扬尘中几天的暴走,以及来不及倒转的时差。
38岁的马岩松有时感觉自己已经活了很久,虽然在建筑界,他的岁数依然算得上相当年轻。绝大部分建筑师在他这个年纪仍然在勤恳地画着小区设计图,尚无可能独立担纲任何一件大型作品的设计(要知道这个圈子对经验和行业地位的依仗是如此之深),马岩松却已经以一个明星建筑师的形象在公众视野中活跃了十年。
马岩松从出道开始就是建筑界的金童,有人发明了一句话来形容他“成名趁早”这件事之于建筑界的小概率:在建筑界,想要30岁前成名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除非你是马岩松。
2004年,29岁的马岩松带着他辉煌的履历从美国学成归来,在北京创立了MAD建筑事务所。这份履历包括: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美国建筑师学会授予的建筑研究奖金,多个大牌事务所的工作经历(包括扎哈·哈迪德和埃森曼),以及“浮游之岛”。
“浮游之岛”是马岩松为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设计的方案,几根巨大的立柱顶起的一片蘑菇云,看起来像线条被扭曲了的古埃及神庙,或包含了神秘未来的天外来客。这项设计让纽约建筑界沸腾,也让马岩松这个中国名字第一次被争相谈论。
一片浮游之物,完全颠覆人们对重建建筑物的想象—要么仿照原形建筑物、要么庄严沉着纪念碑式?马岩松说,NO。年轻的马岩松认为,对9·11这样一场大灾难的反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纪念的层面,纽约不是华盛顿,不需要那么多的方尖纪念碑,匹配这里的是:发展—流动、活力和颠覆性。
马岩松对美国没有留恋,他一心想回到北京。他是北京人,从小在西城的胡同里长大,对这个城市有认真的感情。在马岩松看来,中国城市的大多数现代建筑是惨不忍睹的,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新建筑,“充满了对权力和资本的愚昧炫耀”。
所有的市政府都“矗在城市中心,附带一个巨大的广场,完全不是以人的尺度来丈量的”;法院前面永远“附带几十上百级台阶,特别傲慢”。库哈斯所设计的央视大楼,巨大、强硬、傲立在三环边的“大裤衩”—“只能说库哈斯深切地捕捉到了现实中国的现状,并粗暴地把它表现了出来。”
而在马岩松的理想中,北京这样一座城市,首先天安门广场就应该被改造成“天安门森林公园”,有大片的绿地,人们可以野餐、散步、慢跑。
带着这股天真的抱负,在最初的两年里,MAD工作室做了超过60个项目,工作量很大,却都只限于设计,没有一座能被盖起来。让马岩松在美国被肯定的狂想式设计风格成了他的作品在中国落地的阻碍,如何说服甲方接受他那些“异型”的方案,成了马岩松和MAD无能为力的事。
不过转机很快就到来了。2006年,马岩松和MAD拿下了“梦露大厦”—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一座56层公寓楼的设计权,成为了第一个为外国城市设计地标型建筑的中国设计师。为此,中国的媒体沸腾了,马岩松迅速成为了他们的宠儿,而他的高大形象和看似桀骜不驯的个人风格也十分适宜被塑造成一个明星式人物。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上能开明地理解并愿意为MAD的超前设计买单的甲方也瞬间多了起来。
但在马岩松看来,最初的那两年半并非白过。建筑师不是造房子的人,房子只是房子,建筑师却让房子说话。所以重要的不是实体的房子,而是发声的能力,那些建成没建成的房子都在说—只是有些传播得更远,更加流畅。“就算头两年我们撑不下去,被主流排斥,或者吞噬,这是无法控制的。
但是,有必要保持着对话的态度,与自己对话,与市场对话,与未来对话。电影没人掏钱看就失败了,但建筑没人掏钱盖是很正常的事。有时候就算是在纸上,它也会产生文化影响力,这未必不是一种成功。”
而到了现在,即使MAD的工作量已经非常饱和,马岩松每年仍要坚持做大量“不盖”的设计。“梁思成的特殊性不在于他盖了什么,而是他对城市有着更高层次的理想和规划。对我来说,现在做这些‘不盖’的设计就是对更高层次城市理想的一种探索,有时候,一件完美的建筑产品并不及一个幼稚而具探索性的概念更有价值。”
南都周刊×马岩松
不是保护传统,而是保护未来
南都周刊:北兵马司胡同里有你做的“胡同里的泡泡”。这个作品看上去很有意思,但在一条古老的胡同里,也会有一点点突兀。你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某种内在的和谐?
马岩松: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作品时,隔壁有个邻居是法国人,他天天来抗议,说这里是老北京,四合院,你们怎么能建这么奇形怪状的一个东西。结果建完后,他天天过来蹭(笑)。这个泡泡它是一个卫生间,老北京的四合院是没有独立卫生间的,一条胡同的人共用那么一两个卫生间,在现代生活里,其实是极度不方便的。
所以这个泡泡首先是有功能性的。形式上它是新的—一个球形,外表还是透明的金属质感,但这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新,它并不附带文化层面的其他内涵,所以你说是突兀,我觉得是一种戏剧化,很单纯的形式上的戏剧化,会让人眼前一亮那种。
我用了不锈钢的材料做外立面,就是想把周围的环境都反射进去,所以你看着这个泡泡,能看到老北京的房子、屋檐、树、乌鸦和天井,而泡泡自己已经消失掉了。
我自己小时候就是四合院里长大的,老舍说得特别对,其实老北京的核心不是四合院的那个四合,而是院子,院子是什么,是空,有空的地方才会有自然、生活和人。
南都周刊:所以保护四合院,其实不应该只是保护那些建筑,而是保护里面住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
马岩松: 没错。建筑根本上就是人的问题,理想一点是人和自然,实际一点就是人和城市怎么相处的问题。老北京的房子,那些砖瓦、木头,它重要吗?我们要四合院,不是要一个永久性的石头或者墓碑啊,我们要的是一个生活。生活是真实的,你不能当里面这些人是群众演员似的,天天在里面演古代人是怎么生活,都21世纪了还没有抽水马桶。我们不能把他们跟现代生活隔绝。我觉得,不应该是保护传统,而是保护生活,保护未来。
南都周刊:但有时候现代生活又太大、太无孔不入了,它是吞噬性的。
马岩松:我觉得现代生活、包括高密度城市本身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高密度城市里充满了高速的低级复制。空洞、拥挤、缺乏灵魂。即使现在很多建筑提出要自然啊人文啊绿色环保啊,比如我去过的纽约一个新建好的摩天大厦,是绿色建筑,最绿最绿的了,花了很多钱也得了很多奖,大家都认为他是时代标志了,但这个楼的结构跟50年代的摩天大厦一模一样,我问里面工作的人,他还是想着赶紧下班离开这楼去郊外野餐晒太阳!
一个缺乏自然光、空调温度一度都不能变、以此来养护其中植物的绿色建筑,真的自然吗?
南都周刊:这几年你反复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并且在实践。广西的“假山”—这个名字很好玩,可以谈谈这个项目吗?
马岩松:山水是什么感觉?就是让建筑成为背景,能强调出在其中活动的人的尺度的空间。现代的大建筑很多时候像个雕塑,而缺少对人活动的情感上的呼应。“假山”是我们设计的一片几千户居民居住的高密度住宅区,所有的住户都面向海。一般这样的住宅区,会规划几十栋百米高楼。但我们设计的是一整座起伏的建筑,很长,就像一座连绵的山,所有住户都可以最大视野地观看海景。
在贵阳花溪我们还有一个设计,对自然的融合度比这个更加深。贵州都是山,自然环境里有很多梯田。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它会是城市新的CBD,我们就把它做成了梯田的模样。有层级,有山,有水,当然水是人工做出来的,但流动的水会给人一种层次感。
很多CBD跟实际的人没关系,它没有类似桥、小的平台、流水这些能让人相互交流的空间。我希望在这些大型建筑综合体中插入以景观为中心的点,让人们在这些点上与建筑和环境产生共鸣。一般没有人在大型、高密度的建筑中尝试这种设计方法,因为我们总是讨厌大建筑,大建筑不人性,它是政府或是有钱人建造的纪念碑,跟个体没有关系。
南都周刊:回国十年,你觉得大环境有什么变化,建筑师们个人的努力有没有让这个环境变得更有活力?
马岩松:这几年我北美欧洲都去了,还刚刚去了中东。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机会是全球最好的。这个好不同于5年、10年前—那时候纯粹是商业概念上的好,感觉有赚不完的钱。现在的中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有机会也有胆量、有文化的地方,当然不是所有地方,所有建筑师,但有这样的小环境。
中东有很多有钱的地方,但它处于完全没发现或者说不在乎自身传统价值的阶段,而西方一面非常焦虑一面又非常自大,他们有自己深信的价值观,已经熟透了,在这个层面很难有所变革了,剩下来的顶多是技术层面上的变革。而中国现在有了不错的小环境,价值观上有碰撞有变革,大环境呢,我觉得大环境不用太好,太好太顺了,反倒可能是个陷阱。
南都周刊:你心中理想的城市、建筑是什么样的?
马岩松:能消除建筑的阶层性,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受到尊重的空间。
(2013年10月,马岩松被尊尼获加蓝牌致敬为“中国变革者”,本次访谈籍此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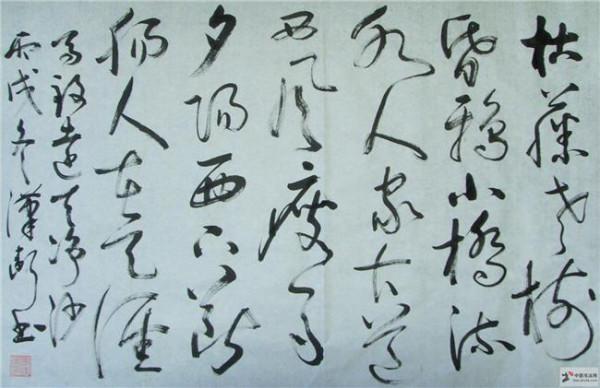
![>马继援夫人 [马继援的两位夫人]马继援的悲歌](https://pic.bilezu.com/upload/d/05/d05de4e95838c4db43fc99854cb56ea2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