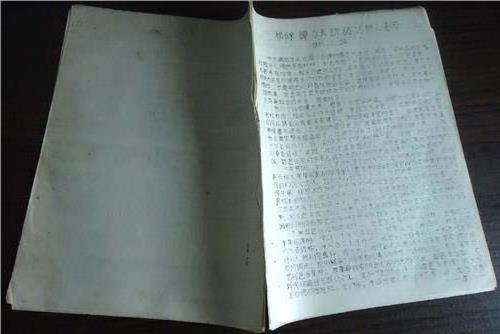胡宗南夫人回想录:我和他的爱 源于一张相片
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 ,字寿山,原名胡琴斋,是中华民国陆军一级大将。黄埔军校一期结业生,声称“天子门生榜首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首要的军事将领。1950年去台后,历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参谋等。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病逝。他与老婆叶霞翟相识于抗战前,却直到1947年才成婚,此刻新郎已51岁、新娘也34岁。
一九三〇年,叶霞翟与胡宗南因一张相片结下情缘;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他们互定终身。随后她远赴美国游学,他奋战在抗日前哨,可是二人没有遗忘彼此的约好。十年往后,他们终成眷属。赴台后,相伴十二年,胡宗南在她的随同下,度过了生命的究竟一刻。
图:叶霞翟与胡宗南新婚期间的留影
本书由叶霞翟编撰,叙说与胡宗南相爱、相伴三十年的日子点滴,文字温婉朴素,情感真诚动听。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出一个年代的沧桑剧变。
文
叶霞翟
悉数都是从一张相片开端。
那是一九三○年,我才十六岁。那年夏天,我考取了浙江大学农学院附设的高中——农高。和我一同考取的女同学总共只需三人,小姜、小朱、小江。我和小江是在入学考试时就知道了的。
因为投考的女同学很少,咱们又恰好在同一试场,注册往后,咱们请求编在同一睡房,天可是然地就变成好兄弟了。小江是宁波人,爸爸母亲仍住在家园,她的大哥是黄埔四期的,那时在杭州保安司令部做大队长,家在杭州清波门。
小江每个星期六都回家,有时也约我一同去。她的嫂嫂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子孙很多,会做一手好菜。她对我也像待自个的小妹通常,所以我很快就拿他们的家当自个的家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小江正在房里看小说,遽然听见一个粗重的男子声响在窗外问:“你们看啥书?”我昂首一看,窗外正站着一个又高又大的男子,三十光景的年岁,黄黄的长方脸,高鼻子厚嘴唇,两眼大而有神。
“看小说!”小江头都没抬地答复了一声,明显这位是他家的熟兄弟。
我觉得小江这么如同不太礼貌,就对他笑了一下作为招待,所以他问我看啥小说。我正在看托尔斯泰的《战役与平缓》,就把书向他扬了一扬,他问我是不是喜爱看翻译小说,我通知他啥小说都看。
实际上我正热衷于小说,分外是很多俄国小说如《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等都看了好几遍。所以他通知我,假设咱们喜爱看小说他可以借给咱们看,他那里啥都有。正本他是小江大哥的同期同学,那时在杭州《民国日报》任总修正,一个报馆的总修正家里,当然有很多书的。
小江听他说要借书给咱们看,喜好也来了,放下手里的书,开端和他谈天。
公然,这次往后他每次来江家都给咱们带书来,逐步地我也和他混熟了。他姓胡,咱们叫他胡大哥,因为他的肌肤分外黑,咱们又给他取了个绰号“老黑”。
咱们几乎每星期都要看两三部小说,日子久了,他也记不清哪些书是咱们看过的,哪些是没有看过的,有一次就提议最佳咱们自个去他家挑。那个周末,咱们从笕桥进城,叫了一辆人力车直接从车站到他家里。
身着便装的胡宗南将军
他有一个并不算大的书房,三面都是书架,只需靠右的一头有一空处,摆着一张大书桌,上面墙上挂着一张相片。我一走进入,还没有开端看书架上的书,就给那张相片招引住了。那是一个青年军官的相片,只见他身上穿戴规整的布戎衣,腿上打着绑腿,腰间束着皮带,姿态漂亮而英挺。那镶着军徽的军帽下是一张极为帅气的脸,浓黑的眉毛,炯炯发光的双眼,鼻梁高而挺,嘴唇紧锁但线条柔软而带笑意,站在那里悉数人是那么生动有神。
我对着它呆呆地看着,竟遗忘去找书了。站在我后边的主人,看我对那相片看得那么入迷,就笑着问我说:“你认得他吗?”
“不,不认得。”给他这一问,我俄然觉察到自个的失态,满脸绯红,期期艾艾地竟有点答不上话来了。他倒不介怀我的窘态,接下去说:“他是大大有名的胡师长,你们这些小姑娘不知道他,前方的武士可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报上有他的姓名吗?”
“怎么没有,你们看报只知道看副刊,看社会新闻,从不看国家大事,才不知道他呢!”
“你说他是师长,他看起来可很年青呀!”
“天然年青,他还只三十岁呢,他的晋级不是一步一步升,是跳着升的。”
“你如同对他很了解似的,他是你的好兄弟吗?”
“天然是,不是好兄弟他还会送我相片?你知道他是很少拿相片送人的。”他明显很振奋,也很欣慰,大概他对这位胡师长确很敬服,如今看我这小姑娘对他有喜好,想趁此刻机为他宣扬一番。我呢,心里也确是对相片中人很是钦羡。我想,他真是了不得的人物,这么年青就做了师长,风闻做师长要带好几千兵,够神情的。
记住咱们家园有一位孟明叔,是北伐军的团长,英勇善战,北伐时屡建奇功。三年前,他带着太太回乡省亲,县长主张了全县士绅、本地团队和两所县小的学生,在北门十里路外列队相迎,说是接革新军。咱们女子小学的校长,那位胖胖的张师母,还替孟明婶打着伞,陪着一同通过等候队伍,她那圆圆的脸上,充沛地表显露“我也有荣焉”的笑意。假设这位胡师长也到咱们家园去走一趟,县长不知道要忙成怎么个样儿啦。
所以,我又对胡大哥提出很多疑问,问他这位胡师长是啥本地人,啥身世。他通知我,胡师长是浙江人,和咱们是大同乡,黄埔军校榜首期的高才生,刚一结业就参与作战,跟随蒋总司令东征北伐通过了不少的战役。因为他作战英勇而又很有谋略,每次作战都得成功,人家称他“常胜将军”。
打到上海时,他已升为榜首师第二团团长,他带着一团兵由闵行偷渡黄浦江,占据了莘庄、龙华和上海兵工厂,进而克复上海,把国旗插遍全市。
进入上海的那一天,他调集全团官长,随带配备卫士,乘坐敞篷汽车,直入法大马路、爱多亚路、跑马厅、南京路等火热大街,绕行大上海一星期,所通过的本地,人潮汹涌,民众夹道喝彩。
正本这些本地都是租界,咱们自个的戎行是不能进入的,他这一次以“不行一世”的气势,阵型堂堂、气势汹汹地长驱而入,租界巡捕看到这威武的景象也不敢出来阻扰了。这次不光替上海的百万居民出了一口气,更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从此国民革新军威震中外,全国际的人对咱们都另眼看待了。
胡大哥愈说愈起劲,我愈听愈入神,那天回家往后,一贯想着那张相片上的人,以及关于他的各种故事,心里想:假设他是我的哥哥多好。
记住那次孟明叔回乡后来看爸爸,爸爸曾拍着他的膀子说:“孟明,桑梓以有你这么的后辈为荣,咱们老迈将来大学结业往后,我要把他送到你那里去锻炼锻炼,俾便能为国家尽点力。”
如今大哥快要大学结业了,可是他是学经济的,哪里能举宝刀以卫社稷呢?真期望有时机能见到这位胡师长,看看他究竟是怎么个英勇姿态。
从那次往后,我常常鼓动小江和我去胡大哥那里借书,趁便看看那张相片,有时机就请他再讲些胡师长的故事。一同也开端留意报纸上的国家大事,国内要闻。公然,“全国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不光常常会从报纸上发现胡师长的姓名,也听到很多人的口中谈到他的各种传奇故事了。
他们说他不光会交兵,更会带兵,他对兵士就像对自个亲兄弟通常,兵士吃啥他吃啥,兵士穿啥他穿啥。风闻当革新军北伐之初有“十不怕”的标语,即是“不怕死、不怕险、不怕饥、不怕穷、不怕远、不怕疲、不怕苦、不怕痛、不怕硬、不怕冻”,这位胡师长十项都做到了。
因为各种的风闻,我对他的形象愈来愈深,景仰之心也愈来愈切,总期望有时机能见到他。可是,直到我高中结业,都没有遇到这个时机。
结业往后我去上海念大学,大学生的日子是安闲生动的,分外是像我这么对比喜爱课外活动的人,和男同学触摸的时机更多,可是,谁也没有使我动心。人家说姻缘是宿世注定的,或许月下白叟的红线现已把我和他连在一同了。
在我念大三的那年春天,我和绮嫂去杭州省亲,一天早上,我去教师那里,他正在楼上处理要公,叫我在楼下客厅等一下。客厅外面是个大花园,那恰是百花吐艳的时分,我就倚在窗边欣赏着园里的风光。
过了不久,听见后边响起了脚步声,以为是教师下来了,回头一看,进来的却是个生疏人。他穿戴深灰色的哔叽中山装,中等身段,方脸宽额,浓眉大眼,鼻梁很直,嘴形很美,面色白里透红,下巴青青一片,明显是刚修过脸的。
当我和他的眼光一触摸时,就像一道亮光射进我的心里,立刻感到脸红耳赤、心头乱跳,一同觉得这自个如同是啥本地看见过的,究竟是谁却想不起来了。为了粉饰窘态,我只好又回过头去持续望向窗外。
他呢,既没有退出去也没有坐下,如同立刻就绕着客厅里的那长方桌开端踱起方步来了。又过了好一片刻间,当我等得有点不耐心的时分,又有脚步声到客厅门口,我以为这一次必定是教师了,急速转过身来。进来的却是王副官。王副官对那位客人笑笑,然后很恭敬地说:“军长,先生请你上楼去。”
“唔,好!”他口里应着,脚步已跨出客厅,只听见几步楼梯声就寂然了,我想他走楼梯必定不是一步步走上去而是越级跳上去的。他出去往后,我已无心再看风光,随意在门边一张沙发上坐下,感到心慌意乱地真想跑掉了。
随后,教师总算下来了,方才那位客人也跟在他后边。他一进来就很快乐地对我说:“你来得恰好,我给你介绍一位兄弟。”然后指着那位现已站在他周围的客人说:“这位是胡军长。”又看着客人指指我说:“这位是叶小姐。”
等咱们坐下来后,教师问了我一些校园的景象以及我来杭州的事,又通知我他正午就要去南京,因为那儿打电报来有要紧的事要他当天赶去。究竟他对我说:“这位胡军长是我的好兄弟,他的学识好得很,你可以多多地讨教他。”然后又对胡军长说:“大哥,我还要上去理一下东西,你们谈谈吧。”说着,没等他作任何表明就仓促跑出去了。
客厅里只剩余咱们两自个,这时我现已知道来客是谁了。正本,这几年他已从师长升到军长,他的姿态有点像那张相片,又有点不像,时刻相隔七八年,人的姿态是会变的。
我觉得他的人比相片更有精力。七八年来我一贯想着他,想知道他,如今,咱们总算面临面了,我将对他说啥好呢?我能通知他,他是我梦里的英豪吗?我能对他表明我私心的渴仰吗?
究竟,我已不再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了呵。我脸红心跳,不知所措,不知怎么是好。幸而他倒很能掌握状况,教师一走,他就立刻移坐到离我较近的一张椅子上来,用温文而亲热的口吻对我说:“叶小姐,风闻你如今在上海念书,念几年级了?”
“三年级。”
“念哪一系?”
“政治经济系。”
“呵,小姐念政治,可了不得,将来必定是个女政治家。”
“哪里,哪里,念政治是最没长进的。”
所以他又问了我很多校园方面的疑问,这些疑问最简略谈,也最不会开罪人,逐步地我的心安静下来,心境也天然了。比及二非常钟谈下来,咱们已不再感到生疏。后来他说要等着送我教师去车站,问我要不要一道去,我心里是想说“不”的,口里却说“是”。
那时时刻还早,他提议咱们先去邻近湖滨公园散漫步,我心里想,刚刚知道怎么可以和他一同出去漫步,正推托间,郑先生来了。郑先生是知道我也知道胡军长的,不知道是有意仍是无意,他听见胡军长说出去漫步的事,急速对我说:“来,来,咱们一同出去逛逛。”因有郑先生同去,我也就不再推托了。出得门来,三自个有说有笑地从榜首公园一贯走到民众教育馆。
那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恰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莺飞的时分,湖滨公园桃花怒放,香风阵阵,吹人欲醉。我走在他们两人基地,有些振奋也有些迷乱,脚步有点飘飘荡荡的,像走在云里,其时遽然想到小江,很期望能在路上遽然遇到她。她知道我对相片里的那位英豪有着一份分外的豪情,假设她看见我竟真的和他在一同,将是多么惊喜。
一小时往后,咱们回到第宅陪教师一同去车站。车站里人潮汹涌,如同还有些部队上车,胡军长没有和咱们同车,我想或许他还要送行的人。车开动了,我向教师的秘书何小姐挥手送行,教师是向来不喜爱这些婆婆母亲式的动作的,一上车他就进入自个预定的房间,持续处理公事去了。
“叶小姐,我送你回去吧!”当我看着何小姐的手帕在远去的车窗消逝后,正回身要走时,忽听得后边有人对我这么说。不知道在啥时分,这位将军竟又回来了。我觉得有点欠善意思,急速说:“不了,谢谢您,我自个回去。”他如同没听见我的话相同,跟着我朝车站出口的方向跑。
我想,比及了车站门口再说吧。出得站来,前面正停着一辆黑色汽车,我想这车或许是他的,但又不敢判定,心里想在快抵达车子时向他握手推托。哪知当咱们走到离车子还有几步间隔的时分,他却一个箭步跑到车旁把车门翻开了。
我感到很是为难,口里叽叽咕咕地像是又说了一两句推托的话,但他并不理睬,仅仅笑嘻嘻地用他那空着的左手很天然地把我挽上了车。我想,这几乎是软性的绑票嘛!全国竟有这种强要送客的事,虽这么想,心里却是很快乐。
到了家门口,已是吃中饭的时分,我想请他进入就餐,又欠善意思,究竟咱们知道还不到三小时,只好谢谢他就算了。他也没有啥表明,只说了一声“再会”就叫司机把车开走了。他走了往后,我又有点失悔,觉得或许自个对他太冷酷了,开罪了他。
就餐时,绮嫂问我这半响的景象我都懒得讲,只说去车站送了教师,仓促吃了半碗饭就跑到房里关起房门,想安静一下,使脑筋喧嚣一点,把那失调的思绪理理了解。谁知刚进到房里,外面的门铃就响了。女佣来陈述,外面有客要见二小姐。
他已换穿一套西装,心境洒脱儒雅,真实不像通常人所愿望的武士。他问我有没有喜好去游湖或漫步,我觉得有点累,不想出去,提议就在家里谈谈。他也乐于承受,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从杭州的气候谈到西湖的风光,再从西湖风光谈到有关西湖十景的各种典故。
正本他是老杭州,在杭高念过书的,对杭州景象非常了解。尽管我也在杭州念过三年书,还将杭州作为第二故土,和他比,却像个生疏人了。他是那么善谈,说话的声响平缓而有力,双眼充溢着豪情,当你听他说话,看着他的表情,是不能不被招引的。
坐到天快黑的时分,他看看表,说是有人请他吃晚饭,才快乐地辞去。
这几天心境略为安静,回想起曩昔的一百单纯像是做了一个悠长的噩梦,可偏又不是梦,如真的是梦倒好了,梦醒后悉数仍是夸姣的,而我所面临的却是永久无法抵偿的缺陷啊!
一九六二年六月,数百位亲朋随同我和孩子送将军于阳明山上的纱帽山麓,墓庐依山面海而筑,他在那里可以看见海那儿的家园。送他那天黄昏,我站立墓前,俯仰之间,但觉六合悠悠,沧海苍茫,三十年年月,仅仅一梦。
记住当南兄那么骤不及防地脱离人世时,我真是遽然从桃红柳绿、绿草如茵的田野坠下了漆黑恐惧的万丈深渊。迷乱、失望,极度的哀痛使我变呆了,脑子是那么乱糟糟的,对事物彻底失掉了解力,情感也干涸了,乃至连母爱的天分都隐没了,感到人人间的悉数都毫无含义。
有时分,自个都在置疑,为啥还要活下去,日子过得昏昏沉沉,就像一架机器人似的抵挡着往常的日子。白日,悉数都是乱糟糟的,很多的兄弟来看我,人像潮水似的涌进涌出,每自个来谈的都是同一个标题,南兄的死。
起先,只需一提到,眼泪就会不自觉地流出来,真可以说是整日地以泪洗脸,后来连泪泉也像干涸了,提到哀痛处只感胸口发闷,嗓子哽塞,双眼是干涩的。夜里亲戚兄弟都走了,孩子们也睡了,剩余我一自个,静谧使我的思维开端生动,所以就仔细心细回想着南兄抱病的通过,在医院里的各种景象,医师对我所说的话,越想越不信赖他是真的死了。
只病了那么短的时刻,不久早年仍是生龙活虎似的,即是在病中也是脑筋了解,决心刚强的,在我的心中向来都没有一点点他会死去的阴影,即是去的当天黑夜咱们仍是说笑着的呀,这教我怎么可以面临实习?怎么可以甘愿?一百个疑问回旋扭转在我的脑中使我无法合眼。
可是实际终归是实际,他确是不在我身边了,比及那究竟的疑团也不存在时,我的心死了。俗语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死了的人确是意外,我正本是一个有多种喜好的人,爱花、爱树、爱音乐、爱看影片、爱读小说,也爱和兄弟谈天,可是到了那时却对啥都不发作喜好了。
在我书房的窗前有株扶桑,它那绿莹莹的叶子和缀满枝头的红花常常是我创意的源泉,有时当我伏案写作时,想不出佳句就昂首向它看看,欣赏一片刻间往后好句就从笔尖出来了。后来几番春雨后它的叶更绿了,花更红了,但我这赏花人却无心去欣赏了。
我那小小的宅院里种有几株茉莉和杜鹃,也有好几盆兰花和菊花,曩昔,拔草、洒水都是我往常的作业。自从南兄身后,我再也无心去照料,任它花谢、叶枯,一条小径长满了荒草,我偶然在那里走过,也懒得去看一眼。
我并不了解音乐,但喜爱听,往常在晚饭往后,总要叫孩子们放几张唱片听听的,这时分对它却一无好感,只需孩子们一翻开收音机或放一下唱片,就觉得心里烦乱不胜,叫他们急忙关掉。那些雄壮的交响乐章,那些悠扬歌喉,关于一个孤寂苍凉的心,如同都不能沟通了。
书报正本是我天天不行或缺的精力食粮,这时分我对它们也没有食欲了。有时,夜深人静,穷极无聊,我也会随手拿过堆积在案头的报纸翻开来看看,但那些国际要闻、国家大事,对我都无关了,再大的标题在我的心目中仅仅几个大号的铅字。
至于书,我也很少摸了。在这期间也早年接到过几位兄弟自个写的著作,他们是期望我可以从那些书中得到安慰的,可是我拿到往后,翻开来看了一下,或许还不到三行,我的心就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有时分会在一页书上停留个半小时,而对书上的意思仍是一点不了解,究竟只好翻两下就摆开一旁,真不知孤负了兄弟们几何善意呢!
对物如此,对人又何曾不相同,多么古怪啊,一自个哀痛到极点时竟连被爱和爱人的才干都丧失了。亲人、老友,她们对我说了多少抚慰的话,流了多少怜惜和怜惜的眼泪,尽管那些言语和眼泪也曾使我的心灵微颤,但再真的豪情如同都无法穿透这颗严寒的心了。
他们在面前时我仍是会哭、会诉,他们一走,我就觉得苍茫然了,在那么多天里,多少的友谊和爱心,都不能给我一点安慰。
最可悲的是我连自个的孩子也不爱了。
曩昔我的大有些的时刻和精力都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笑声是我快乐的源泉,他们的成果是我最大的安慰,只需他们健康生动,他们读书成果好,我就心满足足,觉得这国际诚心爱,做人真有意思,假设他们有点感冒咳嗽或别的的小缺陷,我就忐忑不安心乱如麻,惶惶不行整天。
我每日一早起来亲身为他们准备早点,亲身送他们上学,下午核算着时刻等他们放学回家照料他们吃晚饭,黑夜敦促他们做功课,安排他们睡觉,星期假日我向来没有为自个安排节目,为的是要空出时刻带小孩出去玩。
南兄常常笑我,说我像个老母鸡带领一群小鸡,我自个也供认,我的保护子孙真实不亚于天分慈祥的动物,哪知道南兄一死,我会变得那么凶猛,竟连自个的孩子也不知道珍惜了呢!那时分我不光已无心照料他们的功课和起居休息,对他们的悉数也如同不再关心了。
意外的孩子们,没有了爸爸,又几乎失掉了母亲!当我最哀痛的时分,即是他们亲亲热热地来到我身边,悄然地叫着“母亲”,我也仅仅对他们看看,点允许,心里却无亲热之感。我的悲痛和冷酷使得孩子们莫衷一是了。
大的两个只好把自个关在斗室间里,静心在书本上,他们已不再去打球,不再去下棋,不再去找兄弟们玩,也不再翻开收音机听故事了。小的两个,分外是最小的理解,向来是和我很挨近,老是挨在跟前的,这时分看我对他们那种漠不关心的姿态,就不敢再到面前来。
很多亲戚兄弟怜他们幼小,都自动来照料他们,带他们出去,买东西给他们吃。这种日子上的骤变,和太多的照料和关心反使得他们不知怎么习惯才好,在很短的时刻内日子习气都变了。他们已不再像曩昔那么文静听话,他们的脾气变得很坏,常常哭闹,还会打人谩骂,有时当我听见他们在那里大声叫嚣或对人无礼时,也想去经验他们一番,但都提不起精力,只好让他们去了。
在这段时刻内仅有系住我心,使我持续生计下去的因素即是南兄的棺木还停在殡仪馆,我想:“他的魂灵虽已上天,他的身体还在那里边,只需我能挨近他一天,我就要挨近一天。”
因而,天天一天亮我就急思考往殡仪馆去。我无意梳妆也无心就餐,只等孩子们一去上学就立刻跟着出门,有时因为客人或别的的事使我不能趁早前去,我就心急如焚,连人家问我的话也会答非所问,他们以为我哀痛过度精力恍惚,反而坐下多方抚慰,哪知他们的善意反给我心更大的折磨!
到了灵堂我的心就安了,我的确地觉得他的存在,如没有他人在旁,我会用我的头依托着棺材的一边,流着泪向他细细倾吐。
我对他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尽的想念,如同咱们又回到爱情期间了,在那里时刻是永久不行长的,通常已中午我并无意离去,总要他人一再敦促才牵强举步,每次临走时我都抚棺和他说:“明天见,亲爱的!”尽管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愿望着他必定会浅笑允许的!
后来他的墓快修好了。我开端着急不安,我知道连这点挨近的时机也将没有了。我心里真不情愿把他送得再远一点。可是咱们都说落土为安,仍是早点安葬的好,我虽是一千个不情愿但又怕人家说我不通道理,说我自私,说我会使他的魂创意到不安。
想着他活着的时分,每次他出远门时我都是心里舍不得,脸上却只好装着泰然自若般送他走。如今,这是究竟一次的行程了,我这做老婆的,是不是也应当英勇一点呢!天啊,做一个英勇的老婆是多么的不简略啊!
总算在六月的一个早晨,我披上黑纱送他上山,送他到究竟的安眠地址了,当我眼看着砌墓的工人把究竟的一块砖头封住墓门时,真是恨不得自个也能从那夹缝里钻进入和他一同封在里边呢!
在他安葬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没有本地好去了,苍茫然无处着落,只好把自个关在客厅里对着他的相片发愣。一片刻间客厅的门开了,老迈悄然地走到我身边,亲热地叫了一声“妈”,接着别的三个也进来了。
德德拉着我的手问:“妈,您今日不出去了吧?”美美靠着我的膀子说:“妈,我真想你呢!”站在后边的小明,一瞬间投入我的怀里,用她的小胳膊围着我的头颈说:“妈我喜爱你,我真爱你啊!”
这一连串的稚气而香甜的声响总算感动我这空无的心了,我昂首看看他们,才发觉他们都变样了,他们的头发是那么长,气色那么青,一个个又瘦又黄,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像泉流般的涌出来了,我翻开两臂把他们四人都搂在一同,语音颤抖地对他们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宝物,母亲爱你们,母亲也真的爱你们啊!”
所以孩子们也哭了,母子五人哭作一团,意外自从爸爸身后,这仍是我榜初度想到孩子,为了孩子而哭呢。就在这一片刻,我的心也跟着母爱的复生而复生了。
一道亮光照亮了我的心灵,如同有一个声响在对我说:“你有必要振奋起来,爱他们照料他们,你老公的生命并没有死,他的生命就存放在这四个麦苗身上呀!”
当我再昂首起来看着南兄的相片时,我看见他在向我浅笑,像是在对我说:“霞妹,我真快乐你总算领会了,尔后你要刚强起来,好好教养这四个孩子,要知道只需他们将来有长进,你我的生命也会持续地放着光芒的。”
如今又一个多月过下来了,这些日子里我在企图振奋,愿天主给我力气,使我能担负得起将来的这副重担。
一九三九年因抗日战役延误婚期,我远渡重洋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
叶霞翟(1914~1981),1947年春与胡宗南成婚,台湾闻名教育家、散文家。上海光华大学结业,获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学士学位,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光华大学、金陵大学。1949年下一任台湾教育有些特约编纂,台北师范专科校园校长,退休后专任文明大学家政研讨所所长。著有《家政概论》《家政学》,论文集《婚姻与家庭》《主妇与青年》,散文集《武士之子》《山上山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