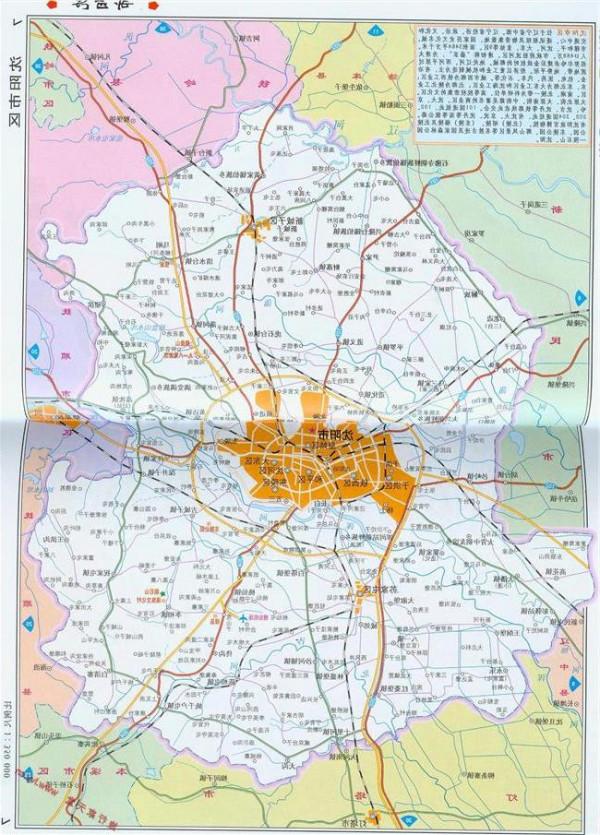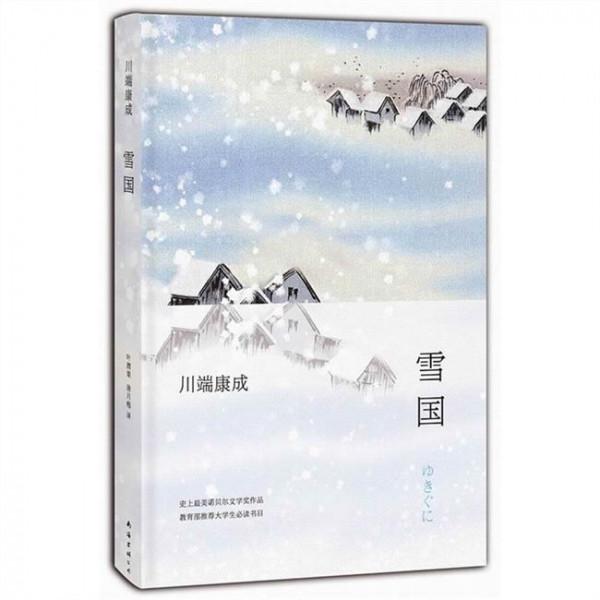叶渭渠唐月梅 叶渭渠与唐月梅(陈喜儒)
我是叶渭渠、唐月梅夫妇的忠实读者,读过他们许多书。
读得最多的是他们翻译或主编的日本小说,如《浮华世家》《井上靖小说选》《川端康成小说选》《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等等。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文坛有深远影响又颇多争议的作家,在我国,学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激烈。
老叶和老唐既翻译,也研究,老叶写了《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老唐写了《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他们汇集梳理有关文献,认真阅读、研究、分析作品,从中国学者的视点立场出发,阐述这两个作家的长短得失,冷静客观地作出了全面评价。
其次是读老叶老唐著的日本文学史。我长期从事对日文学交流工作,接触过如野间宏、井上靖、水上勉、松本清张、加藤周一、尾崎秀树、黑井千次、高井有一、秋山骏等日本大作家。他们知识渊博,学养深厚,旁征博引,海阔天空。
与他们交往,我深感学养不足,比如谈及某作家某作品中的某人物,如果你没读过这部作品,就没法进行深入交流。为了适应工作,加强自身修养,我于是发奋补课。我首先想到的是读日本文学史,希望对日本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有个整体把握,在历史的经纬中,了解作家和作品。
当时,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和创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一本是松原新一等著《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这两本书虽各有所长,使我大体了解了日本文学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但毕竟都是日本史家之言。中国学者怎么看?这是我十分渴望听到的声音。
后来,我陆续读了叶、唐合著的《日本文学史》(现代卷·近代卷)、《20世纪日本文学史》、《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还有唐先生的《日本戏剧史》等,受益匪浅。他们从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出发,探索各种文学的形式、内容、流派、思潮的产生和演变,清晰地描绘岀了日本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最初是怎样认识老唐和老叶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在中日作家座谈会上,他们夫妇应邀参加,但说话不多,尤其是老叶,似乎讷于言,总是静静地听别人发言,所以印象不深。相熟起来,是他们夫妇当编辑的时候。我从1980年开始尝试业余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先是翻了几篇散文,发表在文艺刊物上。
1982年我去北海道访问时,认识了三浦绫子,她给了我很多书,希望我向中国读者介绍。回国后,我抽空译了她的中篇小说《逃亡》,寄给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的老叶,不久老叶来电话说:“稿子看过了,觉得不错,老唐也很欣赏。
《外国文学》是季刊,间隔较长,老唐想发在双月刊《世界文学》上,不知你是否同意?”我当然是喜出望外。在我的心目中,《世界文学》是当时译介外国文学最权威的刊物,身为初学的译者,根本不敢投稿,没想到歪打正着。
这是我在《世界文学》发表的第一篇译作(1983年第五期),从此才有了给《世界文学》投稿的勇气。后来这篇译文又有幸被老唐收入世界文学小丛书《风雪》(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中。
从那以后,他们可能觉得我“干活儿”老实认真,不时邀我参加他们主编的系列丛书,我因工作忙,只参加了两次。一次是翻译宫本辉的《萤川》,由老唐编入《获日本芥川奖作家作品选》;一次是翻译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速写》,由老叶编入《东瀛美文之旅丛书》。我退休后,他们鼓励我搞些研究,我说起步太晚,难有作为。老唐说:“不晚不晚,我们的一些项目,就是退休后开始的。但这种日子太苦,你要有思想准备。当然,苦中也有乐……”
相识二十多年,清淡如水,虽同住一个城市,也很少见面,只是偶尔通个电话而已,但他们对于我这个日本文学的业余爱好者、译者,总是鼓励、帮助、提携。
他们集编辑、学者、翻译、创作于一身,刻苦笔耕,出版的书籍已有二百多册。几年前,看到一篇记者采访文章,提到了两个细节,至今不忘。一是1952年,他们俩从南洋回北京,住在不同的招待所准备高考。中秋夜,他用所剩无几的钱买了一块月饼,约她到东单公园赏月。
在如水的月光下,一对恋人分享一块月饼。二是他们考入同一个班级,又分配到同一个机关,“文革”时,有人指责他们“一个鼻孔出气”,他大惑不解,发出了书生困惑的诘问:难道夫妻非要两个鼻孔出气才好吗?看到这里,我不由得笑出声来。他们是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也是志同道合的学者,可以说,他们的学术成就,也是他们忠贞爱情的结晶。
他们怀着拳拳报囯之心,由湄公河畔归来,与祖国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至今痴心不改。老叶在多年前写的《历访香江》一文中说:当我漫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回顾在电视上看到的回归仪式的情景,我仿佛进入了1952年路过香港,跨过罗湖桥投入祖国怀抱时的那种喜悦雀跃的心境中。那时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如今是七旬有余的老头,但自我感觉全身流动着的血,仍是那样的热,那样的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