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诗词中的旷达情怀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了1000年的12位英雄,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等,其中惟一入选的中国人是苏轼。《世界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一个中国人的生平,尚属首次。苏轼缘何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关、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仕途坎坷,宦海沉浮,但他却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向世人展示了其独特的魅力,为后人留下厚重的精神财富。一、探究旷达情怀产生的渊源
(一)性格的形成
要探索苏轼的人生情怀,须了解其性格的早期形成。苏洵对其二子的脾性甚是了解,这从他给二子的命名可知。他在《名二子说》中,阐明为子取名的缘由:“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轼”是车厢前端供扶手的横木,暴露于外。“辙”是车轮碾过的印迹,既无行车之功,也免翻车之祸。取“轼”以体现苏轼率直外向的性格,取“辙”表示苏辙的平和深沉。苏洵的这个判断在苏轼、苏辙身上得以应验。苏轼锋芒外露,个性真挚坦率,“临事必以正,不能俯抑随俗”。苏轼正直的性格与其家庭教育分不开,他的母亲非常注重苏轼的人格教育。在《宋史·苏轼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日:‘轼若为暗,母许之否乎?’程氏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少年时代就向往像范滂一样,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决不逃避。
其弟苏辙在为苏轼所写的墓志铭中也提及苏轼性格形成的一个原因,“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庄子旷达超脱、任性逍遥的思想促成了苏轼“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性格的形成。正是这种性格,支撑着苏轼在极度失意的仕途中却从未倒下,用道家的超脱与旷达的精神主宰他的词风。
(二)佛禅释的影响
苏轼诗词所表现的宽阔胸襟与豁达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轼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
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和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
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终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他一生都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委曲求全,不迎合时俗,不跟风,不苟从。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朝,他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便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他心中“望美人”(《前赤壁赋》)垂顾的期望一直未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也时时撞击心扉。
在面临官场的挫折与劫难后,苏轼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被贬黄州之后,基于对命运的反思,开始对佛教进行认真的研读。
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说:“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所谓“静”、“达”,就是身在黄州的苏轼对佛学的期许,那象征着佛教空静与达观的境界,就是既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又要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善于开解心结,转换心态,勇于面对挫折磨难。道家的“真”,也是苏轼评价一切的准则。苏轼的主体人格有一种独立于世的品质,一种超逸绝尘的性情,因而不苟于流俗。苏轼乐天知命的思想来源于庄子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的观点。知命,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尽人事直到无可奈何而后已。乐天,是一种无信誉外物,不受外物所累,随遇而安的处世观。
因而,素食一生既能竭尽人事,又能随遇而安,无往而不乐。
二、解读旷达情怀的内涵
“旷达”,是一种洒脱、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内涵是指解脱、超越,改变固有的观念,换个角度看问题,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发现事物的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苏轼旷达情怀中难能可贵的是在三次贬谪、多次流放中仍表现出安然处之,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
(一)吟咏自然,享受清风明月般的恬然自安
苏轼描写大自然的词,取材广阔,意境深远。在对大自然的吟咏中,也表现出摆脱自我、融入自然的旷达境界。“让自己有限人生在大自然无始无终的运动中得到永恒;让人生的种种苦恼在超乎现实的纯美的大自然中得到解脱;让自己从与社会的种种矛盾中净化出来,与大自然天造地设的规律相和谐。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
1.放情山水,忘怀物我
苏轼因乌台诗案,谪贬黄州,住在临皋亭。后来又在不远处开垦一片荒地,种上庄稼树木,名之曰“东坡”。对于经历了一场严重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他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精神。他有时布衣芒屩,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他要从大自然中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
他在《西江月》中写归途所见:“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先说“照野”,突出地点明了月色之佳。用“弥弥”形容“浅浪”,就把春水涨满,溪流汩汩的景象表现出来了。
广阔的天空还有淡淡的云层。“横空”,写出了天宇之广。野外是广袤的,天宇是寥廓的,溪水是清澈的,在明月朗照之下的人间仙境中,诗人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这首小词,反映苏轼在黄州的放旷生活,写景之中,处处有“我”,“我”之情怀,即在景中。写于同时期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读完上片,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位风神萧散的人物,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在这安恬幽美的夜晚,他醉复醒,醒复醉,恣意所适;时间于他,三更,四更,无所不可;深夜归来,敲门不应,坦然处之。
清代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对于历尽宦海沉浮、九死一生的苏轼来说,现在置身于这宁静、旷阔的大自然中,物我两忘,自然超适。
2.寄寓物象,彰显人格
苏词咏物,不但重形似,而且重神似,不但能写出物象,而且能写出高远寄托和旷达情怀。苏轼词中常咏月、咏梅、咏鸿,用这些寓意高远的自然物象来表现自己傲世独立的旷达之情。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红梅》)词中把红梅人格化,也是苏轼的自我独白。他发掘和升华了自然界所塑造的梅花凌寒不屈、迎风斗雪的品格——“梅格”,即使泛点红色,但冰容玉质未肯迎合时俗。
苏轼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受融入到对梅花的描写中,把自身的思想和人生理想寓于“梅”的形象之中,让“梅”成为自己人生际遇和人格的代言物。苏轼还借孤鸿表明心志,“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卜算子》)这里用孤鸿衬托,足以表达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语)。“孤鸿”不仅表现了某种人生哲理,而且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具体地说,孤鸿的超世拔俗、高举独行正是词人自我人格的写照,同时也蕴含了一种人生如幻的哲理,“杳杳而没,不计东西”。还有透露出人生只是个悠悠长途,所经所历不过是鸿飞千里行程中的暂时歇脚,不是终点和目的地,总有希望和未来。
可见,苏轼在承认人生悲哀的前提下,又始终追求人生的自由;在面对人生的缺憾时,会提出了强烈而美好的愿望,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二)躬自反省,积极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苏轼成为新党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的劫难。被贬黄州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苏轼一方面积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一方面认真反思性格上的弱点,“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答李端叔书)他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艰苦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要努力创造出兴味盎然的生活。
例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原是生活中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但其深层蕴含,却是词人的处世态度。词的上片写冒雨而行的心情,在铺天盖地的骤雨袭击下,诗人仍是那样的安闲自若:“一蓑烟雨任平生”,活脱出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仙人形象。词下片写雨后景物和感受,骤雨已过,云开天晴,春风料峭,夕阳斜照,而酒意早已飘散。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出苏轼不畏人生坎坷,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怀。
也正因为这种情怀,从元丰五年七月到十月,苏轼在黄州赤壁的三次歌咏,成为千古绝唱。《前赤壁赋》中的一番主客对话:“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诗人用明月和江水比喻人生,揭示人生的两方面:一方面,生命渺小、短暂,不可挽救的逝去;另一方面,生命又是永恒的。江水东流,明月亏缺,但是水流不断,月缺又月圆。每个生命都与江水、明月一样长存天地。苏轼走出了历代文人对人生短暂的感伤,领悟到只要将自己的每一分投入到自然界无限的境界中,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抒写用心咀嚼的文字,便是永生、永恒。
古人曾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对于此时的苏轼来说,立言成为他在黄州时期实现不朽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身在逆境,他总能把稍纵即逝的感受,把对人生坚定不渝的信念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使之永留人间,使生命焕发光辉。
(三)通达事理,营建自得其乐的精神家园
苏轼遇事通达,能从多角度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使自己不陷于政治的漩涡、不沉于苦难的深渊,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追求。
被贬惠州、儋州意味着苏轼的命运再次遭受重大的挫折。环境更加险恶,生活更加艰难,但是他通晓事理的睿智和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的聪明,赋予了他解脱忧患的非常人所及的能力,“超然自得,不改其乐”(《与元老侄孙书》),林语堂亦称他为“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如果说当年被贬黄州之时,苏轼还有东山再起的斗志和希望,此时一贬再贬,他早已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苏轼明白,在人生败落低迷的极点上,必须做终极的人生思考方能解脱自己的心灵,超脱现实的苦难。苏轼顿悟,人生并非只能一味地往上爬升,暂停脚步,欣赏沿途风景,也无不可。因此在晚年备尝艰苦,九死一生之际,他笔下的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减字木兰花》)海南岛在宋时被目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所咏,多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兴起飘零流落的悲感。而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调,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与此意留蛮荒。他年谁与作地志,海南***真吾乡。”(《九疑吟》)苏轼与其他逐客不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敌视,而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自我拓展了享受人生乐趣的心灵空间和营建了自得其乐的精神家园。
综观苏轼一生,正如其自嘲:“心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虽然一生坎坷,但他始终表现出洒脱旷达的精神。现在看来,即便遥隔近十个世纪,苏轼的至理哲语,依然亲切如昨,仍具现实的生命力,在人生不同的心境里,都会折射出智慧、旷达、欣愉的光芒。
参考文献:
[1]王水照.苏轼[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周汝昌等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C].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4]康震.康震评说苏东坡[M].北京:中华书局,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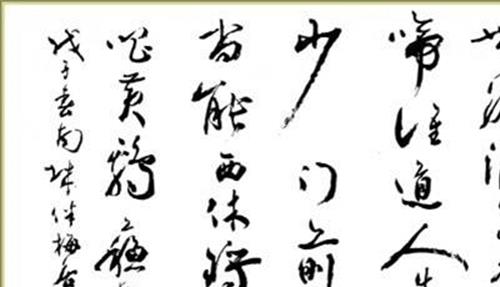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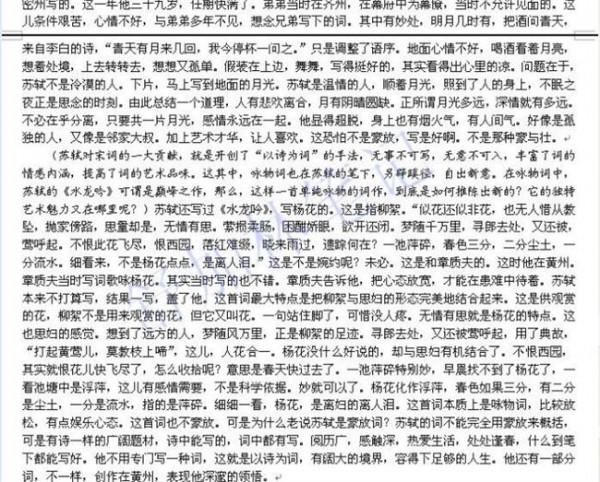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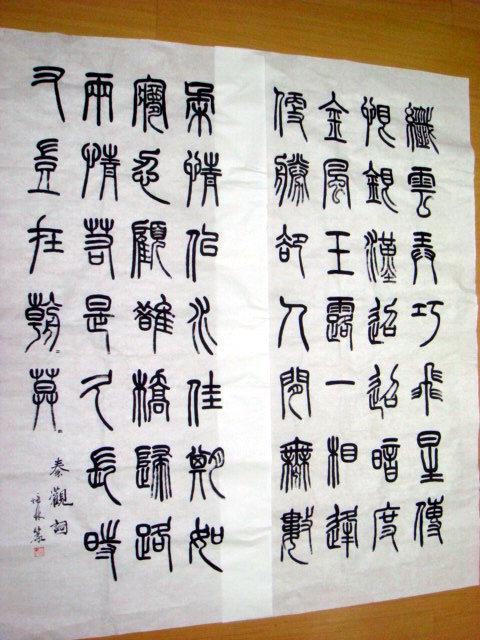


![>[转] 苏轼诗词中所体现的豁达 乐观](https://pic.bilezu.com/upload/6/3c/63cb640e093e64546035bbef19830920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