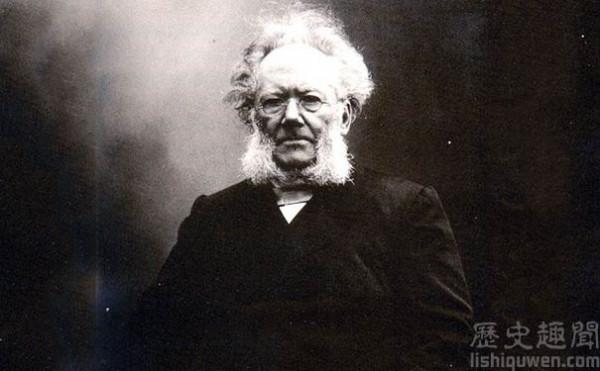易卜生现实主义 中国缺少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土壤
原标题:中国缺少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土壤
□陈季冰 上海媒体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着史诗般的小说《百年孤独》在世界文坛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逝世也再次令整个世界沉浸在一片对这位哥伦比亚作家的溢美之中。
BBC在马尔克斯的讣告新闻中将他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家”,这使我这个想事情顶真到古板的人颇为伟大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感到不服气,虽然我本人也是马尔克斯的热忱读者。在我心目中,能够与塞万提斯相提并论的作家,大概只有但丁和莎士比亚等极少数几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了。
当然,不含蓄的西方人经常喜欢使用这类夸张的最高级来表达一种即时情感,记得《纽约时报》还曾形容《百年孤独》是“《创世纪》之后最受欢迎的一部文学作品”。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世人用任何语言来向马尔克斯致敬都是不为过的。
马尔克斯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是一个世纪以来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外国作家都无法比拟的。我想,这应该是得益于他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不期而遇。上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大陆国门乍开时,扑面而来的便是创造力正当巅峰期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这使得自我隔绝了30多年之后的中国文学一下子就被它所建构的绚烂瑰丽的审美世界所征服。
躺在我家书橱里的那本用劣质纸张印刷的泛黄的《百年孤独》,至今依然飘散着那个时代的文化气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马尔克斯正式向中国大陆授予版权之前的十几年,他在我们这里已是家喻户晓。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作家仿佛人人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人人都在自己作品的一开头就回忆“多年以前……父亲领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眼下仍然活跃在文坛上的比较有名气的中国作家中,没有谁未曾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塑造。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将近一百年前那些五四干将们对“娜拉的出走”产生的热烈兴趣,但相对于易卜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20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作家(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在中国掀起的热潮更加持续。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中国的这股经久不衰的“马尔克斯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读之上的。这种误读就是———当中国作家在马尔克斯以及其他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后,他们的直觉反应是: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但接下来,他们在对这种自新大陆舶来的文学样式进行模仿和借鉴的时候却错误地认为,中国本土历史和现实土壤中也蕴藏着唾手可得的丰沛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资源。
许多中国作家中的马尔克斯粉丝将“魔幻现实主义”等同于讲一些鬼怪故事,他们总是喜欢鹦鹉学舌地模仿马尔克斯的口吻说:“在我们山东平原(或三秦大地)的农村,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讲故事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也许还会列举从《太平广记》到《聊斋志异》的多彩例子,来证明中国文学中的丰富的“魔幻养分”。
然而,他们那多多少有些肤浅的头脑没有进一步思索过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本质。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没有神灵鬼怪故事?但为什么只有拉丁美洲才出现了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文学类型?事实上,魔幻现实主义的重点并非故事里出现一些仙女、狐狸精和超现实情节,而在于故事的发展轨迹经常完全不符合常规的逻辑,并因此产生出一种迷幻绚丽的艺术效果。
为什么这种文学样式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而非“魔幻浪漫主义”或“魔幻超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它根植于拉美大陆的现实叙事中。马尔克斯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曾一再强调,这就是拉美人看待和讲述世界的正常方式:我们并不会认为一个人从母亲的耳朵里生出来或在母腹中孕育3年才出世,是什么超自然的“魔幻”的事情。实际上,它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
马尔克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另一部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为理解这种独特叙事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痛苦而感人的爱情故事,它并没有多少一般意义上的玄怪成分,但小说通篇弥漫着那种一如既往的神秘与荒诞、夸张与扭曲……使之依然称得上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经典。
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门外汉,我没有研究过拉美的民间文化和文学传统,但我认为,深受理性入世的儒家文化和超然出世但逻辑更强的佛教文化浸润的中国是没有多少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和现实土壤的。的确,中国人也非常喜欢讲鬼怪故事,但中国的神灵鬼怪的行为遵从的完全是人世的现实逻辑,它们差不多就是礼义廉耻的超人化载体。
当然,中国缺少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和现实土壤,并不会阻碍中国人欣赏这种文学。因为纵使它再魔幻,也终究符合普遍人性。
不管怎么说,来自遥远拉美的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已经彻底改写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道,这种全盘颠覆性的外来影响很可能是3000年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纵使莫言为中国人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这其中的功过是非也仍然远未到盖棺定论之时,这个“百年误读”只有留待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