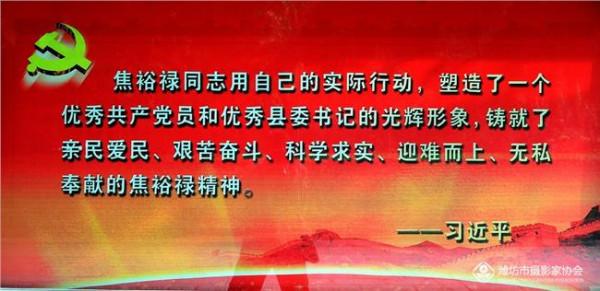焦菊隐心象 焦菊隐“心象”说辨析(转载一)
关键词:焦菊隐 心象 中国戏曲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心象”说是我国著名导演焦菊隐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演剧体系面提出来的重要理论。然而,多年来,在如何正确理解“心象”说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要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并向同行专家请教。
一 “心象”与“образ”
“心象”一词,即使在最新的现代汉语辞典中也是找不到的,它是焦菊隐先生的独创。当然,一切有戏剧理论常识的人们都可能把“心象”一词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内心视象”联系起来,甚至以为“心象”就是“内心视象”的简称,就象“北京人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简称一样。
譬如,著名导演欧阳山尊就认为“心象”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视象”是一回事,只不过说法或译法不同而已。大概是因为这种词素上的相似之处,童道明先生曾说,“心象”说是焦菊隐先生“假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义提出来的。
不过,在童道明看来,焦菊隐提出“心象”说的真正意图是要“从中国民族戏剧美学出发并适应着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实际”,对斯氏体系进行一次“精心的校正和发挥”;“心象”说是“焦菊隐戏剧美学中最有光彩,也最富独创性的一个部分”。[ii]
在中国戏剧界,不同的人对焦菊隐的“心象”有不同的评价。有一种说法,认为“心象”说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它起了“化解”斯坦尼体系的作用。例如:田本相先生指出,“焦菊隐—北京人艺演剧体系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最突出的是熔铸着中国民族诗性灵魂和艺术精神传统的舞台诗的创作方法。
其精萃之点即是焦菊隐的‘心象’学说。更确切说是‘心象—意象学说。焦菊隐正是以这个学说化解了斯氏体系。”[iii]在这里,“化解斯氏体系”的说法和上面提到的对斯氏体系作一次“精心的校正和发挥”有着本质的区别。
谁都知道,在现代汉语中,“化解”有着“解除”、“消除”的意思。那么,焦菊隐的“心象”说,是不是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呢?焦菊隐本人有没有可能试图“化解”斯坦尼体系呢?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焦菊隐的“心象”说是几种不同表演流派“融合”的产物。例如:胡星亮先生认为,中国话剧界在50—60年代有过一次转折,这就是从基本按照斯坦尼的体系排演到融合“体系”与戏曲进行新的创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焦菊隐。
“而焦菊隐的卓越之处,则是他“融合‘体系’、戏曲和哥格兰的演剧学说而独创的‘心象’(或称‘意象’)说。”[iv]北京人艺老演员于是之也持相似的观点。[v]又如:童道明先生认为焦菊隐的“心象”说包含了“体验派艺术理论与表现派艺术理论的辩证结合”,“在焦菊隐的‘心象’说指导下的舞台实践,必然会摆脱两个已知的对立戏剧流派的极端,走向艺术的辩证。
”[vi]在这里,童道明只说“心象”说是体验和表现派两个表演流派艺术理论的辩证结合,并没有提到中国戏曲。
由上可见,我国戏剧理论界对“心象”说的解释不仅是不一致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互相矛盾的。
实际上,焦菊隐先生本人在运用“心象”这个概念时,也有欠推敲之处。焦菊隐是在40年代初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时开始运用“心象”这个概念的。童道明将焦菊隐的译本同丹钦科的原著作过对照,发现凡是原文中现在通译为“形象”的“образ”一词,都被焦菊隐先生译成“心象”,个别地方也译作“意象”。
童道明说:“由此我们可以揣测,在焦菊隐的理解里,‘心象’(意象)乃是舞台形象的初阶、胚胎。”[vii]但是,笔者在对照焦菊隐的译文与丹钦科的原著后,发现仍有一些地方是和童道明的揣测不尽相符的。例如:在中译本的188页有这么一段:
《樱桃园》的心象是现实的、简单的、明朗的,同时,又熔铸成为十分深刻的结晶的精髓,所以,这些心象,结果都象是象征一样了。整篇戏都是这样地简单、这样通体地真实,这样纯净而不肤浅,抒情的本质发展得使我认为那简直是一首象征诗了。[viii]
笔者对照俄文版原著,觉得这里焦菊隐所用的“心象”一词和后来焦菊隐的研究者们所概括的“心象”显然不是一回事。人们通常认为,焦菊隐“心象”说中的“心象”指的是人,是角色在演员心中的感性呈现,而在上面一段引文中,丹钦科所说的“心象”显然不仅仅指人,它还指《樱桃园》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譬如“樱桃园”本身就是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的。
丹钦科在这里用的是“образ”一词,它显然应该译成“形象”。
如果我们采用童道明先生的观点,认为戏剧中的“心象”是“次成熟”的,而“形象”才是成熟的,[ix]那么,在这里同样说不通,因为丹钦科在这里所谈论的明明是“熔铸成为十分深刻的结晶的精髓”的“образ”,即形象。
它们显然是够“成熟”的。可是,焦菊隐先生偏偏把它译成“心象”,如果说有什么意图的话,那也不能说是和后来创立“心象”说有关。笔者以为,在这段文字中,焦菊隐先生把“образ”译成“心象”,与其说是出于理论创新的意图,不如说是翻译上不够准确的表现。
因此,我们在研究焦菊隐的“心象”说时,完全可以不再考虑它和“образ”一词的对应关系;与其这样做,不如干脆把它看成焦菊隐先生独创的一个新词。研究“心象”说本身,搞清它的意义和价值,才是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