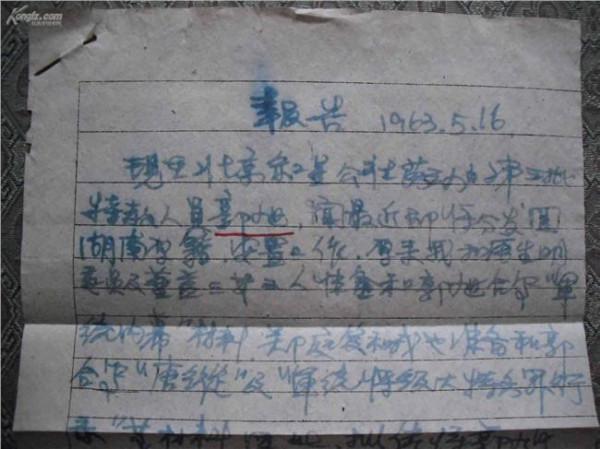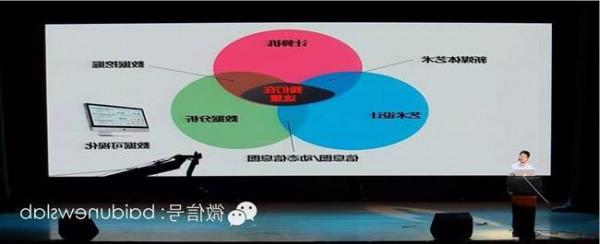沈浩波诗歌 沈浩波:中国当代极少数诗人在写美学上有效的现代诗歌
1、 你对诗歌语言的看法如何?诗歌的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诗人与诗的关系是什么?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与语言的关系,是每一个诗人写作每首诗的时候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我看来,语言不能独立于诗,诗也不能独立于语言。在一首诗歌中,语言不能大于诗,诗也不应大于语言。
不少过于强调语言的诗歌流派,都容易陷入语言大于诗的尴尬境地。语言大于诗,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语言变成了一种概念,一种企图脱离诗而独立存在的理念,这种语言概念化的写作,是一种语言乌托邦,最终的结果往往导致完全丢失了诗,只剩下所谓的语言,但这种语言如同无源之水,无土之木,如同塑料花。另一种是,在诗歌中只见语言不见诗,用语言的形式、花样、修饰来掩盖诗之贫乏,或者说,遮蔽了诗之存在。
诗大于语言,则意味着一首诗只有诗的灵魂,没有诗的身体,或者说诗的内核与诗的身体不匹配,这往往是一首坏诗产生的原因。
语言与诗,应该有共同的完整的世界观,拥有共同的观念,从而形成诗即语言,语言即诗,诗与语言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成为一个空间,一个世界。在这个标准下,如果一首诗出了问题,看起来可能是语言的问题,但实则上还是诗本身出了问题,是诗人对这首诗的内核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是这首诗里的诗歌观念、诗歌世界观出了问题。由此才会外在于语言,令读者感觉是语言出了问题。
中国诗人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大抵是纯口语、泛口语(口语偏书面语)和书面语三种。这三种语言形式,我在自己的写作中都有很多尝试,但我总体上还是更倾向于用纯口语写作。这是由我的诗歌观念、诗歌世界观决定的。我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现代的(适应当代性时间流速)、贴近身体的、指向生命、生存和人性的诗歌写作,这种诗歌写作观念必然会带来相应的语言观念,也就会带来相应的语言形式——纯口语。
但有时我会尝试泛口语和书面语的写作,尤其是在处理一些抒情性诗歌和抽象的、形而上的诗歌题材时,我会觉得泛口语或书面语的语言形式更加匹配,更加容易实现。
从这个角度而言,泛口语的写作更匹配抒情诗歌的世界观。书面语的写作更匹配形而上的与世界形成抽离关系的世界观。在更多的情况下,抒情诗歌容易脱离诗的现代性,更容易走向一种陈旧和腐朽。书面语的写作则更容易让语言大于诗,或者用语言隐藏诗的无能。
而纯口语的写作有时会对诗人提出不能让诗大于语言的要求。当然,纯口语诗人中的极端形式主义者则干脆让语言脱离了诗,变成了只有所谓的语言而没有诗的语言乌托邦,但这种语言并不存在,当语言脱离了诗,这种乌托邦其实同时也消灭了语言。
诗人与诗也应该是一体的。15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其本质也是在试图建立一种诗人与诗的关系,写作一种有身体的诗,这个身体,既是诗的身体,也是诗人的身体。
2 、你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态度怎么样?
我们必然在这个传统中。因此不必放大这个传统。我不喜欢割裂中国传统与世界传统。在我看来,所谓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是一种文化妄想症。我们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单独承接一个所谓的中国传统,没有这种可能。中国在世界上,中国诗歌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都已经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了,地球越来越小,交流越发便利,人类文明越发成为一个整体,世界的传统即是我们的传统。
唯有接受世界的,普遍意义的现代艺术标准,才能使我们的传统在今天变得有意义。
走向现代,而不是回归东方式的乡愁,对于至今仍然充满乡土情结的中国诗人来讲,其实更加重要。只有从身体上解决了现代性问题,才有能力真正自觉于传统,用现代人的内心,重新找到传统存在的依据。
诗人在获得了世界之后,才能取得自觉于地方,自觉于传统的资格。而非相反。更不是像中国当代的一些诗人一样,到了某个年龄,因创造力的衰退,亦因先天现代性的缺乏,从好不容易积累起的现代性标准上转身逃跑后撤,有的后撤到乡村才子抒情,有的后撤到所谓东方文化国故,有的后撤到文革后的政治抒情……在丧失现代,丧失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成为传统一部分的可能。
先有现代性,而后有中国性,这才是真正的艺术逻辑。这两者的兼备,才可能在世界诗歌的历史中,重新建立起汉语诗歌的传统。
中国古代的诗歌写作中,几乎不涉及人性,更遑论对人本身的追问。不追问人性,就难以抵达复杂的灵魂。这与世界诗歌的现代性发展路径,恰好背道而驰。世界文学进入现代主义之后,对人性的追问,对自我的拷问,变得更加深刻——中国当代诗歌依然懵懂于此。
我无意纠正中国传统,中国古典诗歌已经给予了汉语伟大的传承,不必苛求太多,应该苛求的是,当我们开始成为传统的新的一环时,我们该为这传统贡献什么。至少,不能再躲进小楼,背对世界。
3 、对你影响最深的是哪一位诗人或哪些作品?
1999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我和我的同仁们一起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开始置身于中国先锋诗歌的风口浪尖,毁誉参半至今。在这个并不算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有三个艺术关键点在我身上发挥作用。一是:口语写作。二是:先锋和原创。三是:灵魂里的不妥协、不世故、尖锐的人文性。而在这三点上,我在1997年到1998年读大学时,认识的三位诗人恰好可以分别与之对应。
那时我在北师大读大三,写的诗歌大体上都还是传统的学院写作范式,书面语的、形式整饬得像小棺材的、精神上往形而上的方向高蹈而去的,修辞的、语言炼金术的那种写作。就在这时,我先后认识了三位从北师大毕业的诗人师兄,他们年长我10岁左右,也都刚刚崛起于中国当代诗歌界不久。按时间顺序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依次是侯马、伊沙和徐江。他们在我的写作生命中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侯马令我选择了口语。当时侯马已经写出了一些名作,比如《那只公鸡》、《种猪走在乡间的路上》、《李红的吻》等。早期的侯马诗歌,是一种口语抒情诗,从其诗歌语言中能够看出,他应该是受到了韩东的不小影响。与侯马认识并迅速成为朋友的同时,我也开始读到了韩东、于坚等第三代口语诗人的诗歌。
侯马早期的抒情性,与其出生于类似于乡村环境的小县城有关。这与韩东的“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形成了性格中温柔的部分”完全契合,而我也有过相似的乡村经历。
这种抒情性让我与侯马之间也有了更多的契合。侯马、韩东的这种口语抒情诗,令我意识到口语作为一种生动、朴素的语言形式,在表达情感时的优势,它能令抒情变得更有质感、更具体和诚实。而且我始终更热爱朴素的美学。
当然,抒情美学的脆弱性也是我与侯马都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多年以后,侯马用他的智性、理性、思辨、超现实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我的方式和他不一样,早在我的“下半身”时期,就开始采用一种更极端的先锋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我与侯马至今仍然有非常多的共通性,尤其是对于人性的探究,对于文明的探究,都是我们共同具备的写作母题。侯马在我生命中的出现,他当时的写作和他在与我交往中体现出来的雄辩魅力,令我毫不犹豫地从一个泛学院派的大学生写作状态,走向了专业的、口语的自觉写作。我当时一些写得不错得诗歌如《我们那儿得生死问题》、《我想看见光》、《墙根之雪》就来自于这种影响下的转型。
与侯马相比,伊沙与我的精神契合度更高一些。没有见到他本人时,我像大多数年轻诗人一样,也还只是将他视为一种先锋的、异端的存在。我忘了我们是在1998年还是1999年第一次见面,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书信往来。我很快意识到,伊沙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类型化的异端写作,也不仅仅是一种颠覆式的写作,而是一种更彻底的、更坚决的、更现代的写作,其先锋性意义、原创性意义、对口语这种语言形式的推进意义都“当惊世界殊”。
他的诗歌具有惊人的阅读效果和魅力,我甚至觉得,他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时,出现的第一位真正具备现代意识(当时被诗歌界称之外后现代)的诗人。
我当然被这种先锋精神所感召,这与我身体里和生命里的某种因子有高度的契合。
我在短暂的口语抒情诗写作之后,迅速进入了一种更极端的、更先锋的口语状态,写出了《一把好乳》、《棉花厂》、《姐姐去了南方》、《饮酒诗》等名作。而“下半身诗歌运动”也肇始于这种先锋与美学颠覆的热情。
我意识到了伊沙的写作和伊沙这个人身上强大的吸附力,这甚至带给了我漫长的焦虑,我不想被认为是“第二个伊沙”,我希望写出完全不同于伊沙的诗歌。这种影响的焦虑在我的写作中存在了很久。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美学上的杞人忧天,我们在写作个性上的差异太大了,想写得相似也不可能。
但这种影响与焦虑,吸附与反抗的过程现在看来还是非常有趣的,对我自己的写作构成了另外一种意义。这也是现在我被外界认为美学风格比较丰富的原因之一:左冲右突,只为形成完全不一样的自我。
徐江对我的影响要迟缓很多。虽然当时,我与徐江的私人交往其实比伊沙更多。他在天津,我们见面聊天的时间更充分。但长期以来,我和徐江在诗歌美学上颇多格格不入之处,多有彼此的质疑和不以为然。在我的三位师兄中,徐江是唯一明确地表现出对我当年发起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质疑甚至鄙薄,这当然也令我心中多有腹诽。
但交往日久,对其写作的认识和坚持的美学了解得越深刻,我就越发意识到徐江的可贵,以及他的写作和美学立场对于当代中国诗歌的价值。
正是在这种理解下,近年来,徐江对我的写作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精神层面的,灵魂层面的,他是我见过的,与陈旧、腐朽的诗歌坛子保持着绝对内心距离的诗人。他的写作,精神纯度越来越高,越写越高级、纯粹,指向文明和灵魂。
他正在成为中国当代诗歌中最不一样的诗人。而在其美学立场上,他对诗歌中现代性的一面的极端坚持,对非现代性美学元素的极端排斥,虽令我觉得残酷,也有一些不甚同意之处,但仍然心生钦佩。侯马给徐江起了个外号,叫“诗鞭”,他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身边的诗人同行,对于我的写作来说,徐江这根“诗鞭”同样发挥着作用,让我不敢放纵灵魂中陈旧、腐朽的一面。
作为一个诗人,写作生涯中得一良师益友足矣。我一下子拥有三位。更巧的是,这三位还都是我的师兄。我其实不是一个有太多门户之见的人,母校情结也不重,但这种巨大的巧合,还是令我觉得是一种天赐的缘分,神奇而不可思议。
更重要的是,对我的写作形成重大影响和激发的三位诗人,是我的同时代诗人,不是故纸堆里被经典化了的诗人。我与他们的年龄差异,差不多就是杜甫与李白的年龄差异。他们仍然还在生长,尤其是徐江与侯马,都还不能算是已经真正完成了自我写作使命的诗人,都还在艰苦的攀援在艺术之险峰上。因此这种影响、碰撞、激发显得更加生动、具体、日常,也更为有效。再过30年,回到看他们三位与我的写作,我希望看到更大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