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佩佩陈建斌 郑佩佩:初恋陈鸿烈同时追求潘迎紫 还害怕我对她不好
香港庙街,一家老牌餐室里,人声鼎沸。这家餐室有两层楼,地方不大,二楼都是卡座。载我们到此地的出租车司机,听我们一说目的地,就来了精神:“这家餐室非常有名,以前经常用来拍一些怀旧戏。”
郑佩佩选择了在这里接受我们的专访。这是一家和她阅历相同的餐室,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她一见到我们的摄影师老方,就说:“你很脸熟,我好像经常能见到你。”
老方愣了一下,寻思曾在什么场合见过这位采访对象。郑佩佩笑声爽朗,她显然不认为自己抢了老方的开场白——毕竟记者和老方才是经常见到郑佩佩的人,尽管是在影视剧中。
谈话中,郑佩佩喜欢说“yeah”,喜欢大笑,常微笑着说“对不对”,谈到一些往事的细节,如不能确切记得,她会直接说“我不晓得了”。由于与店方熟稔,这里成了她的客厅,很多人能认出她来。采访中,隔壁餐桌来了很多食客,他们低头吃饭,各自谈着事情,在我们走动时,甚至没有人投来好奇的眼光。这似乎坐实了郑佩佩喜欢香港的一个原因:这里的人,就像自己的邻居一样。
谈到人生的各个阶段,郑佩佩最喜欢目前的自己。关于往事,她眼神会黯淡,但很平静。她说,那时候的人,想法很简单,不像今天年轻人想得那么复杂;早点结婚生子,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在巅峰期息影,人们替她惋惜,她对这些惋惜敬谢不敏,但对子女有内疚,认为自己亏欠了孩子一生。
平生侠名为吾累
郑佩佩的愧疚,源于1989年与丈夫原文通的离婚,导致她的4个孩子没有完整的家庭。
那是她人生的分水岭,直接否定了她过去的20年。原文通是台湾商人,其父是邵氏公司在台湾的代理商。他与郑佩佩的相识颇具戏剧性:郑佩佩的母亲到原家打麻将,输了钱,让郑佩佩送钱过来。她就这样和原文通相识并相恋,于1969年结婚。
1970年,郑佩佩决定息影,和原文通移民美国。对于郑佩佩的决定,小她6岁的妹妹郑保佩(现在是佩佩的经纪人)说:“那时候讲究归宿,如果一个女孩到24、25岁还没有嫁出去,就已经是很夸张的事情了。”
老板邵逸夫、恩师胡金铨都支持郑佩佩。她说,“胡导演很喜欢我的选择。觉得我选择很对,很会选。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我选得好,就觉得我嫁这样的人最合适。可能大家也看不到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师长们对原文通评价很高,“主要他不是圈内人,有学问、很正派。”而原文通在众多追求者中胜出,也因为他的确与众不同。
“他老跟我唱反调。(笑)譬如我爱喝可乐,我拍戏时,罗(维)叔叔买一打可乐,放两大杯冰块在那里让我喝。我结婚以后,原文通的第一点是‘不许喝可乐,不喝可乐不会死掉’。我心想对啊,不喝可乐不会死掉,为什么我非要喝可乐?我是觉得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在侠女的光环下,郑佩佩接受着广泛的宠爱。“突然有人唱反调,就觉得其实这个人还比较有道理。至少我说月亮是方的,他告诉我,不是方的,是圆的。”
在美国,郑佩佩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琐碎生活。20年里,她怀孕8次,流产4次。“借个肚子为丈夫生孩子”,她当时认为是自己的义务。如果不是在1985年为单传的丈夫生下一个儿子,她的生子事业还将继续。
郑佩佩没有侠女的武功,但无疑拥有侠女的体质,4次流产并没有对她的身体造成很大影响,相反,她还干了很多活儿:开舞蹈班教人跳舞,管理百货商店,亲自送货上门,经常把大件货物送到买主楼下,然后通知买主:家里有没有男人,下来一起搬东西。
“去了美国之后,我才知道我有多红。”在唐人街,几乎无人不识郑佩佩,那里的华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猜测她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给了原文通很大压力。
“他本身就很大压力。因为别人都会叫他郑佩佩的丈夫,甚至有人叫他郑大哥,不容易,找一个有名的人做太太,而且这个太太还——虽然不要穿名牌,但是她要的东西,太理想,太虚无。”
她要回归社会,希望为当地华人做些事情,于是办了个华语电视台。即使已经息影,郑佩佩似乎还是把武功高强的“金燕子”角色代入到真实生活中,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定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拿到。
移民美国时,她认为在恋爱中拥有了一个happy ending,“没想到以后,完全没有想到。我就觉得女孩子最终还是要一个归宿。没有想到,喔,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华语电视台非但没有做成功,还让她亏损了二三十万美金。丈夫是生意人,并不支持郑佩佩的这一事业。分歧日渐加大,最终他们在1989年结束了这段婚姻。离婚后,一向对钱没有概念的郑佩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她要独力为生计奔波,还要求自己与前夫一起抚养子女,此外还须偿还做电视台欠下的债务,那笔钱对于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最近,郑佩佩总结这段婚姻:“我不是温柔的女人,我太好强了。我觉得女人不要太强,弱一点的女人男孩子会喜欢多一点。我不太像女人,所以丈夫才把我开掉。”
离婚后,她还和丈夫一起住了些日子,不让孩子知道。甚至妈妈及妹妹都是过了好久才知道郑佩佩离婚的消息。
问:“你说过‘戏外不是戏里面’,当时自己没有区分得太开吗?”
郑佩佩说:“对,我想起还是。演戏一定会有个ending,人生其实是不那么容易有ending的,这让我学到很大的一课。虽然我们常常说人生是戏嘛,但是事实上那部戏是比较长的,要你自己导、自己演、自己编,然后自己去承受所有的代价。”
九百多年前,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折磨,九死一生后得以出狱,感慨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如今的郑佩佩总结婚姻教训,颇有那么一点“平生侠名为吾累”的意味。
在绝望中,郑佩佩想起了拍戏,想起了香港。
侠女闯香江
“你现在是美国人,还是香港人?”
“香港人。”
在一生的地域身份中,郑佩佩历经了这样一个变化:上海人,1946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人,“佩佩”的上海话发音与baby接近;香港人,1961年随母亲投奔香港的舅舅,在此地生活、工作、成名;美国人,1971年,她和原文通移民美国。
现在,郑佩佩是香港人。她喜欢这个令她成名的地方,这里让她感到亲切,此外还为老人提供了许多养老的方便。复出至今,她没在香港买房,现在和女儿租住在一间公寓里,“我对我的老来有了安排,香港政府有一种老人公寓,我现在在申请中,等他们批下来。”
然而少年时来香港,郑佩佩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她的父亲是探长,1949年后在内地入狱,被关在了数千里外的内蒙古。在郑佩佩小时候的记忆中,因此改跟母亲姓郑。但即使如此,她也没能逃脱这个群体在那个年代的固有命运。
“刚解放的时候,国内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的,我们那时候的教育,每个人都非常有礼貌。我父亲不在,我妈妈很早就带我弟弟妹妹到香港,剩下我一个人在上海。那会儿治安非常好,人也非常懂礼貌。但是我在他们中间,总觉得很被排挤,因为我身份不好,所以我从小很好胜。我觉得虽然我是家属,但我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我从小就愿意穿破衣服,愿意比人家劳动多一点。我从小就很不服气,资产阶级的家属,我就一定是不好的?!”
16岁时,她并不心甘情愿地来了香港,“我妈妈一定要接我过来,骗我说外婆病了——外婆很疼我,也在香港。我来的时候,觉得香港很腐烂,(这里的人)经常打麻将,不务正业。”
带着这种倔强,她进入了邵氏。当时公司会请一些武行师傅来培训新人,以拍摄武打片。郑佩佩也在其中。当她看见一些女孩因为被打到鼻子出血而哭起来时,心里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丢女孩子的脸。
由于出众的舞蹈功底,她被胡金铨导演看中,让她出演《大醉侠》的主角金燕子。这部电影被誉为新派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上映即大获成功,她很快成为香港街知巷闻的女一号。
那时候,很少有人赞她漂亮,集中在她身上的赞美,是“能打”。她说,自己并非真的能打,而是比其他女孩子会打,能吃苦,所以就以这个出名了,“我走在弥敦道,那些‘飞仔’(流氓)都不敢碰我,他们不晓得我(会武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
更令她得意的是自己那时候参演的电影,票房都很好,“我的戏都过百万。不得了,不得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漂不漂亮,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对不对?他觉得你很漂亮,你可能不是很漂亮,对不对?”
她渐渐定型,成为当时香港媒体眼中的武侠女皇。认识原文通前,她和两个人先后恋爱。第一个是陈鸿烈,在《大醉侠》里演反派玉面虎;第二个是岳华,演醉侠范大悲。和陈鸿烈的恋爱很短暂,结束得还颇有戏剧性,“他虽然整天说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但我们没有真的怎么样好过,那时候他追我,还同时在追潘迎紫,结果他哥哥告诉我了。我蠢得要死。(笑)那时候我很红了,他就担心我会对潘迎紫不好。为什么我要对她不好?”
至于恋爱5年的岳华,她不愿谈及,“我想还是要少提他,回头他回到家里还要挨揍。他太太还是蛮在意,所以我尽量不说他。”
在《大醉侠》里,潘迎紫饰演郑佩佩手下的一个无名女兵,后来潘与陈鸿烈结婚,这段婚姻只维持了8年。《大醉侠》的武术指导是韩英杰,跑龙套的有程小东,当年13岁,在片中饰演一个被刺瞎眼睛的小和尚。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如雷贯耳的人物。只有绝对主角郑佩佩不仅淡出电影圈,还远离了华人社会,一走就是20年。这段时间,香港影视沧海桑田,当年看她电影长大的后辈,已成为这个领域的中流砥柱。而资讯传播发达,让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可以拥有更多光环,更多人涌进来竞争。
郑佩佩还能演戏吗?
东山再起
90年代复出前,她为自己是否还能演戏感到困惑。此外,她仍然希望留在美国,这样能与前夫分担抚养子女的责任——尽管她自己已经破产。但她很快发现自己谋生乏术。
“我当时是想,最好能留在美国,孩子还那么小,所以我就想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以为我开玩笑。我到餐馆说,我给你做洗工。他们觉得我开玩笑。”
纠结中,她陷入了有生以来最深的彷徨中,“谁告诉我什么东西我都会去拜,拜神、念多少经,我都做了。哪棵树砍掉就好,我就把那棵树砍掉了。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些都是错的,根本上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自己只要站起来,往前看,就没事,就把前面不好的全部都斩断,重新开始。”
她去澳洲看望母亲,在那里又见到了师父——1988年她就已皈依星云大师。星云大师告诉她,她还是应该重新做回“郑佩佩”,这样可以做更多事情,帮更多的人——这些人自然包括她的孩子。她想了想,觉得目前为止自己最能胜任的,还是演戏这份工作。
1992年,她回到了香港。因为没钱租房,星云大师让她住在香港佛香精舍,一住就两年。这段时间,她在香港深居简出,平素在佛堂帮忙做早课、晚课。经纪人冯美基告诉她:现在周星驰很红,你要跟他拍戏。于是,她接拍了《唐伯虎点秋香》。
跟影片充满笑点不同,拍摄的时候,片场显得很严肃,“太吵的话,周星驰他们就想不出东西了。你必须要很严肃,不能嘻嘻哈哈。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嘻嘻哈哈的东西,对不对。”
当时接到剧本,她只知道自己演的是一个会武功的华夫人,跟她之前的戏路一样。拍摄时,巩俐不肯搞笑,周星驰就问郑佩佩能否试试,郑佩佩二话不说,就与周星驰卖起药来。
昔日的侠女金燕子,摇身变成谐星。她与周星驰对戏,一个卖“一日丧命散”,一个卖“含笑半步癫”,令观众捧腹,也令胡金铨和李翰祥痛心。师伯李翰祥导演说,华夫人这个角色,把郑佩佩给糟蹋了。
面对师长们的质难,郑佩佩保持沉默,“我心想我现在最要紧的是工作。我只是这么想,接下去我们都要工作,我也不能向你们拿钱,对不对?他们一个是我师父,一个是我师伯,都可以说我,我只能听着,他们讲我什么我只能听着。”
现在的郑佩佩,如何看待华夫人这个角色?“我是幸亏演这部戏,不然内地不会有那么多人认识我。他们(胡金铨、李翰祥)不知道,他们不能想象,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我还是金燕子。”
在众多亲友都依然沉湎于金燕子这个角色的时候,郑佩佩率先走了出来。1996年,李翰祥去世,次年,胡金铨去世。这两个让郑佩佩感念一生的人,没能看到她在《卧虎藏龙》里的演出。这一次,郑佩佩第一次饰演反角——碧眼狐狸。
郑佩佩说,“我相信胡导演见了不见得会喜欢。因为我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影迷反对得不得了,说把我弄得那么丑!其实他们不把我当演员,把我当郑佩佩,还是漂亮的郑佩佩。”
离婚后的郑佩佩,从来没有想过再婚,“我觉得婚姻不是全部,我在婚姻这个课程里面,已经修足分了。不管生孩子也好,作为太太也好,都修足了。如果这辈子要做的事就是修那个分,我前面还有演戏分还没有修完,所以我回来修那个分了。”
午后的餐室,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名女食客,大概因为店方上错了菜,与掌店的一个高大男子吵了起来。吵架显然不是男子的强项,他情绪激动,略有失态。
郑佩佩先于我们下楼,68岁的她脚步轻健,从男子身旁走过时,停下,微笑,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迅速下楼,把吵架双方的喋喋不休,抛到了脑后。
我的朋友,在天上的比人间的多
人物周刊:爸爸入狱之后怎么样了?
郑佩佩:他1963年在牢里死了。1963年我才开始拍戏,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后来结婚的时候舅舅告诉我的。拍《杨门女将》的时候,我到内蒙古拍戏,正好是我父亲100周岁。我就觉得是冥冥之中,父亲希望我能够回去看他,看看他当时是怎么样生活的。
人物周刊: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你有什么反应?
郑佩佩:我跟父亲不是很亲,知道他去世的时候,已经距离去世差不多快十年了。就等于是很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反应。但在我的脑子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阴影:没有父亲长大的孩子。我婚姻不好,我对孩子们觉得抱歉,也是因为这点。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是希望他们有父亲和母亲存在的。
人物周刊:经历过这么多身边亲友去世的过程,你现在对死亡这个问题有过什么样的思考?
郑佩佩: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停一个站,可能在下一站我们又碰到。我周围很多好朋友都走了,有时候我们好朋友也不是天天见面,但是有什么事情我就说哎,打电话给谁,就发现这个人已经不是打电话就可以找到的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已经越来越多了。可能我的朋友里边,在天上的比在这里的还多。
人物周刊:拍《大醉侠》红了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郑佩佩:没有什么变化,我从小赚多少钱都给我妈妈,我妈妈那时移民澳洲,把我几年的薪水都拿走了。所以我要教跳舞、要配音,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人物周刊:那么多合作过的导演,有哪些人是让你记忆很深刻的?
郑佩佩:那真是讲不完。比如岳枫导演,他是我第一部戏《宝莲灯》的导演,他一直告诉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演员,让我一定要做一个演员,不要做一个明星。他的话我一直记到心里面,后来他走我也送了他。胡金铨导演是改变我命运的人,对我的影响很大。其实我如果能学胡导演那么爱看书就好了。
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你
人物周刊:去了美国后,有没有觉得自己过着那么平常的日子?
郑佩佩:我没有想这个,只是觉得想的事情,不可能做不到。这其实是我的致命伤。(笑)譬如说,我们搬了新房子,不够钱买窗帘。我说不要紧,我可以车(做)窗帘。那个房子很大,有2600尺,五六个房间,而且他们还讲究要像戏院那种波浪形的,我都可以做。我还煮饭,还要带孩子,还要车那个窗帘,有人不满意我就拿下来重车,车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人物周刊:离婚后,你欠下来的账要独自偿还吗?
郑佩佩:确实应该是我的事,对。
人物周刊:当时欠的债,也不至于到令家庭破产的地步吧?
郑佩佩:后来我们分开以后,我个人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所以就宣布破产,跟他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你曾谈到,离婚之后你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前夫是生意人,离婚的时候没有进行财产分割吗?
郑佩佩:我觉得自己不懂理财,4个孩子还小,至少我们之间有一个需要负起责任,况且那些都是他辛苦赚的钱,所以并没有去争取。
人物周刊:如果能让时光回流,你最想修正生命中的哪个阶段?
郑佩佩:其实每一部分都是不可缺的。逆境你能学的,要比顺境多。我现在回首看当时,想法完全不一样。当时很多事情过不了,其实过不了的就是你自己。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去怨别人。我们分开的时候,我找过心理医生,医生说你为什么不怨他?我说因为我觉得这没什么好怨的,做还是你自己要做的,比如生孩子这件事,是我情愿的,不是他拿着枪强迫我做的,所以我认为,或许我修正任何一部分,我都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人物周刊:所以当时心里面难过的点是哪些?
郑佩佩:这个人跟我生活在一起那么久,为什么他会那么不了解我。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了解你。
人物周刊:他误解或者说是不了解你的地方有哪些?
郑佩佩:我们俩对于很多东西的观念太不一样了。比如教育孩子,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所以认为孩子们必须要有父亲;他觉得我从小没有父亲,所以我不懂得父亲的重要性。
得失不能看太重
人物周刊:90年代复出那会儿,香港观众又换了一大拨人了,有没有担心年轻一代会把自己完全遗忘?
郑佩佩:我觉得我很lucky的一点是,虽然换了一代人,但是领航这一代的人,都是跟我在一块儿长大的,而且这些人,小时候我都对他们很好,所以他们都对我好。所以我觉得人,得失不能看得太重。
人物周刊:你当年怎么对他们好?
郑佩佩:当年我是坐馆姐姐嘛。打风了,我们拍戏很多那种叫花子演员,他们都不能出去,我就在片场招待他们,他们都记得。还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接了一个戏,那个监制,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今天,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人物周刊:是哪句话呢?
郑佩佩:我不晓得了。(笑)他说是我在片场跟别人随便讲的一句话,就帮助他,一直到后来,成就了他的今天。
人物周刊:他们后来怎么帮你?
郑佩佩:给我很多机会。你看不管哪个戏,尤其是动作片,他们这些武行或者武指,都是以前我们的小武行,他们都把我看作亲人。所以我常说不用他们老是帮我请助理,每个人都是我助理。(笑)
人物周刊:90年代回到香港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故人的?
郑佩佩:那时候住在佛堂,慢慢才跟朋友交往联系。我当时的一些老朋友,比如胡导演啊,罗叔叔啊,岳老爷啊,我相信他们慢慢慢慢开始觉得既然我能接受,他们也能接受,对不对。
人物周刊:当时的同辈朋友呢?比如陈鸿烈他们。
郑佩佩:陈鸿烈是帮我最大的,他很快就介绍我给周令刚,到北京去拍《马永贞》,去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人物周刊:当时已经拍了《唐伯虎点秋香》,经济方面还是很困难吗?
郑佩佩:还是很困难。经济上困难,工作也很困难。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经济上的问题一直到拍了《卧虎藏龙》后才比较好。
2009年上吴君如、钱嘉乐的《星星同学会》节目,我和岳华、陈鸿烈都去了。那天看3个人的话,觉得他比我和岳华两人感觉都要好,看起来身体都比我们强。他一直跟我说,他过不了67岁,是算命的跟他讲的。我就整天骂他,因为他有一个很小的孩子,我就说,你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的孩子怎么办?我每次都这样说他。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突然就走了(注:2009年,陈鸿烈在香港拍戏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我们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讲。
人物周刊:碧眼狐狸让你拿到金像奖最佳女配角,你拿到这个奖后有什么感受?要知道你当年是非常红的女主角。
郑佩佩:我当时是很感激的,感激这些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其实是女主角还是女配角都无所谓,只是他们对我认同。在生命里面,你永远是自己的主角,需要你一路走过来。你做些什么,那是工作,不是那么需要去执着的东西。(颖颖_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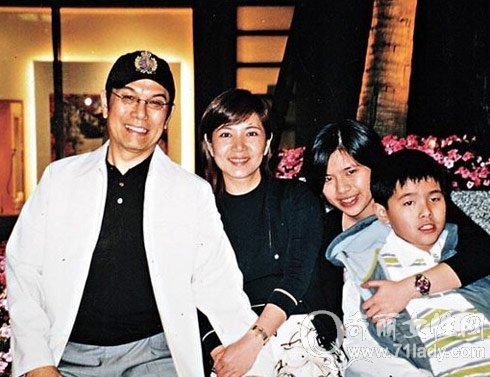


![>陈鸿烈去世潘迎紫 陈鸿烈拍戏途中猝死 与潘迎紫往日情被热炒[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d/27/d279101fab092a8fd330b251bd8da09a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