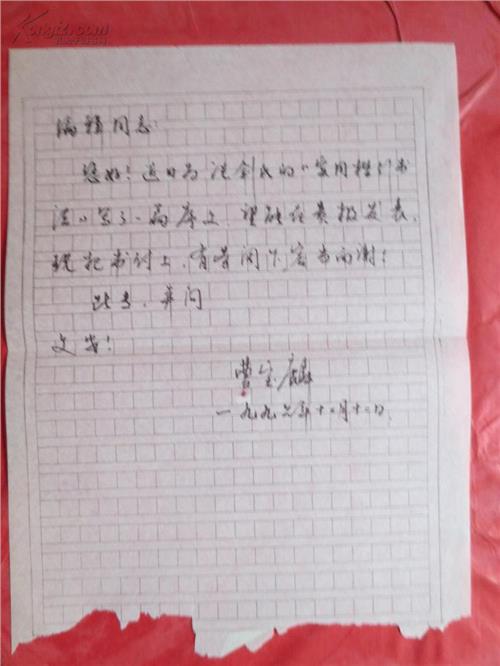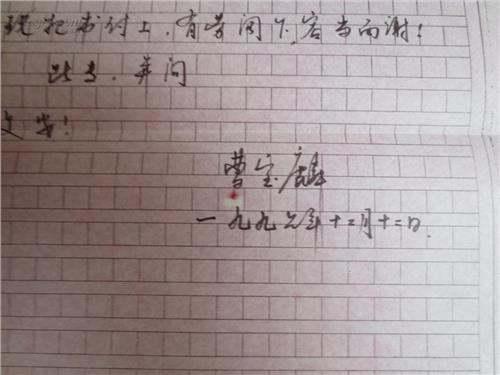曹宝麟抱瓮集 从《抱瓮集》看曹宝麟的书学研究
曹宝麟先生是当代中国书法界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二十多年间,他运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以传世书迹的考订为中心,对于宋代书法史的各个层面作了精深独到的研究。其成果汇编于最近由文物出版社推出的新版《抱瓮集》中。
新版《抱瓮集》在旧版的基础上新增文章20多篇,篇幅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其中考据类的文章占了大半,因此考据学也就必然成为本文的主题词。诚如白谦慎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曹宝麟所景仰的乡贤钱辛楣,不但长于训诂学,还精于史学。曹宝麟也以考证为津梁,推进书史的深入研究。”
将金石碑帖作为研究的对象,此风自宋以来就不绝如缕,至清代则蔚为大观。虽然如此,研究角度多有不同,或侧重于著录收藏,或着眼于辨别真伪。至于从文字内容出发考证碑帖的成果并不多见,自宋至清的法帖考证一类著作偶一见之,逮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兰亭》论辩”,这种“语言的考古”渐成书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与很多人只将眼光盯着名帖不同的是,曹先生更属意于那些较少受人关注而对书法史又起着重要作用的片纸短札,尤对宋代名家特别是米芾的传世书迹情有独钟。他以近乎愚痴的态度抱瓮而行,渐行渐远,几于大成。
选择书帖的文字内容作为考据的切入点,这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传世的书迹大多为一些“无头的公案”,要透过一些“不知所云”的话语勘破与书帖相关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需要广博的历史文献知识和洞若观火的识见,其难度无异于以针挑土。
与很多年谱著作和作品编年考订的做法不同的是,曹宝麟先生不是罗列资料、按序编排、以大观小地对个别事件予以阐释,他采取的做法是“小题大做”。
有时候,一个词、一句话成为他全篇展开的依据,反复辩难、层层推进、以点带面,力求深入彻底地解决问题。在学术风气极为浮躁的当代,曹先生以“窄而深”的研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而他也正坦然地享受着发现的快乐。
人们对于曹宝麟考据学成就的了解很多都是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蒙诏帖》和《平复帖》真伪的论争,特别是他遍检《全晋文》和《晋书》拈出与《平复帖》中“寇乱”相同用例的八个例句,以此证明《平复帖》中的“寇乱”指“永嘉之乱”,从而得出《平复帖》的作者不是陆机的结论。
虽然在现在看来,这未必是最后的定论,但是曹宝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于乃师王力先生“例不十,法不立”箴言的创造性运用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方法在《抱瓮集》中并不少见,如《〈蒙诏帖〉非伪再辩》中对于“亲情”一词的用法举例,这种严谨的态度正是曹宝麟先生作为考据学家最为可贵的品格。
也许收集资料对于学古汉语出身的曹宝麟先生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从一堆似乎毫不相干的资料中发现问题并由此窥破天机却是曹先生的专擅。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自许有佞古之癖,时时扮演细作,以勘破千年谜案,还历史真相而乐此不疲。
”从人物关系切入往往使他的考据收到绝处逢生之效。如钱公辅《别久帖》考证中,通过证明“元珍”(即丁宝臣)是丁骘的叔父,从而使对本帖文意的理解豁然贯通。
古人的称谓,往往能够显示人物特定的身份。曹先生在考证中对此也有熟练的运用。晁端彦《前日帖》落款为“端彦再拜”,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认为是李正臣(字端彦)。曹先生则指出:“称人表字,自称必是全名,这即是本帖毫无可能出于宦者(李正臣)之手的铁定事实。
”从而为此帖的作者释千古之憾。正是基于对人物身份、地位、行实的充分把握,曹先生多次翻古人之覆。如《钦止帖》的作者历来认为是王份,曹先生通过考证则认为应该是胡份;又如《平江帖》作者历来认为是王觌,而曹先生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为孙觌。翻检《抱瓮集》,真可谓新见叠出、触目珠玑。
曹先生虽然专业领域是训诂学,但是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对于宋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均了然于胸,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欧阳修《灼艾帖》称呼对方为“学正足下”,曹先生在排除疑似的胡瑗时说:“本帖的学正之所以不会是胡瑗,乃因为直讲为正八品,学正为正九品,欧公称呼绝无舍高就低之理。
”徐邦达先生认为章惇《会稽帖》中的“会稽”是指章惇出守的越州,曹宝麟先生则认为“会稽”属于以官所代人的称呼习惯,最后坐实为蔡卞。
真是横空出世,令人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曹先生对于一些公案的勘破有时会借助一些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如在苏轼《廷平郭君帖》的考证中,证实“汶上”即是“汶阳”,即现在山东东平,从而为准确系年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细读《抱瓮集》,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其材料来源大致不外乎正史、文集、笔记、方志等常见古籍,并没有什么秘籍善本之类。有些资料甚至是极为普通的,但是这些材料一经曹先生之手,有时就成了解决问题的重要线索。
这得益于曹先生对史源学的精深造诣。曹先生善于将一些资料作互证式的研读,这一方面可以将史料还原成一个立体的史实,同时也可以在相互的比勘中发现一些史籍记载的错误。
如在考证张商英《女夫帖》时,通过比较王明清《玉照新志》和施元之注苏诗的记载,指出王明清将王汉之、王涣之表字颠倒的错误。曹先生在《晏庐自述》中说:“我读书从来细致,几不疏漏,博闻强记和审思缜析,是考据的必备素质。
”曹先生读书除了细致之外,他对于资料的深入理解和创造性解读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与王安石变法对立面的司马光,在明白变法之势无可挽回的时候,只好选择退居洛阳从事著述。曹先生在欧阳修《上恩帖》的考证中说:“其洛阳所居的独乐园,我看不如叫‘失乐园’更为确切。”真可谓一针见血。
曹宝麟先生不仅是一位考据学家,他更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他的考据不仅是“学”的发挥,更有“才”的显现。使人赞叹的是,曹先生在考证书帖时不管挖得有多深,走得有多远,最后我们发现他的落脚点还在于书帖本身的书法风格。
他对于书法的评论,虽然只是只言片语,足以发人深省,收到使人冰释之效。在这方面,有两篇专论堪为典范,一是《章惇论》,二是《沈辽〈秋抄〉、〈颜采〉二帖考——兼论沈辽的生平和书法》。
此两篇文章皆先从书帖的考证切入,再及其人其书,显然是独立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书法风格有时也成为考证的辅助,如《米芾〈竹前槐后诗帖〉考》的附记中即借助签名形态进一步证实了此帖作于元祐七年的结论。鉴赏与考证本是二途,但在《抱瓮集》中,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曹先生的才、学更体现在文章之法方面,诚如白谦慎先生所言:“在书学领域,就注重文章之法而言,《抱瓮集》堪称典范。”
《抱瓮集》虽然是一部书法史的考证专集,但是由于它牵涉到宋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宋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遗缺”(白谦慎《序》)。这种填补不仅表现在一些具体的结论,而且表现在曹先生在行文中对于一些史实的发明。
如《蔡襄〈郊燔帖〉考》中对于宋代“郊燔”形式和时间的考证即是如此。曹先生并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这使得他的考证没有任何畛域的限制,他的笔触可谓无所不至。
从这一点立论,《抱瓮集》无愧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文化史和书法史方面的重要收获。诚然,《抱瓮集》并非尽善尽美之作,但其意义更在于昭示了一种求实和慎独的精神,特别是在学风不正的今天,尤其具有警顽起懦的力量,而曹先生“抱瓮而出灌”的愚公精神也将随着《抱瓮集》的出版而终将受到后人的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