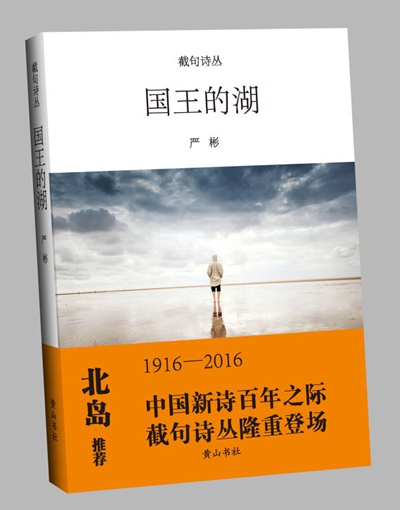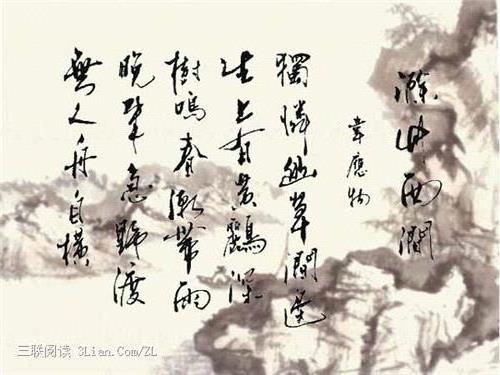严彬的诗 他反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我到现在都没能回答|和诗人严彬的对话
今晚,我想推荐一个诗人和他的三首诗给你。
在还未写诗前,我常在凤凰文学频道阅读他主编的文章。因缘际会,他作为嘉宾参与了诗歌精选的头一次线下活动。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真正见面,但总觉得要是我会喝酒,说不准哪天就会跑去找他喝酒谈天。这是他带给我的感觉,即便事发突然,也会令人感到发生的一切都很自然。不过,我压根不会喝酒,只好把这段可能发生于未来的谈话挪到线上。
他是诗人严彬,1981年生于湖南浏阳,工作生活在北京,是一个极具现代精神和个人气质的诗人。出版诗集《我不因拥有玫瑰而感到抱歉》《国王的湖》《献给好人的鸣奏曲》,著有小说集《观察家》《中等生活》。国庆后自老家一回北京,他就发来长长的答案。从用心的回复中,可以看到到严彬如何从一个普通工科生成长为一个诗人的路径,还有他对诗歌的特别理解。
万没想到的是,他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我从未想过也不知如何做答的问题,角度新鲜。我陷入了思考,但到现在都没想好怎么回答,可以的话,请你帮我一起回答诗人严彬的提问,好吗?直接在底部评论区回答即可。
▏ 两人对话诗歌君 X 严彬
诗歌君:去年你送我一本诗集,扉页上送给我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诗是好东西,又不是一时一地之功”。这句话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体会吧,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什么机缘开始写诗的呢?
严彬:当然。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几次,它是否意味着,我已经是一个被逐渐提及的诗人了(呵呵)。
写诗,以及其他艺术创作,我相信天分是第一位的。我写第一首诗是在2002年,在那之前,没有受过任何有效的诗歌教育,也没有读到过什么诗歌方面的经典。
说起来好笑,那时我还在念大学一年级,居然没有读过一本诗集——现在我接触过一些身边的人,或网络上的陌生人,我知道他们小学就读《红楼梦》,中学读了十几本世界名著,而我在大学以前,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
我和所有中学生一样,在课本中读过徐志摩的情诗和戴望舒的《雨巷》,但“什么是诗?”,“怎样写一首诗?”,我没有想过,也不知道《雨巷》和《静夜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样的状况,好在我语文成绩很好,高考,据当时的校长说,我是浏阳市第一。
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在语文方面的特长,阴差阳错到了一所工科大学,上一门可有可无的《大学语文》课,我遇到了一生中的重要人物姚海燕老师。
除却大学所学不说,是她这样一位在工科学校教文学的老师,将我这样一个混进管理学专业的理科生,领到了北京,走了文学的路。
在她为我们上第一节课时,没有讲课,放两部电影《死亡诗人俱乐部》和《爱比死更冷》,接着让我们所有人试着去写一首现代诗。
作为课堂作业,我写出了那几段如今看起来幼稚到让自己羞愧的《死亡诗组》。
我的诗人生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尽管到了十年以后,我几乎还没有发表一首诗。
诗歌君:这些年来,你觉得写诗给你带来了什么?
严彬:一方面,我享受这样的诗人生活。
中国的当代诗人长期作为小丑、哗众取宠者、留辫子的异类,和摇滚青年、吸毒犯,等等,被媒体和普通人嘲弄。我不回避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甚至类型,我愿意接受将人分为诗人和非诗人,而我自己坐在诗人那边。对于写诗,我没有过什么感激之情。
但我庆幸啊,比如到了现在,如果我坐在一桌人的饭局上,坐在市长、总经理、协会会长和退休老人的集会上,如果我不想说话,我就不会说话,如果有人愿意听我唱歌,我也可能选择唱歌……诗,让我感到身上有了护身甲,我活得比较真实,大致依照自己当时所想去做。
诗让我不因沉默而羞愧,除非我真的感到羞愧。
再说我也乐意写诗。
不是所有人都能写诗,甚至,成年的文学、哲学……一切看似无用之书的读者,已经很少很少了——你可以留意下,即便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地铁上、街边,几个人在读书——而不是背单词呢?我觉得读书,对于成年人来说,好像已经成为一种需要纯真(请打着重号)来支持的行为。
写诗比读书更不易,你手上能写出杰作,更是万里挑一吧——去年似乎有人统计,中国有近百万诗人。
我写诗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我现在隐隐有这样的感觉:这也是我留给世界的遗产。
我的记性不好,中文词汇量也不见得太多,前几天读一本书,其中提到《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这个人终其一生不被同时代人所知,他在“未来将还他以公道”的想法中获得安慰,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并且生活下来。
不管如何,司汤达如果不写出他的《红与黑》,世界上也就没有《红与黑》。《红与黑》和你手上的《小马过河》当然也不一样。我很希望能看到自己或被认为有创作《红与黑》的能力。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我的生活别有所图,但我活着,是希望能留下一部“红与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
哈哈,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自大了。我还是原谅自己此刻的自大吧。
诗歌君:读你的诗,总感觉里头的人物透着一种温和的颓废与现实的无奈,像小说,又像你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投射。而在现实中,你是凤凰读书的主编,几年来做的得心应手。两者比对,你感到诗歌中的塑造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有『分裂感』吗?
严彬:一个拥有理性的人在最终分裂之前,是能够保持整体平衡,让自己站在绳子上的。
我自己并不赞成类似“非此即彼”的做事与生活方式。我觉得怎么样几乎都可以——我是指做一件事情,或者生活,不做强人所难的事。
也许是我太凑活了,这不符合处女座的一贯特征。我可以选择中午吃食堂,或者不吃,也可以去外面吃,我如果没有去外面吃,是因为我当时想,去外面吃了也不过如此,那为什么要去?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对自己甚至组成的家庭负责,我也工作,我并不能以写诗或者文学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