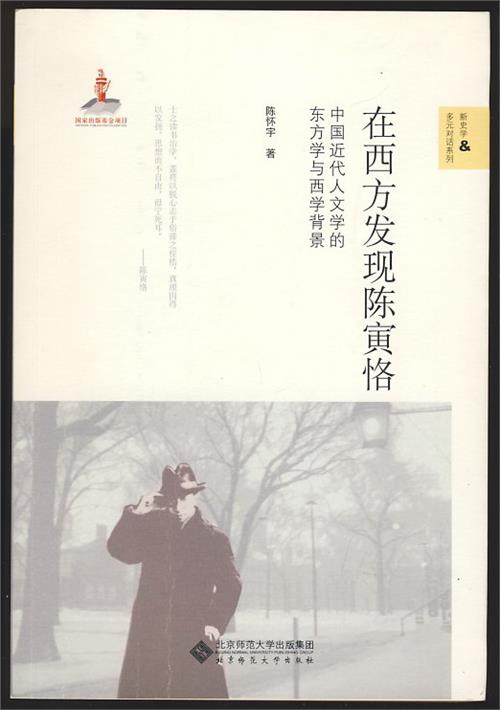陈寅恪俞大维 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陈怀宇,生于1974年,江西樟树人。先后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并获选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历史学部研究员、剑桥大学克莱尔堂(Clare Hall)斯伯丁研究员(Spalding Fellow)。
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宗教史与思想史、丝绸之路文化史、近代思想与学术。已出版《中国中世寺院主义之复兴》、《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近代传教士论中国宗教》、《景风梵声》等论著,并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1921年秋,陈寅恪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和东方古文字学。他在柏林学习期间结交了一批德国的师友,其中包括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缪勒(F.W.K.Müller)、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 idt)和诺贝尔(Johannes Nobel)。
关于这几位印度学家,新出版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陈怀宇著,下文简称《发现》)做了一些错误的介绍和推测。这些错误有的很简单(比如页303图六十"盛年吕德斯",其实是页228图五十三"格伦威德尔"的错配),有的则不那么简单,值得多评述几句。
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经提到,在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方面,缪勒是影响过陈寅恪的西洋学者之一。但《发现》却说缪勒"没有在中亚史地方面下功夫"(页308),这就和俞大维所说发生矛盾了。
从上下文看,作者大概是把F.W .K .Müller同另一位更著名的印度学家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给搞混了。缪勒于1883年入柏林大学学习神学和东方语言,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新成立的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工作。
1901年,他曾受普鲁士文化部派遣远赴中国、日本和朝鲜为民俗学博物馆搜购古物。缪勒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是释读了普鲁士探险队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现的若干种东方古文字,"吐火罗语"一词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孙次舟在其《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西北通讯》第3期,1947年5月)一文"附记"中,曾提到陈寅恪引用过缪勒的一个观点:"本文系拙著《匈奴种族研究》之一章,该文全部曾经陈寅恪先生看过。
对匈奴非东方土著、系由西方东来者,陈先生曾提示意见曰:‘德人F.W .K .Müller谓莫顿之名出于依兰语,盖火神之义。若其说果确,则亦匈奴与西方有关之一例证。’"(转引自《匈奴史论文选集》,页532;"依兰语"即古伊朗语)这段话似乎从未受到陈寅恪研究者的注意。
瓦尔德施密特的名字出现在陈寅恪《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一文中,写作"林冶",就是"Wald"(林)和"Schm idt"(冶人,即铁匠)的对译,可惜《发现》把"林冶"全部引成"林治"了(页312、313脚注1)。
我十多年前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借阅过林冶的《说一切有部比丘尼戒本梵文残片》(1926,其博士论文),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曾感谢陈寅恪帮助他解释了若干汉文佛教术语。林冶和伊朗学家Wolfgang Lentz合作,于1926年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中的摩尼教汉文残经《下部赞》的一部分校译刊行(Die Stellung Jesuim Manichaeism us)。
在1926年9月6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一封信中提到:"顷陈散原之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学校,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言论敦(伦敦)有汉文摩尼教赞颂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关系。"陈寅恪提到的汉文摩尼教赞颂,应该就是指林冶和Lentz校译的《下部赞》。
诺贝尔在1927年译注过慧皎《高僧传》里的《鸠摩罗什传》。学者陆扬注意到,在译文序论的末尾,诺贝尔曾感谢陈寅恪"为他解决了材料释读和其他方面的许多难题",于是认为"这似乎也是西方学术著作中最早提及陈寅恪的记录"(参看陆扬的《解读〈鸠摩罗什传〉》及《发现》页60)。但如上一段已经说过的,比诺贝尔还要早一年,林冶已经在其正式出版的论著中提到陈寅恪。
《发现》的作者根据诺贝尔1911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陈寅恪正好在1910年到1912年间在柏林大学游学,推测诺贝尔"估计是在1910-1911年间在阅读汉文文献时获得寅恪的帮助"(页112)。但诺贝尔学汉文的时间似乎较晚,与他后来学术兴趣转向北传佛教有关,1911年前后关注的主要还是纯粹的印度学问题,似无可能阅读汉文文献,更别说慧皎的《高僧传》了。
还有件事值得提一下。在陈寅恪通过季羡林卖给北大东语系的东方学书刊中,有一本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翻译的Die Hundert Strophen des Amaru(1925),是诺贝尔根据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吕克特手稿整理出版的。据说此书前面有诺贝尔亲笔所题"1925年11月26日于柏林",不知道是不是他签赠给陈寅恪的。
在自己学习的过程里,以及同这些德国师友的接触和切磋中,陈寅恪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特征获得了一些迥异于俗流的认识和体会。据徐志摩说:"陈寅恪君在海外常常大放厥词,辩印度之为非东方的。"这一对印度人文化和心理所下的总判断,现在看来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由此还可以看出来,陈寅恪并不像《发现》作者想象的那样对"印度人心理"这类问题"全不关心"(页308)。( 学者:高山杉,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