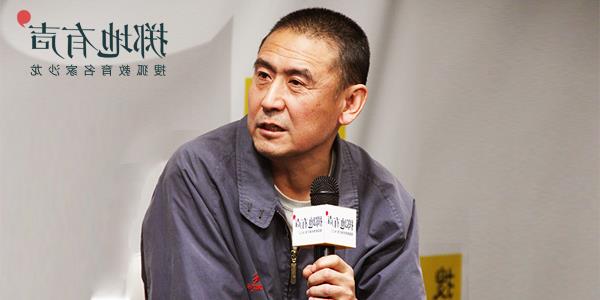北大郑也夫 北大教授郑也夫开设教育批判课:顺从不意味着被洗脑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退休前的最后一门课,是领着学生们“批判”中国教育。
这堂名为《批判的教育社会学》的课程开设于2010年9月。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老师传授的是理论,但课程的核心内容却是要求学生们进行一项社会调查,“翔实地描述教育领域中的某一个博弈、现象或勾当”。
用郑也夫自己的话讲,“教师中一个眼光毒辣的异端,凭借身上的少许感召力,调动出一个个后生的热忱。后生来路各异,故事五花八门,其中颇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比如,一所乡村学校如何倾全校之力迎接检查。
比如,一所高中如何通过鼓励学生弃考制造升学声誉。
比如,一个制造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如何以分钟计算、精确控制学生。
2014年1月,这些年轻人的课程论文结集出版,题为《科场现形记》。在书里,郑也夫亮明自己的观点:“中国久有科场,演至清代习八股被冠名曰‘制艺’。到了鄙俗之今人口中,高考被说成是‘敲门砖’。不期科举废弃百年之后,敲门人成山成海,敲门砖诡异奇绝,便是清代科场鼎盛之时亦不可比肩。”
除了展现教育之种种怪现状,在郑也夫眼中,学生们从大学、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里带回的这些故事其实还牵涉着他未竟的社会学教学,“我希望学生可以从中训练出一种对待问题的思维,不能光从书本到书本,不要人云亦云,要养成做点实情研究的习惯,要动手动脚去调查,把现状搞得水落石出后再去发言。”
讲好一个故事,最好是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当郑也夫开始形容自己在教育领域里的角色时,他先后称自己为“怪物”、“边缘人”以及“超龄愤青”。
事实上,这些词的确可以概括出这位社会学教授的行事作风——他反对科研腐败,为此从来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他发现北大运动会上存在体育特长生冒名顶替参赛的现象,便给副校长写信要求体育部整改;他甚至不惮于公开抨击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试题出得“太过垃圾”——在考试培训机构的“帮助”下,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读过的学生也有了进入面试阶段的可能,郑也夫将此视为出题者同考生博弈中的完败。
“老爷子不是争胜,而是争理。只要他认为在理的东西就会力争到底。”一名硕士生这样评价郑也夫的性格。
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性格部分促成了郑也夫在60岁的时候决定开设一门全新的课程。“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攥着全世界多大比重的基因库?按照正态分布,在顶级大学里面的学生应该是才能非常之高的,能让全世界惊叹的。然而在我所接触的学生里,我没有看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我没有看到哪个学生对哪个门类特别上瘾,没有少年曹禺这样的人了。为什么?我觉得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大把大把的学生在后天被修理坏了。”
提起开课的动机,郑也夫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愤懑”这个词,“这应该是你最熟悉的领域,不用研究就知道很多事情,如果一个搞社会学的人对教育问题失语,说不过去。”
颇具意味的是,原本郑也夫初拟的课程名称是“教育社会学”,却因为教务部要求避免课程名称重复而不得不加上了“批判的”三个字。至今,他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两位教授不可开设同名课程,并坚持将此也视为中国教育之荒诞的最小证据。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自嘲道:将风格做成标签贴在脑门上,好生无趣;以批判的旗帜邀集好事者,不失为策略。
选课开始后不久,这门能容纳150人的选修课便已经满员。在郑也夫的从教生涯里,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从来不开必修课,“凭什么我的课你就必须来,必须学?我不愿意发生这种误会,所以我只开选修课,选我课的,都是自愿上贼船,有点兴趣了,再加上点缘分,咱们就同舟共济一段。”
郑也夫上课的方法同样很特别——不管讲授什么样的课程,他的课堂一向是两个旋律并行:理论传授与学生的社会调查作业。而且,郑也夫对于学生完成一份有价值的社会调查的看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他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1945年以来的德国教育》,作者的一个观点令他印象深刻:学校教育研究,长期以来在德国是以“教育实情研究”的名义进行的。
“德国学者的话让我知道了,此一做法可以‘上纲上线’,它不是一个‘侏儒的’偏好,它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堪称是首要的工作。实情不知晓,谈什么道理,搞什么方案,构造什么理论?”郑也夫说。
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十几年,郑也夫发现,长期不当教育养成的“八股思维”严重影响着一茬茬的年轻人,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一写作业就愿意掉书袋,“全是大话空话玄之又玄的废话,言必称卡尔·马克思,要么就是马克斯·韦伯,学生读了多少书,能和哪个大师对话?不是一定要有这个节目吧。”
一位学生记得, 郑也夫在第一堂课上就强调这门课“不伺候八股”,而学期作业也不是“论文”,而是一项“实情研究”,“他说想要我们讲好一个故事,最好是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教育应该是一种“化”的过程,它需要教会你许多准则,也需要教给你不单一的价值判断
智楠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四学生。一年半之前,她选上了郑教授的这门课。她记得郑也夫当时曾说过,“你们的作业不用写成标准的论文格式,做一个调查就可以”。
当时智楠通过社团活动结识了来自衡水中学的几名同学,她决定以衡中为调查主题。这所连续13年成为河北省高考第一名的“超级中学”如此有名,以至于智楠过去所在的省重点高中老师还专门前去观摩学习,然后长吁短叹地向学生们介绍衡中的学习方法。此前,智楠对衡中的印象停留在“跑步喊口号、升旗背古诗”这样的传闻中,“就觉得学校太变态了呀!”
她清楚地记得,在对衡水中学展开访谈之前,自己曾经通过数据库查阅了所有关于衡中的文献资料,结果发现人们对于衡中的评价往往容易走向极端,“校方或者政府部门发表的文章往往是一边倒的褒奖,而媒体报道的资料则是一边倒的抨击”。
“我就是想客观地做一个记录。”智楠回忆,自己先后采访了5位2010年毕业于衡中的学生,他们对于衡中最为一致的印象是——量化一切。
其中一位受访同学就向智楠回忆起,自己平时的作息安排是,不能早于5点半起床,但要在5点36分赶到操场跑操;可以在12点半结束上午的学习,但12点40分就必须躺在宿舍的床上;晚上10点左右结束晚自习,但必须在10点07分进入宿舍并在10点10分前躺在床上。
这种对时间精确到分钟的控制,并不只出现在作息表上。在衡中,每一间宿舍的门上都有一扇小窗户便于老师检查,任何有可能被视为不按时睡觉的行为,都有被记违纪的风险。
“曾经有个人被记违反午晚休纪律,记的是10点20分某某宿舍某某床突然坐起。反正就是突然坐起。”一个学生提起。而另一名学生则记得,“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玩手指头,然后路过的老师就看见了,记:某东南下(铺)女生玩手指。”
一位姓刘的受访者直言不讳地告诉智楠,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她几乎整整三年睡觉时都没有脱过衣服,即使冬天也只是盖着羽绒服睡觉,“在衡中这样的现象也不是少数”。
在同学们的回忆里,衡中的严苛并不仅限于对时间的安排,任何有可能被视为影响学习的行为,包括抖腿、转笔、靠墙坐乃至在自习课时抬头都有可能被记过。
但令智楠感到意外的是,伴随着高考的成功,大部分接受采访的衡中毕业生都对那段生活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一位曾经“在高中想要挑战它”的同学如今已经转变了看法,“其实衡中教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抗压能力。”另一个明确的支持者则提出,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能让学生在3年的时间里只认真干学习这一件事,他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有了孩子,“仍然会送他去衡中学习”。
在受访者中,一个叫何天白的学生是为数不多的“批判者”之一。这名被保送到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写过一本以衡水中学为蓝本的小说《重点中学》。他告诉智楠,衡中给他带来了一些东西,却也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写了这么一本书,所以好多人也知道了我,在人人网上加我。
但是我看到一些师弟、师妹发的评论,觉得他们的许多看法我都不能理解,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我觉得教育应该是一种‘化’的过程,它需要教会你许多准则,也需要教给你不单一的价值判断,但是衡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个阶段,用不着你褒贬,你要做就做一个范儿比较正的东西,把事情运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
后来,智楠给自己的作业起了一个题目,叫《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但在通篇文章里,她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具有价值判断的个人评价。除了引述何天白的观点,文中再也找不到一点“批判”的影子。
“这就是我想要的。”郑也夫说。尽管他在讲课时不乏批判姿态,但在指导学生作业时却“最忌讳批判”。
他强调道:“在这个阶段,高水平的批判你还达不到,廉价的批判你就别来了,用不着你褒贬。你要做就做一个范儿比较正的东西,去呈现复杂,去表现细节,把事情运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就是最大的意义。”
2010级本科生李利利记得,自己的选题是“均衡生政策在乡镇中学”。出于惯性,她在开题的提纲里摆出了自己的预设观点,“我一开始真有看法,觉得均衡生制度治标不治本,想从公平的角度议论一下,结果就被郑老师批评了”。
“我只是希望学生们不要急于诟病某个局部的畸形,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也容易走向偏激。”郑也夫说,自己更希望学生认真地做一个研究,看看这样的故事是发生在怎样的背景中,“讨伐当事者大可不必。当事者有太多选择吗?”
他的提醒部分成为了2008级本科生张灵(化名)确定选题的初衷。
2009年,“重庆考生少数民族身份作假”事件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有31个学生因为被确定为伪少数民族考生而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当年的“文科状元”何川洋。来自重庆的张灵记得,在那场风波中,几乎所有的舆论矛头都指向了造假者,“都是要求曝光造假学生的名单,揪出其后台”。
“我就想,其实可以去调查一下少数民族考生的事情,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族身份为什么说改就改?后面还隐藏着什么故事?”后来,张灵通过老乡会找到了许多来自重庆的少数民族考生,其中不乏依靠身份造假涉险过关者。
一个往届考生告诉她,自己担任某局局长的父亲为自己运作了少数民族身份。因此,尽管他裸分只排在第27名,却成功进入了北大在当地的22人录取名单。这个年轻人提到,因为加分这件事,自己始终对一个高中同班同学心怀愧疚。在那一年的高考中,那名出身农村的同学裸分原本排在重庆市第9名,但所有考生算上各种项目加分后,他却因为只有一个三峡库区的5分加分而被挤到了第25名,与北大失之交臂!
在2009年少数民族加分事件曝光后,这名始终对那段往事耿耿于怀的男孩子一度想坦白自己的经历,但是最终没能鼓起勇气。他告诉张灵,在当时的重庆,各种隐性加分泛滥,其实他们的成绩都有可能考入北大,但却担心自己不办假加分就会被其他人的假加分挤掉。
通过深入的访谈,张灵发现,在这场加分博弈中,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往往是下下策的选择,“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体现在获取加分的能力上,大部分加分项目的分配名额都被超级中学、市区中学占据,市区学生还可以伪造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而对于偏远的县城,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则是为数不多的竞争路径之一”。
事实上,这种被迫性的造假不止存在于背景相对强势的家庭。她所访谈过最难忘的一个学生来自一所县城中学,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个学生告诉张灵,在自己参加高考的那一年,重庆市区的几所好中学,很多人都有国家二级运动员加分,因为怕儿子“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公平考试的机会”,他的父母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其找到了一户子女众多的人家,并设法将他过继到了该家庭名下。
为此,他不仅更改了户籍,也更改了法律上的父母。
直到今天,每当申请贫困补助或者需要填写父母状况时,这个男孩子都不得不写上假父母的名字。
“网友在抨击少数民族身份造假的时候,是否想过每个考生加分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有别的路子的话,谁愿意通过伪造民族身份来获得加分?如果谁也没有加分,或者加分机制分配及评选公平,还有谁会背弃自己民族,甚至是更改自己法律上的父母,来获得高考的20分或者5分?”
在这篇题为《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的背后》的学期作业里,张灵在综述分析中写下了上面这段话。
他们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
在编者按中,郑也夫曾经提及自己对弟子们的期待:没有比他们更胜任写出“教育实情”的人……他们完成这些文章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
“有时候连我都以为是编出来的。”郑也夫记得,有一次在看到一位学生的作业后,他急切地要与对方见面。
“这是真的吗?是在你的小时空发生的吗?不是传闻吗?”他一口气抛出了三个问题。原来,这位学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里,每逢高考,有权势的人便会打听清楚谁的学习成绩最好,并安排自己的子女坐在其旁边抄袭试卷。以至于到后来,这个县城里的优秀学生不得不纷纷以高考移民的方式逃离此地。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郑也夫说。
最终收录书中的学生作业共有43篇,书的封面上用黑体字印着这些话题的关键词: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高考移民自述、北京示范高中的借读生、高中招生大战、一所中学教改的导师制、寄宿教师家庭、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
教育学者杨东平在序言中将这几十篇作品称作对教育病的一张张彩超和CT,“不动声色而深刻入微,呈现出清晰的病理,时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发现”。
令杨东平印象深刻的是一篇题为《复读与中学声誉的制造》的文章。在这篇社会调查里,作者揭示了一所西部名校的成名之路——在高考前动员那些一本、二本无望的学生转考或弃考,从而通过压缩学生分母的方式制造升学声誉。作为回报,弃考生可以免费免试进入该校当年的复读班,而转考生则会被介绍到愿意接纳他们的学校,因为那里的“校绩”是以三本或专科上线人数来计算的。
另一篇被郑也夫津津乐道的作业是《一所乡村学校迎检过程考察》,记录的是一个乡村学校如何迎接“省教育督导室”检查的故事。
根据校领导的讲述,从5月份的动员大会开始到10月底的正式检查,在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将近200名教师平均每天要多加班两个小时。这意味着,全校教师要为了这次迎检足足多工作72000个小时,这相当于一个人9000个工作日的工作量。
时间用在了哪里?答案是素质教育。
据接受采访的教师回忆,为了符合上级的要求,学校需要新建造十几个专室,包括音乐室、美术室、微机室以及图书室等,而这些工作在此前全部处于空白状态,“学校只看升学率,根本不会关注那些所谓的素质教育之类的话题”。
除了时间,金钱是顺利迎检所必须付出的另一项成本。
“检查说白了就一句话,看你的钱花够了没。花够了就万事大吉,没花够就凡事遭殃。”在访谈中,县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提到,检查经费的开支包括基础建设、招待费用以及打点领导的送礼费用。事实上,据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回忆,就在检查之前,县长曾经专门去过省里一趟,“拜访”教育厅的几位领导干部,“其实就是到省里送礼去了,主要目的是为后面的工作开展做铺垫”。
值得玩味的是,一旦“准备工作”做到位,检查当天的工作便简单起来——足足准备了半年之久的检查竟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小时。在一番汇报之后,督导小组给出了颇高的评价,尽管他们并没有看到学生——为了避免检查小组与学生接触,学校临时将课间休息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
郑也夫对这篇作业给出的评价是:如果你不谙上级检查组对学校的视察,还算不上了解吾国教育的生态。
我希望他们上了这门课,能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生机的人
这门课讲完第五轮的时候,郑也夫也到了要退休的年龄。
看得出来,63岁的他仍然很留恋这个讲台。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起自己是如何在“暴土扬长的黑板前”,将学生们报来的题目写上个几百次,点评个几百次;也会哈哈大笑着回忆,每逢期末打开邮箱,“发现哎呦这么厚的一沓子作业”;他还津津乐道于同事对自己开的玩笑,“没有调查费,也没有课题费,恐怕只有你才能把他们忽悠成这样”。
“这只是一门选修课,所以我和学生们的深入接触并不多。但我希望他们上了这门课,能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生机的人。不盲从一个东西,就说明已经上路,就好办了。”谈起自己教师生涯里的最后一门课,郑也夫这样说。
2007年入学的褚文璐是郑也夫这门课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她后来成了郑也夫的研究生。她坦承,上大学之前,自己是个不太爱思考的学生,“对主流话语比较信服,就连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也是随大流选的经济学”。
某种意义上,郑也夫的治学风格部分影响了褚文璐的大学生涯。在一次读书会上,郑也夫提到自己是77级的老三届大学生,他记得那年的高考录取率是4.8%,现在则是60%以上,但他却感到“那时的高考竞争都没有现在这么激烈”。“郑老师对我们说,有很多人觉得他太激进,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体验或见识过不同的制度,失去了想象,见怪不怪,所以才接受甚至认同现状。”
“经过那门课的训练,如今我对一些社会现象不会再那么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自己活得更明白,也更聪明了。”褚文璐说。
同样是在研究生阶段开始深入接触郑也夫的李海蓉,也对那门以“批判”为主题的教育社会学课程印象深刻,“他说自己愤懑,但我觉得愤懑只是态度,他想带给我们的东西是理性”。
李海蓉来自农村,接受采访时她正在老家过年,电话里还能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在郑也夫的课上,她的选题是“台湾高校与北大的比较”。借着操作选题的机会,她结识了多位来自台湾的北大学生。在对他们的访谈中,李海蓉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NGO。也第一次了解到,在台湾学生的暑期生活里,“做义工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
“在此前的大学生活里,我从来没有这样系统地去了解过其他大学里的事,更谈不上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于是逐渐认为一切都是自己所见到的那样,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在李海蓉看来,这门课让她有了不一样的眼光,“不再把学习看做评判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
与她们不同,2010年毕业的汤宁如今已工作了3年多。但她依然能清楚地记起,郑也夫喜欢说自己是“精神的贵族”,还经常告诫学生要多给思想“做体操”。她说,郑也夫教会自己很多东西,比如“生活上的顺从和精神上的批判可以同时存在,顺从不意味着要被洗脑”。
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个嗓门很大、坐在教室里最后面都能听见他声音的“超龄愤青”已经退休了。他们也并不知道,为了这门课的学生作业可以结集出版,郑也夫先后找了好几家相熟的出版社,“我说如果你们想出版我的新书,就得把学生们的作业也捆绑出版”。
某种意义上,将每门课的学生作业结集成书,已经成了郑也夫的习惯。加上这本《科场现形记》,他已经为学生编辑过16本文集。“就当是留下一份沉甸甸的记录吧。回过头来看,我们很高兴,我们很踏实,我们没有虚度。”
五六年前,清华法学院的王亚新教授对他说:“你学生的文集,是我课上的必读书,有时候读他们的文章,比读你的书还有乐趣。”去年,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晓晶也找到郑也夫:“我要求我们学习写剧本的学生必须来看你学生们的文集。时下的剧作家总是胡编乱造一些故事,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当捧着《科场现形记》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郑也夫高兴得像个孩子。